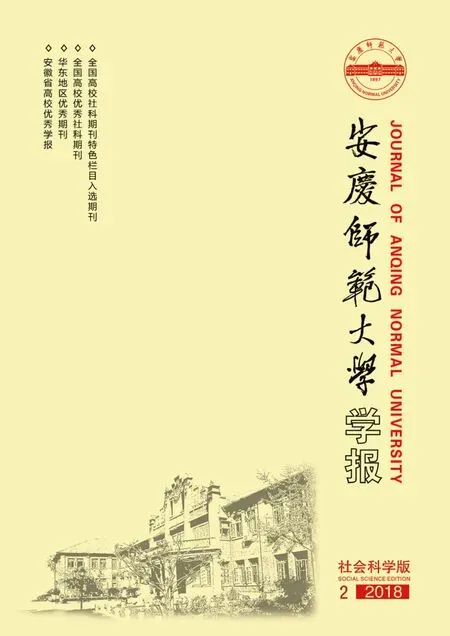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困境、成因与破解
——兼谈实质性公众参与
范华斌
(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230)
一、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困境
工业化、城市化在驱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亦衍生出众多威胁公众安全与健康的负面后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便是这一后果的突出表现。水源污染、雾霾肆虐、固体废弃物以及辐射已经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生活风险的一部分。为了遏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除了从制度层面对各种排放物的排放标准做出严格规定,从组织层面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从政策层面出台各种激励/惩罚措施来规制企业行为外,还试图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如加强环保类项目建设,降低和消解生态压力。这类项目建设通常具有公益性,涉及大多数人的环境权益,但通常会给项目所在社区带来安全与健康风险。垃圾焚烧项目建设,虽然减轻了周边较远区域的垃圾吸收压力及其他次生风险,但对项目所在地而言,这一风险是额外的。也正因为潜在风险的不公平分配,环保类项目选址通常会遭到所在社区公众的普遍反对,以致项目迟迟不能落地,或只能迁址。以垃圾焚烧项目选址为例,仅2016年4—6月发生在浙江海盐、海南万宁、江西赣县、湖北仙桃、广东肇庆的抗争性群体事件,均以选址搁置或搬迁为结果,无一例外。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屡屡出现“项目选址—公众反对—项目搁浅或迁址”的怪圈,陷入一闹就停、一闹就迁的零和博弈困境。
二、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困境的生成
要想解析选址困境是如何生成的,必须就传统选址决策模式固有的内在张力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垃圾焚烧项目选址的传统决策过程为“项目预选址—风险评估(环评)—政府宣布”。这一模式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从决策结构看,选址决策属于地方政府内部事务,决策主体是单一的政府选址机构,即便是项目风险受众也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二是对项目建设风险的评估,包括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后果”“可接受程度”等的研判,建立在科学的风险分析基础上。这就决定了技术专家(官僚)在风险评估中的核心地位。从理论上讲,只要科学的风险知识能保证项目风险得到客观准确的评估,同时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选址机构以公众的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客观公正进行科学决策,这一选址模式就能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然而,这一决策模式在垃圾焚烧项目选址中的实际运作存在如下问题。
(一)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导致客观的风险评估存在困难
科学知识存在“不确定性”和“滞后性”特点,不是所有项目风险都能通过科学的风险分析方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是有毒有害气体,但这种毒性是否可控即便在科学上也充满争议。为了防止垃圾焚烧的有毒气体扩散,需设置垃圾焚烧厂与公众的安全距离,那多大距离是安全距离?《生活垃圾焚烧污染可控制标准》(2016修订版)规定:“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生活垃圾焚烧厂厂址的位置及其与周围人群的距离”。但该《标准》并没有标示出明确的量化范围。并非不想,而是很难给出科学、可信的依据。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特征意味着垃圾焚烧项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后果”“可接受水平”等判断,即便在专家系统内部也会存在争议。一旦预选址所在社区的公众知晓这一风险认知分歧,特别是风险评估结论与公众的切身感受背道而驰时,“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1]便会产生,立足于科学评估结果的政府选址决策就会受到挑战。
(二)封闭式、精英型决策结构引发公众信任危机
“项目预选址—风险评估(环评)—政府宣布”这一决策模式是一种封闭式、精英型的决策结构。主要体现在决策主体单一、决策过程不公开、信息不透明。从垃圾焚烧项目选址、环评到开工的整个过程缺少公众或第三方机构的有效参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项目选址阻力,要么在政府官网不显眼位置静悄悄地发布选址信息,公众并不知情。如湖北仙桃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中,官方表示曾在环保官网进行过项目公示,但多数公众表示从项目选址到招标建设的两年内,地方政府刻意隐瞒相关信息,周边社区对正在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并不知情;要么突然公开,等一切已成定局再公布。根据《南方周末》报道,2014年惠州垃圾焚烧厂选址一直在封锁消息中进行,定址后突然公布,引发了公众的激烈反对,直至换址,风波才平息。从众多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引发的抗争性行动案例可以看出,全程隐瞒信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公众了解到相关信息,即便选址机构会采取一些解释、沟通措施,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也只会适得其反,失去的是公众对选址机构的信任,甚至选址机构的一些规范化行为也会受到连带影响而被公众否决。选址决策过程不透明、信息不公开会引发公众对这一“暗箱操作”的异议。而不时见诸报端的利益共谋案例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选址机构的不信任。2010年1月30日,《亚洲周刊》的一篇《烧不掉的垃圾真相,中国环保公害揭秘》就曾揭示了以海归人士为核心的、由学者、企业家、国外设备供应商、投资者所组成的利益集团,通过先说服地方高官,后撬动环保局长的方式,形成庞大的利益链,共谋获利。
(三)风险受众-技术专家风险认知分歧
选址社区公众与技术专家围绕垃圾焚烧项目风险的认知分歧是引发选址失败的抗争性行动发生的先决条件。这一分歧与上述两因素相关,即公众对立足于科学知识的风险评估的怀疑,以及对封闭式、精英型决策过程的不信任和利益共谋的担忧。但分歧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两者认知风险的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别。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认为,普罗大众的风险认知与其归属的文化类型或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风险威胁到现有生活方式时,人们倾向于重视和高估风险,当风险没有影响到或是维持现有生活方式所必须之物时,人们倾向于低估或有意忽视风险[2]。风险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大众传媒、个体经验和生活阅历、本地记忆、道德信念以及个人判断的话语为依据而建构起来的[3]。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因素如对麻烦的体验、感觉污染物的存在、对污染物的熟悉感、担心经济下滑及是否相信地方官员保护健康和福祉的能力等,卷入了风险解读的复杂过程,特别是社区环境通常成为风险认知和行动的重要依据[4]。由此可见,在一般民众眼中,风险一词并非单纯的技术概念,更多的是社会生活概念。公众通常在风险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关系中来建构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这一风险认知方式与专家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风险评估方式在逻辑上存在根本差别,且这一差别成为双方认知分歧甚或矛盾的认识论根源。当传统选址模式在选址实践中遭遇抵制时,选址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临时性地普及科学知识来设法抹平认知分歧。这种做法虽意识到了认知分歧这一事实,却对分歧产生的原因没有深刻的认知,无法取得预期成效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三、突破选址困境:反思科学精神,调整决策结构,尊重公众认知
上述三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是传统选址模式本身固有的张力,后一个因素则凸显了引发公众抗争行动的风险认知分歧的认识论根源。这一根源——风险认知方式差异与传统选址模式所反映出的科学崇拜理念(否认公众风险认知的合理性)是一致的。因此,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失败的根源应归咎于选址决策结构及其背后反映出的一般理念。结构性问题当然要通过调整决策结构和转变理念来解决。
(一)正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反思科学精神
传统的项目选址模式与我们生活和工作日常提倡的“科学崇拜”精神是相吻合的,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则必须考虑到科学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这一不确定性不但会引发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分歧,甚至在专家群体内部也会引发分裂。由于认知分歧与分裂会产生导致选址失败的抗争性行为,选址决策机构有必要反思选址进程中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反思并不是说要否定科学知识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会使风险评估偏离科学评估要求的客观、精确。为了降低这一不确定性,减少相关负面后果,选址决策机构有必要考虑引进或参考其他领域的知识,使选址决策显得更加合理。比如面对垃圾焚烧产生的有害气体“二恶英”是否可控这一在科学上充满争议的问题,决策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垃圾焚烧项目立项、建设和建成运作中是否发生与“二恶英”不可控相关事件、发生率是多少等实践经验。同样,垃圾焚烧项目与居民区的合理距离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获取较为准确、可信的参考标准。当然,面对选址所在社区对风险评估的怀疑,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选址机构有必要客观陈述垃圾焚烧项目风险及风险评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认真听取所在社区的利益诉求,合理尊重公众风险认知,与公众协商解决风险的措施和应对这一不确定性的方法,以消除疑虑、取得信任。
(二)调整决策结构,引导公众参与,提升公众信任水平
结构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结构优化才能得以解决,面对选址决策结构带来的决策过程不透明、信息不公开引发的公众信任危机,最为普遍性的建议是制度性的缓解机制——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决策意味着决策主体多元化,潜在的风险受众、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体参与到选址决策进程中,能有效避免传统决策结构的封闭性,减少认知分歧。多元主体间的风险沟通对于达成一致的选址目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风险沟通的目的并非彻底抹平(也无法抹平)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认知分歧,而是将风险认知差异降低到可以接受选址的程度,即求同存异。由于垃圾焚烧项目建设给所在社区带来额外风险是不争的事实,风险沟通的议题通常不局限于或者说并不主要在于是否存在风险,而且包括风险评估议题,如对项目所在地的长期保护与补偿机制、各社区间的义务均摊、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等。议题拓展有利于释放因风险不平等分配引发的选址社区公众的“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愤懑情绪,也有利于弥合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上的风险评估与立足于社会理性的公众风险认知之间的差异,在尊重这一差异基础上达成妥协与共识,最大限度避免基于认知差异的“邻避运动”,以减少项目选址的实质性阻力。另一方面,公众参与选址决策也是有效的监督机制,能避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共谋行为,确保选址决策合理、科学。
一旦公众参与成为选址实践的必要环节,就意味选址社区的风险受众被“赋权”,成为影响选址决策的因素。这一赋权过程有助于培育和提升公众基于决策过程开放、信息透明的对选址机构的信任和信心。信任是合作关系中永恒的话题。作为公众参与主导机构的选址部门必须认识到,社会信任的缺失是一个宽泛的、根本性的社会现象[5]。因选址机构在过往选址实践中欺瞒甚至诉诸暴力的表现,以及监管机构对环保企业超排、偷排及环保产业项目运营过程监管不力等历史因素所形成的较为低下的信任关系要想在选址时间框架内得到根本性扭转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当选址遭遇阻力时,通过各种途径释放的官方话语不能取得成效的关键。如何在不完全信任的情境下完成有效的风险沟通,便成为公众参与中选址机构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卡斯帕森等人认为,在不完全信任情境下,“风险沟通者的关键任务在于,培育一个使得信息和观点能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换的环境,便于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可以作出自己的评判和决定。”[5]当然,在选址过程中,信任问题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单向度地强调决策的“科学崇拜”,忽视公众参与,无疑阻碍了利益相关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不利于形成共识。
(三)正确认识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认知分歧,承认公众风险认知的合理性
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认知分歧源于两者认知方式差异,这一差异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即选址决策得不到社区公众的认同,会引发公众的环境抗争行为。基于认知方式差异的风险认知分歧是很难抹平的,从众多垃圾焚烧项目选址案例中可以看到,当项目遭遇公众的反对时,选址机构较为普遍的处理手法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公众中普及科学知识,但均以失败告终,公众并不认同选址机构的官方话语。这一处理方式的实质是否认公众风险认知的合理性。选址决策要想获得公众的认可,简单地将科学理性凌驾于生活理性之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风险认知中必须承认知识体系是多元的,知识一方面固然来自于科学研究,而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知识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允许不同于专家观点的存在,甚至承认不同认识论或可替代认知的合法性[6]。人们关于环境的观点是被诸如自主性、自我确定、公平公正和人类权利等概念所框定,要尊重不同民族、群体文化[6]。说到底,就是要承认在风险的认知过程中专家和公众的相对平等地位,不因专家的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而确保其在特定风险的理解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将其观点看成是凌驾于他人观点之上的特殊话语。进一步说是要承认认知方式的多样化,认可和尊重草根知识。而这正是实质性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
四、迈向实质性公众参与
无论是承认公众风险认知的合理性,还是正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反思科学精神,抑或是调整决策结构,引导公众参与,提升公众信任水平,最终均以公众参与选址实践为指向。实际上,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实践中的公众参与是存在的,但没有发挥解决认知分歧之功能,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参与在现实中往往流于形式,只有参与之外壳,失去了参与的实质内容。为了促进形式化参与向实质性参与转向,实践中还需要解决好如下问题:
1.参与双方要具备相对平等的参与地位
不可否认,与选址机构相比,公众因风险认知途径相对有限,风险信息来源缺乏,信息搜集、处理手段缺失,风险沟通渠道不畅等造成的弱势地位,客观上造成公众无法拥有足够的能力,平等参与风险评估的协商过程。要避免这一不平等局面,在选址机构充分认识到公众风险认知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尊重意识之外,提高公众的博弈能力是关键。这一能力提升有赖于公众自身努力,如公众应该学法、懂法和用法,努力做到依法参与;公众应该提高自组织能力,将碎片化个体有机联结起来,以组织方式参与对话过程,避免出现个体直接面对组织这一不利局面;与公益性非政府组织合作,降低信息搜集等市场化行为成本。在现有体制下,风险博弈中的平等地位的确立仅靠公众自身努力尚不够。选址机构有义务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来降低公众信息搜集成本,搭建有效的博弈平台,不断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提高其参与能力,在实践中探索形成公平公正的博弈规则和运转有效的参与机制。
2.有效区分利益相关者群体,避免参与人员结构不合理
韦尔巴(Verba)和尼尔(Nie)在《美国的参与: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一书中,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态度和行为取向,将公众参与者区分为非活跃者、专业投票者、狭义参与者、社群主义者、活动者和完全活跃者六个理想类型[7]。在案例分析基础上,何艳玲和陈晓运根据风险认知和行为取向,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划分为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与抗争者四种类型,深刻地阐述了存在众多而非单一的公众参与群体[8]。垃圾焚烧项目风险协商中同样存在不同性质的群体,在普遍的安全与健康诉求外,不同性质群体有自身独特的关注和需求,如根据“接近性假设”,离选址地空间距离不同的群体对项目的反对程度不一样;同一空间距离的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群体关注的问题优先等次不同、对选址机构的信任度有差别、参与的积极性程度有差异、博弈能力高低不同[9]。从逻辑上讲,在各种形式(如听证会、座谈会)的公众参与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个体组成参与群体,但公众参与实践则很少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需要作为主导方的选址机构在前期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将不同群体诉求进行类别化区分,在风险沟通中寻求不同的应对策略。而现实的参与个体选择,通常遵循方便原则,忽视了参与群体的代表性问题。以较为普遍使用的网络调查为例,因为技术或不知情等原因,其将相当一部分属于被调查的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了。就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实践来说,尤其要注意弱势群体,这部分人由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通常政治地位低下,参与机会缺乏且表达诉求的能力不足。一旦按照最小抵抗原则来选址,受到伤害的必定是这部分群体。从公平公正这个角度来说,参与活动的组织者在选择参与组成人员时,务必要覆盖所有群体,以保障参与人员结构合理。
3.合理设计公众参与议题
垃圾焚烧项目风险所涉及的群体利益存在客观差别,这一差别会带来基本诉求、预期和选址态度的群体差异。在公众参与方式设计阶段,首先需要对公众需求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类别化区分,在风险沟通中尽可能考虑每一类需求,照顾多样化的风险沟通议题,如固定资产贬值的补偿、选址机构的角色定位、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等。这些议题通常超越简单的技术风险评估范畴,需要选址机构、专家、项目承担者与公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双向回应。而就这些实质性议题沟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向公众“赋权”,承认其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有实质性影响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利于打破选址机构的“权力垄断”,有效构建选址机构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方法不一定能保证一项选址工程成功地被接受,但它的确向项目开发者与公众提供了一个坐下来谈判的机会,这正是瑞典各种核设施选址成功的核心所在[10]。
[1]郭巍青,陈晓运.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J].公共行政评论,2001(1):95-121.
[2]DOUGLAS M,WILDAVSK A.Risk and Culture[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3]MURDOC G,PETTS J,HORLICK J T.After Amplification: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Risk Communication[C]//PIDGEON N.KASPERSON R E,SLOVIC P.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56-178.
[4]FITCHEN J M,HEATH J S,FESSENDEN R J.Risk Perception in Community Context:ACase Study[C]//JOHNSON B,COVELLO V.The Soci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isk,Dordrecht:Reidel,1987:31-54.
[5]罗杰·E·卡斯帕森,多米尼克·高尔丁,赛斯·图勒.有害物质填埋场选址与风险沟通中的社会不信任因素[C]//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上).童蕴芝,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29-32.
[6]FAN M F.Justice,Community Knowledge and Waste Facility Siting in Taiwan[J].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0,21(4):418-431.
[7]VERBA S,NIE N H.Participation in America: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
[8]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J].学术研究,2012(5):55-63.
[9]杨槿,朱竑.“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3(1):148-157.
[10]PARKER F L,KASPERSON R E,ANDERSON T L.Technical and Sociopolitical Issues in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M].Safety,Siting and Interim Storage:Volume I.Stockholm:Beijier Institute,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