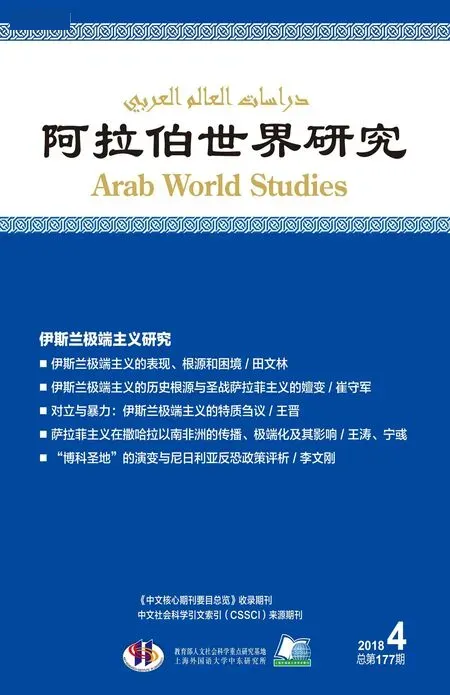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
崔守军
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性兴起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从“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动的“反恐战争”,到2011年以来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再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和扩张,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冲突已经成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与秩序的“毒瘤”。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或极端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它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排斥一切“异见者”和“异教徒”,以宗教之名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7页;Michael Fredholm, Islamic Extremism as a Political For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entral Asian Islamic Extremist Movements,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2006, p. 5.伊斯兰极端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将伊斯兰教政治化。在实践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往往采取组织化的运作模式,以极端手段排除异己,以期实现政治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的目标。*Brian R. Farmer, Understanding radical Islam: Medieval Ide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rn: Peter Lang, 2007, p. 36.作为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重要形式的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 Salafism),构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大多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思想基础。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中东政治和国际政治互动的产物,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异变的产物,具有全球性、暴力性和政治性等特征。*Gilles Kepel,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9-142; Emmanuel Karagiannis, “Defi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Jihadi-Salafi Movement, Asian Security,” Vol. 10, No. 2, 2014, pp. 188-190.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圣战萨拉菲主义已发展成为“伊斯兰国”等全球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和动员工具,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
厘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内核,是理解伊斯兰极端组织行为逻辑的关键。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仅包括在物理层面摧毁极端组织的实体,也包括从思想层面治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源头,最大程度地避免伊斯兰极端主义通过扭曲伊斯兰教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
从历史发展来看,早期伊斯兰教派哈瓦利吉派对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主流伊斯兰教与极端思潮论争的中世纪,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理论为伊斯兰思潮极端化和暴力化埋下了种子。进入近代时期,瓦哈比主义、伊斯兰主义思想中的激进内容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伊斯兰主义代表人物毛杜迪(Sayyid Abul A’la Mawdudi)、库特布(Sayyid Qutb)的思想,对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扎卡维(Abu Musab al-Zaraqwi)、法拉吉(Muhammad Abd al-Salam Faraj)、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和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等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圣战萨拉菲主义缘起及核心思想
“萨拉夫”(Salaf)在阿拉伯语中原指“前辈”和“先人”,后引申为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先知穆罕默德的前三代圣门弟子*Mohammad Abu Rumman, I Am a Salafi: A Study of Actual and Imagined Identities of Salafis, Amman: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14, p. 43.。“萨拉菲主义”(Salafism)是指保守尊古的伊斯兰主义思潮,主张通过宗教和社会改革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信仰与实践的思想和运动。*[美]哈伊姆·马尔卡:《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危机》,刘中民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第19页。萨拉菲派(Salafis或Salafists)强调“认主独一”(Tawhid),在宗教问题上主张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以及前三代圣门弟子的言行立教,倡导效仿“清廉的先贤”,是“尊古派”。*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萨拉菲派认为,由于真理是真主通过《古兰经》降示给先知穆罕穆德的,任何对《古兰经》和“圣训”文本进行的创新性解读都应被视为是“异端”,应予以禁止。该派强调,对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的尊崇会歪曲《古兰经》和“圣训”的本义,进而对尊崇真主造成障碍,因此只有“遵古崇正”才能净化教义、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貌,复兴伊斯兰文明并建立“真主主权”(Hakimiyyah)统治下的“哈里发国家”。
萨拉菲派内部存在拒绝暴力的寂静派(Quietists)和崇尚暴力的圣战萨拉菲派之分。后者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伊斯兰教义明确规定禁止杀害穆斯林或平民,这迫使圣战萨拉菲派着重从理论层面为其暴力行为寻求宗教合法性支撑,尤其注重运用“定叛”(Takfir)和“圣战”(Jihad)等思想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定叛”是指宣判某人为不信道者或叛教者的过程,主张推翻未按照伊斯兰教法建立的世俗政权和谴责不信道者。伊斯兰极端主义认为,“圣战”具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推翻“叛教者”建立的政权;第二种把“异教徒”从穆斯林的领土上驱逐出去,实现伊斯兰文明的复兴;第三种是“全球性圣战”,惩罚“异教徒”,还穆斯林以“正义”。*Mohammed Hafez, “Takfir and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Assaf Moghadam and Brian Fishman, eds., Fault Lines in Global Jihad: Organizational,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Fiss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30.
从思想源流上看,哈瓦利吉派倡导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和行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雏形,其中尤以该派中的艾兹拉格派(Azariqa)最为激进。艾兹拉格派不仅将那些犯“大罪”的穆斯林当作叛教论处,而且将那些非本派别者也列于“异教徒”的行列,认为这些人都应该被处死。*马轶才、丁俊:《哈瓦利吉派及其极端思想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3期,第3-16页。
长期以来,哈瓦利吉派因其极端主义倾向被伊斯兰教主流派别视为异端和边缘派别。为同哈瓦利吉派划清界限,主流伊斯兰教法学家对“叛教”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叛教即一位先前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言语或行为上摒弃伊斯兰教,例如公开宣称或被证实放弃伊斯兰信仰、持异端主张、对戒律明知故犯且拒绝悔改、公开质疑伊斯兰信仰本身等。*Diane Morgan, Essential Islam: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Belief and Practice,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0, pp. 182-183.具体而言,主流伊斯兰教法学家认为穆斯林的身份取决于言论、信仰和行为三大要素。其中,言论方面是指“清真言”(Shahada),即诵读对真主和先知的共同信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信仰方面是指遵循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行为方面则指履行伊斯兰教规则所规定的宗教义务。
最早反对哈瓦利吉派的是穆尔吉埃派(Murji’ites),后者认为应慎重并延迟(Irja)对“叛教者”的定性,“有罪者”并不见得就是“叛教”,因而该派又被称为“延缓派”。延缓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后来创立了哈乃斐教法学派,其核心观点认为信仰与“清真言”保持一致,信仰在心中,而不在行为中*Daniel Lav, Radical Islam and the Revival of Medieval Theolog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4.。艾什尔里派代表人物安萨里(Al-Ghazali)对此持相似立场,认为除非穆斯林公开否认“信主独一”、先知穆罕默德和末日审判,否则就不能被视为是“叛教者”*Sherman A. Jackson, On the Boundaries of Tolerance in Islam: Abū Hmid al-Ghzalīs Faysal al-Tafriqa,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6-47.,这种观点逐渐被伊斯兰教主流派别所接受。
二、 中世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
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的思想为当代萨拉菲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伊本·泰米叶认为,宗教信仰由言论、内心信仰和行为构成,只有特定的行为才能被视为“叛教”。他指出哈瓦利吉派的错误在于对“叛教”行为界定过于宽泛,但也对穆尔吉埃派持否定态度,批评穆尔吉埃派不能容忍伊斯兰信仰严格化的发展倾向*Daniel Lav, Radical Islam and the Revival of Medieval Theology, p. 33.。伊本·泰米叶的理论经发展后成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
伊本·泰米叶生于伊斯兰世界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从内部来看,中世纪伊斯兰教法僵化,苏菲主义盛行。由于“创制之门”关闭,伊斯兰教法学发展停滞,不仅难以撼动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四大教法学派的地位,而且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成为伊本·泰米叶着手改革的主要原因。8世纪后期,苏菲派由苦行禁欲主义逐渐发展为神秘主义,伊斯兰统治阶级分裂、腐化导致百姓生活困苦,进一步推动了苏菲主义的传播。苏菲主义的泛神论倾向与正统的伊斯兰派别格格不入。伊本·泰米叶目睹苏菲派的消极避世,认为任其发展最终会导致伊斯兰世界走向衰退。“苏菲派在伊斯兰国家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苏菲派沉迷于幻想,统治者沉迷于腐败,不约而同地使整个民族陷入困境。”*[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四册)》,朱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页。在此背景下,伊本·泰米叶对苏菲主义的否定立场代表了当时伊斯兰教内部的纠偏思潮和改革倾向。
从外部来看,1096年至1291年十字军进行的八次东征以及1258年蒙古西征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夹击之势,阿拔斯王朝被灭亡后,伊斯兰文化遭到摧毁,冲击了传统伊斯兰政治的合法性。马木鲁克王朝先后抵抗十字军和蒙古军,激发了王朝内部整个社会的斗志和尊崇自身历史与传统的思潮。出身于马木鲁克时代的伊本·泰米叶正是在这种内部教法僵化亟待变革、外部强敌环伺的背景下,提出了既强调改革,又充满保守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思想。
当代伊斯兰极端分子推崇伊本·泰米叶的思想,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叛教者”所持的排斥态度。泰米叶认为,穆斯林在内心顺从真主就意味着对真主的敌人持敌视态度。为支持这一论点,伊本·泰米叶援引了“圣训”中的相关论述:“那些没有抗争,甚至没有思考为什么要抗争而死去的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他据此提出,穆斯林应避免模仿非伊斯兰信仰,甚至不能模仿非伊斯兰信徒的穿着和饮食,因为这种模仿会导致伊斯兰传统的流失,“对那些(非伊斯兰)事物的喜爱和忠诚与伊斯兰信仰是不兼容的”*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i: The Ideology and Influence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50.。
但伊本·泰米叶也强调应该对领导者的错误保持容忍和耐心。“现在,由于人类更倾向于不公正和无知,统治者有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应该禁止穆斯林去反抗他们的领袖,只要领袖每日还在向安拉祈祷。这是因为统治者仍然尊崇安拉”*Fazlur Rahman, Revival and Reform in Islam: A Study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 2003, p. 157.,这一观点被当代保守的萨拉菲派作为效忠执政者的理论依据。
伊本·泰米叶的思想因其保守性和极端倾向,后被伊斯兰激进派别和极端派别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自身的理论体系,尤其以瓦哈比派最为典型。面对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腐败,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1703~1792年)寻求以更加狭隘的方式来实践伊本·泰米叶的思想。瓦哈比派认为,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仅靠履行宗教功修是不够的,除严格遵守“认主独一”原则外,还要对“叛教者”实施相应的惩罚*Hamid Algar, Wahabbism: A Critical Essay, New York: Islamic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2002, p. 32.。该派认为,宗教活动若遵循崇拜“圣徒”、“圣墓”等任何形式的苏菲主义行为,都属于“叛教”行为,是对真主的亵渎。这一主张源自伊本·泰米叶对苏菲派的批评,瓦哈比派据此希望完全铲除苏菲派,肃清其影响*M. Abdul Haq Ansari, “Ibn Taymiyya and Sufism,” Islamic Studies, Vol. 24, No. 1, 1985, pp. 1-12; Sayed Khatab, Understanding Islamic Fundamentalism: The The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Basis of al-Qa’ida’s Political Tactics,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1, pp. 64-65.。在历史上,穆斯林学者认为,崇拜“圣徒”、“圣墓”是一种善意的“创新”。但瓦哈比派认为,任何先知穆罕默德及圣门弟子未曾采用过的祈祷方式,都应被视为“大罪”。*Hamid Algar, Wahabbism: A Critical Essay, p. 35.
从1740年起,瓦哈比派开始实施阿卜杜·瓦哈卜的极端思想,捣毁了第三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的圣墓。*Ibid., p. 18.此后不久,阿卜杜·瓦哈卜所属的谢赫家族与沙特家族结成政治联盟。1746年瓦哈比派对被该派界定为“叛教者”的群体发动了暴力“圣战”,其手段十分残忍。*Ibid., p. 28.在当代,“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抢劫、倒卖文物、破坏圣墓、以残暴手段惩罚平民等行为,与早期瓦哈比派的有关做法较为接近。
三、 近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演变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列强以传播文明为借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领土和进行殖民活动,一场旨在复兴伊斯兰文明的运动逐渐兴起。发起这场运动的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8~1897年)。因受到基佐的《文明史》启发,阿富汗尼提出文明的复兴取决于美德。*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15.当时,欧洲思想家认为宗教并不是最重要的,但阿富汗尼认为践行伊斯兰教的理念能给人带来美德和力量,只有真正信奉伊斯兰教才能实现文明的复兴*Ibid., p. 119.。他由此提出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即以共同的宗教责任将穆斯林团结到统一的“乌玛”(Umma,穆斯林共同体)之下*Ibid., p. 115.。阿富汗尼的追随者发展了其思想,强调伊斯兰教是建构社会最理性的基石。教法学家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 1865~1935年)及其追随者通过共同创办《灯塔》(Al-Manar)杂志,将这种思想传播和推广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富有改革意识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则反对任何创新。*Bernard Haykel, “On the Nature of Salafi Thought and Action,” in Roel Meijer, ed.,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London: C. Hurst & Co., 2009, p. 46.尽管里达早年对伊斯兰教改革持开放态度,但进入晚年后,他在思想上开始转向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逐渐被里达所吸纳并用于推进伊斯兰化的进程。*Hamid Algar, Wahabbism: A Critical Essay, p. 231.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后,伊斯兰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真正将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的是毛杜迪。毛杜迪的“圣战观”和“伊斯兰革命理论”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相较于其他意识形态,伊斯兰理念对国家统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印度次大陆,由于逊尼派伊斯兰教被印度教、什叶派、英国殖民主义者视为威胁,逊尼派伊斯兰思想家严格划定了“真正的信徒”与“异教徒”之间的界线。*Quintan Wiktorowicz, “A Genealogy of Radical Isla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8, Issue 2, 2005, p. 78.这些思想对毛杜迪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杜迪承袭并系统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理论,强调伊斯兰教是摆脱“蒙昧”(Jahiliyyah)的唯一选择。意识形态一般是指个体或团体所持有的规范性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综合*Ted Honderich,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392.,毛杜迪将伊斯兰教理论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伊斯兰教遂开始替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权力阶层统治国家的基础。*Jan-Peter Hartung, A System of Life: Mawdūdī and the Ideologisation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43-59.毛杜迪宣称,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还是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致力于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160页。
在印度次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穆斯林通过发动“圣战”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为镇压穆斯林,西方殖民者将伊斯兰教歪曲成“一种嗜血的宗教,向自己的信徒宣扬屠杀”。作为回应,1927年毛杜迪撰写了《伊斯兰教中的“圣战”》(Al-JihadfilIslam)一书。该书后于1930年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圣战观”。毛杜迪将“圣战”界定为建立公正的伊斯兰制度、传播伊斯兰教以及与“异教徒”进行斗争的手段*同上,第165页。,强调“圣战”不属于战争范畴,其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制度的统治,不是为了消灭个人或集团或者摧毁他们的财产,而是为了消灭罪恶”。个人和团体都应该“惩恶扬善”,任何旨在使个人或团体走上“正道”(Sunna)的行为都属于“圣战”范畴。*同上,第166页。毛杜迪认为“圣战”以革命手段实现正义,且只能在伊斯兰国家中实现。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旨在实现真正的正义,不考虑任何阶级或国家利益*Jan-Peter Hartung, A System of Life: Mawdūdīand the Ideologisation of Islam, p. 15.,既然所有人类都应该受益于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正义,“圣战”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革命*Ibid., p. 22.。毛杜迪强调,“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神权国家,而是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民主国家*Ibid., p. 94.,世间一切权力皆归真主,只有真主才能统治人类,因此伊斯兰国家应该由具有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的人来领导,而且国家的管理不应该是独裁的,而应实行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分立。毛杜迪关于建立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尤其是对“圣战”的泛化,都对后来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嬗变
成立于1928年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组织之一,该组织的创立者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1906~1949)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穆兄会的目标在于进一步推进此前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促进宗教虔信、重建“伊斯兰国家”的理想。早期穆兄会主要强调劝诫和宣教,后来才开始频繁参与政治活动并建立了武装力量。*Omar Ashour,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Jihadists: Transforming Armed Islamist Movemen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7.1948年,穆兄会因其成员刺杀埃及总理诺克拉西而遭到当局大规模镇压,哈桑·班纳也遭暗杀,之后上台的纳赛尔政府宣布取缔穆兄会。
穆兄会被取缔时,赛义德·库特布(1906~1966年)是遭逮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库特布曾长期在美国求学和生活,但这段经历却使他的观点变得更为激进,逐渐从西方文化的仰慕者转变为西方制度的批判者。纳赛尔政府的镇压进一步加深了库特布思想的极端化。1964年,库特布的《路标》一书出版,该书提出了一套完整且具有鼓动性的极端主义理论,推动了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库特布也由此成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教父”。
库特布在《路标》中对毛杜迪的伊斯兰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库特布将“蒙昧”社会描述为“非穆斯林社会”或“在思想、信仰和律法上都不顺从真主的社会”。他认为,在任何时空中,人类都要面临选择:要么全然遵守真主之律法,要么实施人为的法律,而后者就是所谓的“蒙昧”状态。人类必须顺从真主才能获得自由,“蒙昧”状态实际上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因此需要通过发动“圣战”来“解放那些被奴役的人们,以便他们为万能的真主服务”。*Ibid., p. 65.
《路标》指出,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组织实践活动以解放人性”,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实行伊斯兰教法,实现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Ibid., p.101.库特布否认国家的最高权力源于“人民主权”,主张“真主主权”,认为只有把国家的领导权重新归还于真主,才能摆脱人为法律下的“蒙昧”状态。*Ibid., p. 148.他强调,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复归原初本真的伊斯兰是伊斯兰运动的首要目标,“所有不属于伊斯兰思想的事物应予以消灭”,因此穆斯林必须依靠“圣战”实现该目标。*William McCants, ed., Militant Ideology Atlas, Executive Report, New York: Combatting Terrorism Center, 2006, p. 10.库特布提出的“真主主权”思想成为此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核心内容,并广泛传播至伊斯兰世界。
1971年,受到毛杜迪和库特布理论影响的奥马尔·阿卜杜·拉赫曼(Omar Abdel Rahman)在狱中撰文,公然号召消灭“不信道者”和“异教徒”。根据他的定义,“不信道者”包括作为“有经人”(People of the Book)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与传统伊斯兰教倡导的宗教宽容思想相违背。*Jan-Peter Hartung, A System of Life: Mawdūdīand the Ideologisation of Islam, p. 218.此后,阿卜杜·拉赫曼的追随者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法拉吉将库特布的思想转化为实践。在他看来,穆兄会的行动模式不够激进,因而于1979年退出穆兄会并成立“伊斯兰圣战组织”,“基地”组织理论家扎瓦赫里也是该组织的核心领导之一。1981年10月6日,“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刺杀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埃及当局逮捕了法拉吉和扎瓦赫里。1982年法拉吉被处决,1985年扎瓦赫里出狱后离开埃及前往沙特朝觐,次年在沙特吉达结识本·拉登,而后者领导的“基地”组织于1988年成立。
哈桑·班纳被暗杀后,穆兄会领导人哈桑·胡代比(Hassan al-Hudaybi)继任。作为埃及上诉法院的法官,胡代比比穆兄会其他成员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Omar Ashour,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Jihadists: Transforming Armed Islamist Movements, p. 41.,他对库特布追随者日益激进的思想和暴力倾向感到焦虑。1977年,胡代比出版《宣教者,而非教法官》(PreachersNotJudges)一书,抨击库特布的《路标》,试图解决埃及社会日益严重的信仰问题,恢复穆兄会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力。胡代比从驳斥毛杜迪的思想入手,强调穆斯林是否恪守伊斯兰教信仰不能仅通过诵读“清真言或行为来进行判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认为,任何人为法律都会导致偶像崇拜,是“叛教”的表现。与毛杜迪立场不同,胡代比拒绝承认一个真正穆斯林的身份是由他的言语或行为决定的,因为很难从人的言语或行为来判断其内心的真实信仰。*Daniel Lav, Radical Islam and the Revival of Medieval Theology, p. 70.胡代比对“叛教者”的判断标准进行了修正,力图使穆兄会能够超越“库特布主义”(Qutbism)的极端立场。库特布及其追随者认为,顺从真主之外任何权威的行为,都属于“叛教”行为,针对“叛教”的穆斯林,理应运用暴力“圣战”或全球“伊斯兰革命”的方式予以征伐。胡代比对“叛教者”概念的重新界定,实际上否定了库特布极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基。《宣教者,而非教法官》一书的理论成为穆兄会新一代成员的指导思想,穆兄会开始调整策略,逐步放弃使用暴力手段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转而釆取更加温和、合法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进程。胡代比努力修正伊斯兰极端主义,成功将穆兄会改造成温和的伊斯兰组织。然而,胡代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理论的否定,也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社会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矛盾。
1979年,为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的巴基斯坦宗教学者阿卜杜拉·尤素福·阿扎姆签发了名为“保卫穆斯林土地”(In Defense of Muslim Lands)的教令,呼吁发动“圣战”以恢复穆斯林对阿富汗的统治。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响应号召并组建“圣战”队伍,本·拉登为此提供了资金。阿扎姆认同伊本·泰米叶的观点,强调“圣战”是“伊斯兰的神圣使命”,比礼拜、斋戒和朝觐等宗教功修更为重要,理由在于“圣战”的目的是建立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其他功修则是为履行个人的精神义务。阿扎姆全身心投入阿富汗“圣战”,不仅致力于发展“圣战”理论,而且设法筹集资金、招募国际“圣战”分子,发动了一场跨国“圣战”运动,因此被称为“全球圣战之父”。*Muhammad Haniff Hassan, The Father of Jihad: ‘Abd Allāh ‘Azzām’s Jihad Ideas and Implications to 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3, p. 105.
阿扎姆的理论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都具有复兴伊斯兰文明的诉求,但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上,两者存在本质区别。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认为,复兴伊斯兰文明通过践行伊斯兰教的美德来实现;而阿扎姆则认为,“圣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在阿扎姆看来,“圣战”有助于伊斯兰教迅速传播,使伊斯兰文明战胜其他文明,“圣战”是导致罗马、波斯两大帝国急剧衰败的根本原因。*Ibid., p. 106.
阿扎姆强调,“圣战”是穆斯林终结“蒙昧”时代的唯一路径,只有小部分精英团体能够在“乌玛”的引导下团结一致并发挥领导作用,精英团体所遵守的严苛条律是构建整个伊斯兰体系的基础*Ibid., p. 135,并提出“只有圣战和‘枪’,不谈判,不开会,不对话”*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 3.的口号。阿扎姆认为,解放阿富汗是从“异教徒”手中夺回穆斯林失去领土的全球“圣战”的第一步。*Abdullah Azzam, “Defense of the Muslim Lands: The First Obligation after Iman,” Religioscope, February 1, 2002, https://english.religion.info/2002/02/01/document-defence-of-the-muslim-lands/,登录时间:2017年9月14日。阿富汗“圣战”期间,阿扎姆招募和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圣战”分子,为后来“基地”组织的成立奠定了现实基础。1988年,阿扎姆的学生本·拉登成立“基地”组织,并很快发展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除“定叛“和“圣战”思想外,“效忠与拒绝”(al-Wala’Wal-Bara’)也是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效忠与拒绝”是指“对信徒忠诚,对非信徒持否认态度”,其实质是要求“信道者”断绝与“不信道者”之间的关系,“不信道者”包括那些非虔诚的穆斯林。约旦宗教学者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在当代语境下对“效忠与拒绝“这一概念的阐释强化了萨拉菲主义者对“异教徒”的排斥和仇视。1989年,马克迪西在其著作中批判了沙特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结盟,他甚至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视作对西方制度的崇拜。*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i: The Ideology and Influence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pp. 70-71.
五、 当代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全球扩张
1989年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次年,本·拉登回到沙特阿拉伯。不久,伊拉克发动对科威特的入侵,沙特担心自己成为伊拉克下一个入侵目标。本·拉登在会见沙特王室成员时提出动用“圣战”组织来应对威胁,遭到沙特王室拒绝。此后,沙特王室转而向美国寻求帮助,在本·拉登看来,美军的介入无异于异教徒对沙特领土的入侵。*Steven Brooke, “The Near and Far Enemy Debates,” in Assaf Moghadam and Brian Fishman, eds., Fault Lines in Global Jihad: Organizational,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Fissures, p. 49.形势的变化促使本·拉登转而对沙特境内的美军发动进攻。1992年,本·拉登与“基地”组织其他领导人联合颁布“法特瓦”(Fatwa,伊斯兰法令),宣布对“入侵沙特”的美军发动“圣战”,并对因此可能引发的误伤平民的行为进行辩解。1996年,本·拉登再次颁布“法特瓦”,号召“圣战”分子对美军“占领”的伊斯兰圣城展开攻击,“将异教徒驱逐出阿拉伯半岛”,导致极端分子在沙特境内频繁袭击美军。*Steven Brooke, “The Near and Far Enemy Debates,” p. 50.
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策动的暴力活动在该国内战中掀起了高潮。1992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因担心势力不断壮大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通过选举上台,遂宣布取消大选。随后,阿国内冲突不断升级,从阿富汗战场回国的极端分子开始加入“伊斯兰武装组织”(Groupe Islamique Armé)。此前,伊斯兰极端势力袭击的主要是政府目标,但“伊斯兰武装组织”却将袭击目标扩大至游客、医生、记者和知识分子等平民。“伊斯兰武装组织”头目安塔尔·朱阿伯里(Antar Zouabri)在其著作《利剑》(TheSharpSword)中试图为恐怖主义活动进行合法化解释,论证恐怖袭击的“必要性”。他指出,记者群体是帮助“叛教者”政府进行宣传的喉舌,学生则“通过继续学习来维护非法政府的稳定与延续”,任何不支持“伊斯兰武装组织”的社会成员都是政府的支持者,是伊斯兰“圣战士”袭击的目标。*Quintan Wiktorowicz, “A Genealogy of Radical Islam,” p. 88.《利剑》出版后,“伊斯兰武装组织”以部分村落支持政府立场为由,发动了数起针对这些村落的大规模杀戮。朱阿伯里将“定叛”思想运用到了极致,“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残暴行为令“基地”组织也感到震惊,“基地”组织随后宣布切断与“伊斯兰武装组织”的隶属关系。此后“伊斯兰武装组织”逐渐走向衰落。
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埃及境内兴起了“伊斯兰团”,该激进组织是穆兄会的一个分支,其精神领袖是奥马尔·阿卜杜·拉赫曼。“伊斯兰团”对埃及政府采取对抗策略,“定叛”原则在该组织的暴力实践中被推向更高层面,其袭击目标不仅涵盖政府公职人员,还包括知识分子和游客。阿卜杜·拉赫曼早期号召穆斯林对作为“异教徒”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发动攻击,1993年他曾企图对纽约世贸中心发动袭击,但未得手。1997年,“伊斯兰团”在臭名昭著的埃及卢克索大屠杀事件中枪杀了62名游客,令国际社会哗然。此后,在穆巴拉克政府的重拳打击下,该组织主动放弃了暴力。
国际环境的变化迫使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了策略调整。1998年,本·拉登对“基地”组织做出了重大战术调整,将攻击目标从占领穆斯林领土的“近敌”转向“远敌”美国。本·拉登在一份名为《世界伊斯兰战线共同对抗犹太人和十字军》的“法特瓦”中列举了美国的罪状,如侵占阿拉伯半岛领土、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灾难、支持犹太国家以色列等。本·拉登认为,美国人所犯下的罪行是对真主、先知以及全体穆斯林宣战,根据伊斯兰教义,只要敌人企图摧毁伊斯兰国家,发动“圣战”就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义务。该“法特瓦”得出结论,对抗美国不仅要打击“占领穆斯林领土的美军”,还要“摧毁美国及其盟友,不管是平民还是军队”,后者是任何穆斯林在任何国家都必须采取的行动,终极目标是“迫使外来者的军队撤出属于穆斯林的国土,从此丧失侵略和威胁伊斯兰世界的能力”。*Bin Laden et al., “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 World Islamic Front Statement,”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ebruary 23, 1998, http://fas.org/irp/world/para/docs/980223-fatwa.htm, 登录时间:2018年4月17日。该“法特瓦”标志着“圣战”从本地化向全球化的转变。同年,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3年后的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伊斯兰极端组织使用“远敌”与“近敌”概念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基地”组织开始广泛针对美国人发动袭击,这些袭击事件往往伴随着对普通穆斯林平民的误伤,但“基地”组织却声称误伤平民实为抵抗美国侵略的“圣战”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扎瓦赫里解释称,“防御性圣战”必然伴随“附带性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进攻性圣战”是一种选择,而“防御性圣战”则是一种必然,在“防御性圣战”中因误伤而死亡的平民会被追认为“烈士”。扎瓦赫里建议做好预防措施,并对遇害的平民家属提供补偿,但前提是在支持“圣战”后还有资金剩余。*Alia Brahimi, “Crushed in the Shadows: Why Al Qaeda Will Lose the War of Ideas,” Studies in Conflicts & Terrorism, Vol. 33, Issue 2, 2010, pp. 99-101.
被称为“基地”组织理论家的扎瓦赫里系统阐述了“定叛”与“圣战”之间的关系。他将“定叛”作为伊斯兰运动的核心思想,“圣战”则是具体的实施手段。对绝大多数伊斯兰极端组织而言,“圣战”是践行“定叛”思想的手段,其目标是拒绝实行伊斯兰教法或者对“圣战士”进行压迫的政府。无论是“暴君政府”,还是其效忠者或者与之存在关联的人,都被视为“异教徒”,即“圣战”的对象。
伊斯兰教教义认为,“穆斯林的生命是圣洁的”,但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看来,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旨在推翻“变节者”统治的暴力活动。“基地”组织的另一头目阿布·叶海亚·利比(Abu Yahya al-Libi)认为,“‘不信道者’对伊斯兰国家的统治是一种灾难,是魔鬼的大门,也是最终的磨难”,“容忍‘不信道者’对穆斯林领土的统治是一种变节行为,是最原始的异端行为,应被视作一种堕落,‘信道者’不管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或遭受多大麻烦,都应该推翻‘不信道者’的统治”。*Mohammed Hafez, “Takfir and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p. 32.
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人体盾牌”(Qatlal-Turse)的辩护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教义学家阿卜杜拉·古尔图比(Abdullah al-Qurtubi)的论述。古尔图比认为,只要有利于打败“异教徒统治”,使用自杀性袭击手段便是被允许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原头目扎卡维对古尔图比的解释尤为推崇,他认为“异教徒统治者”通常混杂在穆斯林民众中间,在铲除“异教徒统治者”时难免会对穆斯林同胞造成伤害;对于穆斯林而言,终结“异教徒”对自己领土的占领所带来的整体收益远大于牺牲穆斯林个体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该鼓励穆斯林使用“人体盾牌”、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成就“大业”。*Ibid., p. 37.这种逻辑使得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伊拉克频繁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
2006年扎卡维被美军炸死后,马斯里(Abu Khabab al-Masri)接任“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该组织成为2014年兴起的“伊斯兰国”组织的前身。“伊斯兰国”组织在意识形态上采用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核心理念,并以此作为开展暴力恐怖活动的宗教合法性依据,开展了震惊全球的暴力恐怖活动和“建国”行动。
六、 结 论
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本质是将“圣战”作为履行宗教功修和道德承诺的绝对义务,鼓吹回归伊斯兰初创时期的宗教与社会传统,运用暴力手段消除社会中的一切“非伊斯兰”因素,打击“异教徒”和“叛教者”,以此实现所谓的“净化伊斯兰教”和“复兴伊斯兰教”的目标。中世纪伊本·泰米叶的理论为当代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后世伊斯兰极端主义理论家对伊本·泰米叶理论的选择性运用和改造,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运用暴力手段打击异己的宗教合法性。在战乱频仍的中东地区,从“圣战”分子抵御苏联入侵阿富汗到海湾战争,再从伊拉克战争到“阿拉伯之春”后的利比亚乱局、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兴起,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国际政治互动的产物,圣战萨拉菲主义始终在激化地区冲突与暴力恐怖活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逐渐成为各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思想基础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