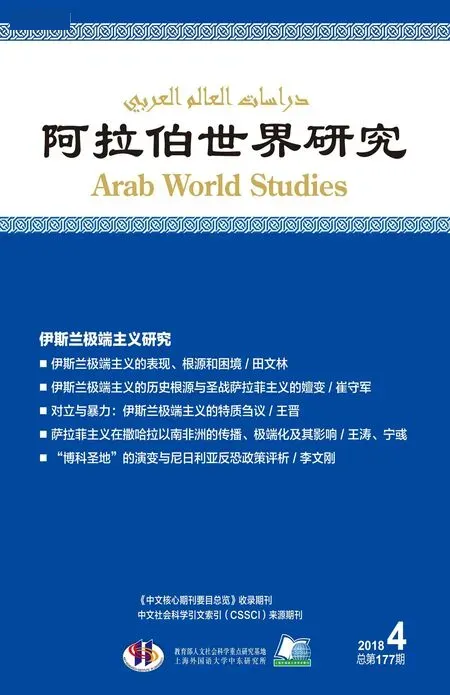伊拉克战争后沙特与伊朗关系探析*
韩小婷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传统地缘政治和各派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由于沙特和伊朗都力图独占中东鳌头,谋求在中东的话语权和海湾地区主导权,导致两国在诸多问题上推行对抗政策,从而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伊拉克战争后沙特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博弈,充分展现出中东政治扑朔迷离和纷繁多变的发展态势。
一、 伊拉克战争前的沙特和伊朗关系
现代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实质性交往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沙特王室与巴列维政权联手,共同抵御反对封建王权和主张泛阿拉伯主义的埃及纳赛尔政权。*关于这一时期两国的关系,参见Faisal bin Salman, Iran,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 Power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ondon: I. B. Tauris, 2003。1968年英国从海湾地区撤离后,美国为填补在该地区的权力真空,对海湾地区奉行所谓的“双柱政策”(Twin Pillar Policy)。美国的这一政策力图借助各种手段将保守而亲美的沙特和伊朗巴列维政权作为合作伙伴,遏制当时中东地区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抵御苏联在该地区不断拓展的影响。截至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沙特和伊朗之间一直维系着蜜月般的合作关系,同时扮演着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代理人的角色。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改弦易辙,同美国反目。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对外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猛烈抨击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政权,煽动沙特民众推翻“非法的”沙特王权,导致沙伊关系迅速逆转。同年11月,沙特国内接连发生宗教极端派武装占领麦加大清真寺和东方省什叶派穆斯林骚乱事件,这两起事件的背后都有伊朗因素的影响。在随后爆发的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始终站在伊拉克一边,向萨达姆政权提供各种支持和援助;伊朗则通过支持中东和海湾地区各类反政府什叶派团体和组织来扩大自身影响,这些组织包括“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或Hizbullah)以及活跃在海湾地区的其他真主党组织。每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也为伊朗提供了另一个极为敏感的舞台,使之能够借助伊朗朝觐者的激进言行表达对沙特王室的不满和抨击。1987年麦加朝觐期间,爆发了一场针对沙特政府的骚乱。由于450多名伊朗朝觐者在冲突中丧生,*Shahram Chubin and Charles Tripp, “Iran-Saudi Arabia Relations and Regional Order,” Adelphi Paper, No. 304,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Oxford Universiyty Press, 1996, p. 17.导致此后沙伊断交达三年之久。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出于维护国内安全和巩固政权的考量,沙特在求助美国提供保护的同时,开始缓和同伊朗的关系。沙特方面认为,伊朗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国力和军力急剧下滑,已不再对利雅得构成直接威胁。在伊朗,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其内政和外交出现悄然变化。伊朗新任总统拉夫桑贾尼主张,海湾国家应摆脱对外来势力尤其是对美国的依赖,任何地区性安全协议都应排除美国的介入。*Henner Fürtig, “Conflict and Cooperration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Interregional Order and U. S. Polic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4, 2007, p. 629.他还特别强调伊朗在海湾地区实施睦邻政策。1991年年底,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对德黑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哈塔米时期得到进一步改善。哈塔米主张在对伊斯兰文明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寻求伊斯兰文明下的政治发展道路,并相信伊朗完全可以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伊斯兰民主政治。为实现这一目标,哈塔米对内倡导建立“公民社会”,对外强调“文明间对话”。实际上,这也是哈塔米对其内外政策核心内涵的高度概括。就外交而言,他试图借助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使伊朗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进而发展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哈塔米在外交上对海湾国家的主要突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坚定地奉行拉夫桑贾尼所开启的缓和与睦邻政策,积极推动同海湾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促进彼此间关系的发展;二是他有效改变了伊朗长期固守的发展同海湾国家睦邻关系,要以美国从海湾撤军为前提的政策。*Ray Takeyh, Hidden Iran: Paradox and Power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London: Turnaround, 2007, p. 68.时任伊朗国防部副部长、阿拉伯裔伊朗人阿里·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是执行哈塔米这一政策的重要人物。他流利的阿拉伯语不仅增强了伊朗承诺改善同邻国关系的可信力,同时也帮助他和许多海湾国家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1999年,哈塔米在热烈气氛中访问了沙特的吉达。随后,沙伊又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签订了一系列地区和安全协议,其内容涵盖反恐、反洗钱、打击贩毒和非法移民等。*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21.在哈塔米执政的8年中,伊朗逐渐摆脱了外交窘境,并同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自20世纪60年代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沙伊关系的发展演变充分反映了外交与内政互动关系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沙伊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起伏和亲疏变化取决于双方国内的政局动向与利益诉求的不断更替,以及由此确定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当沙伊两国彼此追求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一致并互有所求时,两国关系便有了共同合作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反之,两国关系就会彼此戒备和敌视。从本质上讲,沙伊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双方在不同时期利益的博弈较量或权衡妥协的产物。
二、 伊拉克战争后影响沙特和伊朗关系的若干问题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中东地区又陆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对伊战后中东格局的不断变化,沙伊都急于充当中东伊斯兰地区的主导者。沙伊较量的实质是两个区域性伊斯兰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政治制度、地区话语权、教权和势力范围之争。伊朗视沙特为美国的代理人和美国打压伊朗在海湾势力的工具;沙特则担忧伊朗实力的迅速上升及其称霸海湾的野心,更畏惧伊朗在战后伊拉克的影响骤然膨胀以及谋求核力量的决心。*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9.故此,伊战后的十余年来沙伊两国围绕海湾和中东地区的诸多敏感问题折冲樽俎、明争暗斗,彼此都试图影响乃至掌控海湾和中东政治的走向。概括说,沙伊关系的矛盾和斗争主要围绕六大问题展开。
第一,沙特国内的什叶派问题。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权之争一直是伊斯兰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困扰沙伊关系的重要因素。伊朗什叶派人数约为7,280万,*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估算。参见《伊朗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2月1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72/1206x0_677174/,登录时间:2018年4月7日。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而沙特以正统逊尼派的罕百里教法学派为国教,什叶派为少数派。海湾地区已探明石油储量的一半左右处于什叶派聚集区,对中东和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沙特什叶派主要居住在波斯湾西岸东方省的哈萨和卡提夫等地,占沙特总人口10%左右,约为270万。*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北京:三联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它是海湾地区除伊拉克之外最大的阿拉伯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地,也是沙特石油的主产地,什叶派穆斯林构成了沙特石油工人的主体。
由于教派分歧,什叶派穆斯林在沙特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是阿拉伯什叶派中受歧视最严重的群体。尽管什叶派信徒为沙特的石油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这激起什叶派信徒的怨恨。什叶派信徒成为沙特社会中的反对派之一,并成立了包括沙特“改革运动”(Reform Movement)、“希贾兹真主党”(Hizbollahal-Hejaz)等在内的各种反政府组织。伊朗作为什叶派国家,受益于伊战后中东地缘政治和战略均势的新变化,地区影响力迅速上升。伊朗试图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什叶派势力圈,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海湾各国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沙特对伊朗的渗透及其对东方省什叶派或明或暗的支持始终持戒备心理。因此,沙特的什叶派问题是沙伊关系的一大障碍。
第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问题。海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决定了地处海湾的沙特和伊朗两国都将其视为核心利益区,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遏制和削弱对方。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围绕海湾权力的争夺由来已久,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即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在综合国力上同伊朗相比处于劣势。为了抗衡伊朗,在沙特的倡导下六国的联合应运而生。1981年5月,在两伊战争初期成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其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带有抵御强邻伊朗和伊拉克扩张的明显意图。但海合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尽管海合会成员国在对内政策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但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涉及伊朗的问题上,却因战略考量与利益不同往往存在明显分歧,并造成成员国间的不团结和对伊朗政策的多样化。在伊朗问题上,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同沙特的立场基本一致,但各方仍有自己的小算盘。例如,阿联酋在经济上同伊朗关系密切,它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迪拜的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家族也都有伊朗血统,再加上阿联酋的伊朗移民接近50万,*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58.阿联酋在沙伊关系中实际上扮演着“中间人”和“平衡者”的角色。
卡塔尔与伊朗的关系更为接近。卡塔尔曾是唯一抵制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决议的国家。*“Security Council Demands Iran Suspend Uranium Enrichment by 31 August, or Face Possible Economic, Diplomatic Sanction,”United Nations, July 21, 2006, https://www.un.org/press/en/2006/sc8792.doc.htm, 登录时间:2018年2月7日。同时,卡塔尔在外交上特立独行,不时彰显与沙特对外政策的疏离,甚而置沙特于不顾,擅自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成为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所在地。卡塔尔与沙特的逆向而动,最终导致2017年6月5日沙特向卡塔尔摊牌,联合埃及、巴林和阿联酋等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破坏地区安全以及与伊朗结盟等为由与其断交,并共同对卡塔尔实施禁运和制裁。6月22日,沙特进一步向卡塔尔提出通牒式的恢复关系的13点要求。而卡塔尔的强硬态度使沙特与卡塔尔的关系至今仍未恢复。
阿曼也和伊朗长期保持紧密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缘于20世纪70年代阿曼因镇压南部省份佐法尔叛乱而被其他阿拉伯盟友抛弃。当时,阿曼和伊朗签订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边界协定。直到现在,阿曼—伊朗联合军事委员会一直定期会晤,讨论双边安全问题。阿曼军方认为,阿曼在沙伊之间发挥着潜在外交“桥梁”作用。*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52.此外,阿曼还一直拒绝介入针对伊朗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集体安全措施,并认为它是沙特攫取海湾事务主导权的“一种虚伪的阵线”。*Joseph A. Kechichian, Oman and World: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95, pp. 66-67.阿曼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主要是担心沙特在海合会内独自坐大称雄,力图借助伊朗掣肘沙特势力的上升。海合会国家不同程度的疏离倾向则为伊朗实施纵横捭阖的外交运作提供了可利用空间。
伊拉克同为沙特和伊朗的邻邦,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逊尼派在伊拉克的统治地位宣告终结。原来一直受打压的伊拉克什叶派通过全国大选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战后伊拉克政府的主导者。伊朗早在萨达姆时代便长期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反对派,两者关系极为密切,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的影响不言而喻。沙特担心掌权后的什叶派力量迅速膨胀,而他们同伊朗的特殊关系必然导致伊朗在伊拉克的话语权倍增。两股什叶派势力的合流将对沙特的安全及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构成威胁。实际上,掌权后的伊拉克什叶派确实在强化同伊朗的关系,而伊朗则通过向伊拉克萨德尔运动的“马赫迪军”和“伊拉克正义者联盟”等组织提供各种支持来加大对伊拉克的渗透。*Marrisa Cochran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adrist Movement,” Iraq Report, No. 12,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January 2009, pp. 18-21,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Iraq%20Report%2012%20Sadrist%20Movement%20Fragmentation.pdf, 登录时间:2018年5月8日。
第三,黎巴嫩政局和巴以问题。黎巴嫩的权力斗争和巴以问题是中东政治中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伊拉克战争后,沙伊两国在这两大问题上持续角力。但由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与沙伊两国均不接壤,沙伊都采取代理人策略施加影响。
黎巴嫩是一个由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组成的多教派阿拉伯国家。教派和家族林立是黎巴嫩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为外来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伊朗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开始介入黎巴嫩事务,支持建立了黎巴嫩真主党,使后者的政治参与打上了鲜明的伊朗烙印。2012年2月,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曾公开承认,“自1982年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切可能的形式,给我们以道义、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Frederick W. Kagan et al., “Iranian Influence in Levant, Egypt, Iraq and Afghanistan: A Report b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May 2012, p. 38,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IranianInfluenceLevantEgyptIraqAfghanistan.pdf,登录时间:2018年3月10日。伊朗全力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势力迅速扩大,并在黎政坛举足轻重,实际上已成为体现伊朗意志的工具。为了反制和抗衡伊朗的渗透,沙特选择黎巴嫩逊尼派的拉菲克·哈里里家族及其派系作为长期的合作盟友。双方的争夺一度趋于白热化。
在巴以问题上,伊朗清醒地意识到在亲美的阿拉伯海湾领导人与强烈反美的民众之间存在罅隙。伊朗希望与各国的什叶派构建一种均衡的关系。为淡化什叶派色彩,德黑兰不仅寻求它在阿拉伯民众中的声望,并且尽可能缓解海湾统治者对伊朗在阿拉伯民众中影响不断上升的不安。伊朗实施了一种所谓“阿拉伯街区战略”(Arab Street Strategy),这一战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抨击沙特政权是美国的忠实走卒,并以此诟病其“合法性”,呼吁阿拉伯民众反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二是将巴以问题作为关键因素,强调伊朗在巴勒斯坦事业中的责任。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曾公开宣称巴勒斯坦是“我们肌体中的一个细胞”*Shaul Shai, The Axis of Evil: Iran, Hizballah, and the Palestinian Terro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p. 149.,并通过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各种支持,竭力将沙特等阿拉伯政权置于阿拉伯民众的对立面。因而伊朗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了“比阿拉伯人更阿拉伯的”策略来“打破什叶派的局限”,并扩大其影响。*Morten Valbjørn and André Bank, “Signs of a New Arab Cold War: The 2006 Lebanon War and the Sunni-Shi’i Divide,” Middle East Report, No.242, Spring 2007, p. 23.这也是伊朗的一种以守为攻的策略。
沙特是在伊斯兰旗帜下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沙特呼吁联合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力量抗击以色列的侵略扩张。但这一主张背后也蕴含着巩固沙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并确立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话语权的动机。*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沙特政府不断向巴解组织提供大量财政支持。2002年,时任沙特王储的阿卜杜拉代表沙特政府曾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力图使巴以冲突能够沿着它设计的轨道发展。伊战后,沙特继续加大对巴的财力支持。但沙特同伊朗支持下的哈马斯之间存在矛盾,不断抨击哈马斯拒绝将黎真主党视为“恐怖组织”。近年来,为了抑制和打压不断扩大的伊朗势力,沙特甚至悄然与以色列走进,策划反伊朗的沙特—以色列—美国轴心。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后,沙特的“暧昧”立场与伊朗所持的坚决反对态度形成强烈反差,这使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伊朗的竞争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第四,叙利亚内战问题。叙利亚是由隶属什叶派的阿拉维派长期掌权的国家,阿拉维派在叙利亚为少数派,仅占全国人口的11.5%,约为200万人。*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估算。参见《叙利亚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3月1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00/,登录时间:2018年4月7日。自1970年以来,阿拉维派的阿萨德家族一直控制着国家党政大权。在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是为数甚少的坚定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不仅如此,叙利亚还长期为伊朗给予黎巴嫩真主党的各种军事和财力援助提供重要通道。这一切都为叙伊两国的牢固关系奠定了基础。2011年3月,在“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叙利亚政局动荡,形成了以巴沙尔为首的政府军和以“叙利亚自由军”为首的反对派武装两大阵营,巴沙尔穷于应付外部势力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多条战线发起的进攻,其政权岌岌可危。伊朗作为巴沙尔政权的同盟,全力支持巴沙尔政权。伊朗担忧巴沙尔政权一旦垮台,将会导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叙利亚逊尼派夺取国家政权,并与沙特结盟,采取敌视伊朗的策略。因此,伊朗慷慨解囊,先后向巴沙尔政权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以及大量的原油补给。同时,伊朗还提供了一系列常规性和非常规性的军事援助,以便维系巴沙尔政权的存续。此外,伊朗还帮助叙利亚组建了一支50,000人的被称为“民兵”的准军事组织,以配合叙政府军作战。*Frederic Wehrey and Karim Sadjadpour, “Elusive Equilibrium: America, Iran, and Saud Arabia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6, 201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5/22/elusive-equilibrium-america-iran-and-saudi-arabia-in-changing-middle-east-pub-55641,登录时间:2018年1月5日。沙特则对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给予各种支持,期盼叙反政府武装推翻巴沙尔政权,借此削弱伊朗在黎凡特地区,甚至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势力,使沙特最终占据地缘政治的优势地位。
第五,沙特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问题。也门与沙特南部接壤,素有沙特“后院”之称。1934年沙特与也门曾因阿西尔低地归属问题而爆发战争,也门兵败后被迫与沙特签订《塔伊夫条约》,将阿西尔划入沙特版图。1962~1970年,为抵御新生的也门共和派力量渗入沙特,沙特支持的也门王室派与埃及支持的共和派之间经历了长期的内战。这些史实都说明了沙特极为重视也门政局变化对它的影响。伊战后,也门国内以部落势力为基础的胡塞武装崛起,并与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取代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哈迪政府分庭抗礼,而哈迪政府得到沙特的鼎力扶植。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哈迪政府被迫逃往亚丁。为挽救垂危中的哈迪政权,2015年3月,沙特以哈迪政府之邀和2009年《利雅得宣言》为由,组织阿拉伯联军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军事行动持续至今,但战事并未朝着沙特预期的方向发展,双方陷入胶着和拉锯状态。
胡塞武装属于也门什叶派分支载德派,它与也门逊尼派穆斯林大致各占也门人口的一半。沙特认为胡塞武装是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并得到伊朗及其资助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而国外的一些评论家则将沙特和伊朗在也门的争夺视为“地区性冷战”,它不是在军事上的抗衡,而是政治上的较量,彼此都渴望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Mabjoob Zweiri, “Iran and Political Dynamism in the Arab World: the Case of Yemen,”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5, No. 1, 2016, p. 4.实际上,也门问题不过是沙伊在海湾激烈争夺的筹码。沙特处于主动和攻势,伊朗处于被动和守势。处于守势的伊朗希望能够抓住也门战事这一时机削弱沙特。*Alireza Nader, “Yemen: Victim of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The Arab Weekly, May 8, 2015, p. 2.
第六,变化中的伊朗核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伊朗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从事核能开发活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由于外交上的孤立,且强邻环伺,加之西方国家的制裁,伊朗力图以发展核力量来缓减各方压力。2002年,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由,重启铀浓缩活动。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伊朗重启铀浓缩活动旨在发展核武器,是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威胁。为迫使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西方国家要求联合国加强对伊朗的制裁,美国甚至扬言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沙特起初虽然坚持中东无核化,反对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坚决支持国际社会通过多种措施制止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但它并不支持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沙特担心军事打击伊朗在海湾造成的后果可能更具破坏力,同时也将打破现存的地区安全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讲,沙特当时在伊朗核问题上似乎更倾向于充当“调解人”的角色。*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p. 67-68.然而,2015年7月六国与伊朗经过长期谈判签署伊核协议后,沙特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沙特认为,伊核协议对伊朗铀浓缩活动的限制有限,不足以彻底挤压伊朗重启核活动的空间;而伊朗从伊核协议中获得的各种好处过多,再加上伊朗的影响在“阿拉伯之春”后不断扩大,因此,沙特政府对伊核协议深感不安。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一改奥巴马时期制裁与谈判相结合的政策。2017年10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对伊朗核协议不会做出认可,指责核协议存在严重缺陷,要求相关部门和国会修改《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等。沙美态度的变化成为伊朗核问题的一大变数,亦将影响未来沙特与伊朗的关系。
除上述六大问题外,还有一个影响未来沙伊关系的潜在因素,即两国在石油政策上的分歧。沙特的石油政策在总体上着眼于全球石油市场的长期利益,并向美国和西方的石油需求倾斜。它在欧佩克内和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中发挥平衡作用,旨在确保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努力维持温和、适中的油价,避免因油价的大起大落冲击世界经济。伊朗与沙特不同,伊朗更倾向于通过限制石油产量实施高油价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石油利润。但由于伊朗2002年后受到美国和西方更严厉的制裁,石油出口和经济面临重重困难,所谓的“限产保价”政策只有在其石油产量完全实现正常化后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届时伊朗才能拥有抗衡沙特现行石油政策的能力。因此,石油政策上的分歧至少在目前还不是影响两国关系的要件。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本文对此不作探讨。
三、 沙特和伊朗关系的基本特点及未来走向
伊拉克战争后,沙伊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取决于构成双方国家战略利益的各种综合要素,同时也受制于海湾和整个中东乃至国际形势的影响。对沙伊关系嬗变的基本特点和未来走势,既要从影响当前双方关系的六大问题来解读,又要将地区和外来因素特别是大国的介入作为评估两国未来关系的重要依据。由于影响沙伊关系的六大问题在双方交往中存在轻重缓急或主次矛盾之分,因而需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层次梳理和分类比较来总结其特点。
沙特和伊朗都将海湾地区视为各自的核心利益区,彼此倾全力谋求在海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借助各种可利用资源来遏制和打压对方势力的上升,从而确立自身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优势,实现维护最高国家利益的目标。这是伊战后沙伊关系的第一个特点。出于确立海湾优势和主导海湾事务的需要,沙伊围绕各自的海湾政策及其对海合会成员国的争夺会不断激化。伊朗将采取各种挖墙脚的措施从政治上强化卡塔尔和阿曼在海合会内的离心倾向;利用它对大、小通布岛和穆萨岛的主权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同阿联酋的密切联系,运用施压和安抚拉拢的双重手段诱使阿联酋向伊朗靠拢;还将借助巴林什叶派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优势及其反政府的立场,对巴林王室和沙特制造更多的麻烦。伊朗针对不同对象国实施的策略旨在分化海合会的内聚力,削弱其整体实力,并在海合会内部埋下滋生矛盾的隐患,从而使其能够在同沙特的争夺中占上风。而沙特将通过各种反制手段打破伊朗削弱海合会的企图。例如,沙特会利用伊朗对巴林和阿联酋的领土要求所激发的阿拉伯民族情绪,加深强化巴林和阿联酋对波斯人的敌意和拒斥。同时,沙特还将借助海合会的内部机制巩固和强化其内聚力,使沙特同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的各种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2017年6月,沙特联合埃及等四国对卡塔尔鲁莽地实施禁运和制裁,反映了沙特力主绝对掌控海湾话语权,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杂音”的强烈意志。
沙伊两国在“什叶派新月带”的争夺,构成沙伊关系的另一对主要矛盾。双方在新月带的博弈尤其是暗中角力将会是一种常态,但不排除双方也会根据时空和事态的变化,促成两国关系在该地区的局部性或间断性缓和,这是伊战后沙伊关系的第二个特点。由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共同组成的所谓“什叶派新月带”是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的基本盘,也是伊朗施展影响力的主要管道,因而自然也是伊朗命运攸关之地。伊朗向该地区的什叶派组织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支持和帮助,以确保和巩固自身的地缘政治和教派利益。沙特的选择是通过支持什叶派新月带的逊尼派势力来遏制伊朗。例如,沙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大力扶植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的反政府组织和反政府武装;在黎巴嫩的权力斗争中,沙特支持“3月14日联盟”竭力抗衡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3月8日联盟”。*“3月14日联盟”因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2005年2月遇刺,亲哈里里的派别于2005年3月14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反对叙利亚的示威游行而得名;“3月8日联盟”是指2006年3月8日黎巴嫩国内亲叙利亚的派别为感谢叙政府此前对黎的帮助所举行的游行活动而得名,该联盟包括真主党、阿迈勒运动和米歇尔·奥恩领导的自由爱国运动等派别。这被视为沙特和伊朗代理人之间的抗衡。*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79.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战后中东出现的一系列剧变,许多西方国家从地缘变化的视角认定伊朗什叶派有可能“崛起”,但事实上,这并非伊朗的主动出击和扩张,而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整体势力突然削弱的结果。伊朗长期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和打压,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将守势作为首选,其影响始终也未突破什叶派新月的基本盘。与此同时,伊朗在中东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也与传媒的渲染和人为地放大有关。
从长远看,沙伊的矛盾和较量尚未触顶,未来仍有升级的可能性。对伊朗阵营而言,什叶派集团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属于次国家行为体的整合,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尚不足以掌控国家的一切权力。而沙特阵营的逊尼派集团虽然多在本国执掌大权,但国家力量却处在不断的衰落和分裂中。这种态势显然限制了两个阵营冲突的手段与烈度。现阶段沙伊的实力大体维持均势,基本能够遵循斗而不破的原则,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概率不大。
在沙特的什叶派问题、巴以冲突、也门内战等次要矛盾方面,鉴于这些矛盾不会直接侵犯各自的核心利益,因而双方存在适度妥协的意愿,甚至一定形式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伊战后沙伊关系的第三个特点。作为次要矛盾,上述问题对于沙伊来说不像主要矛盾那么紧迫,因此可将它们视为沙伊两国核心利益争夺的延伸。双方都试图借助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动权来为自己加分。
以沙特什叶派问题为例,沙特什叶派在中东属于温和派,他们自称穆斯林,但并不刻意强调其什叶派身份,*Ibid., p. 74.而且决不听命于伊朗。他们只是反对沙特政府对其宗教信仰的歧视和限制,要求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伊战后,沙特政府采取各种举措加快与什叶派的和解。例如,加大对什叶派居住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解除对什叶派信徒的宗教限制,吸纳他们进入王国和地区政治协商机构等。对于沙特的怀柔与和解策略,伊朗只能坐观其成。2016年初,沙特政府以反恐为名断然处决了沙特著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伊朗政府对此强烈谴责,伊朗民众在沙特驻伊朗使馆前示威并纵火,最终导致沙特政府宣布与伊朗断交。实际上,处决尼米尔只是沙特对国内反政府势力的震慑,并不直接针对伊朗。因为被处决的包括尼米尔在内的47名罪犯均以违犯伊斯兰教法、参与暴恐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定罪。伊朗的反应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反制措施。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伊朗煽动沙特什叶派制造大规模反政府事端的可能性较小。
在巴以问题上,伊朗是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而沙特长期支持巴解法塔赫主流派。伊朗在2006年和2008年以色列先后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大显风头,并被西方传媒视为最大赢家。为扭转这一态势,沙特旋即通过承诺对战后黎巴嫩重建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以及支付黎巴嫩所有学生一年的教育费用来遏制伊朗在黎影响的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沙特又把伊朗作为谈判伙伴,力促两国在黎巴嫩各联盟之间达成一个权力分配的协议,以便提升沙特在黎巴嫩的影响。*Frederic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p. 80.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沙伊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闭门”的外交努力,两国的高官要员在德黑兰和利雅得不断进行互访,其中包括沙特班达尔亲王和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首脑拉里贾尼。*Ibid., p. 81.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问题上,两国仍有可能根据利益需要做出相应让步。
在也门问题上,尽管沙特一直将也门视为自己的后院,但也门国内的部落割据和教派因素,造成也门的整合与治理困难重重。沙特支持的哈迪政权更是危机四伏,这决定了沙特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也门,沙特联合多个阿拉伯国家对也门实施的长达三年之久的军事打击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使利雅得几度遭到导弹的袭击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伊朗作为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它对胡塞武装的有限帮助,也不可能使其在阿拉伯半岛扩大影响上实现重大突破。可以说,沙伊在也门问题上的较量没有明显赢家,也门不过是双方明争暗斗的筹码和牺牲品。*Alireza Nader, “Yemen: Victim of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pp. 1-4.也门问题的未来和解,仍离不开沙伊关系的缓和与彼此间的斡旋。
关于伊朗核问题,伊核协议是一个由多国长期谈判而签署的国际性协定。截至目前,该协议的执行得到了除美国现总统特朗普之外的签署国各方以及联合国的认可,伊朗基本恪守了协议的各项规定。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将对伊朗实施一系列最严厉的制裁。伊核协议的其他签署国和伊朗均表示仍留在协议内,并愿继续履行协议相关规定。但在美国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并对第三方采取连带制裁措施的条件下,伊核协议签署国特别是英法德,能否在伊朗继续履行协议后确保其应得权益和实惠,尚待静观。一旦伊朗认为它应得的权益和实惠无法兑现,它很可能被迫退出核协议,并重启铀浓缩活动。其结果必然使伊核问题又倒退至原点,从而在中东酿成新的危机。同时,它将严重冲击沙伊关系,促使两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由局部缓和重新走向对抗,甚至上升为两国核心利益之争的主要矛盾。
国际大环境和美俄的中东政策是评估未来沙伊关系变化的另一要素。伊战后,中东剧变迫使美俄的中东政策不断调整。总体上看,伊战后美国主导中东的大前提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不同区位和不同问题上美俄双方互有攻守,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中东政局和中东国家间的关系。换言之,伊战后美俄的中东政策同样对沙伊关系构成特殊影响。由于美俄在中东都竭力避免相互间直接的武力对抗,未来沙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会被限制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但相比较而言,伊朗占有一定优势。其原因在于伊朗内部的统治力和凝聚力强于沙特,加之什叶派集团多由次国家行为体整合而成,彼此之间的利益纷争和价值冲突比较少,伊朗则是可倚靠的盟主;而沙特目前君主政体的稳定性较弱,年逾八旬的萨勒曼国王2015年初登基后,在短短两年间两度更换王储,最终将自己年仅32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上王储之位,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上任后在内政外交上的各项超常和激进举措能否持续,并得到整个沙特王室和统治集团的认同,尚存不确定性。另外,以沙特为盟主的逊尼派集团经常被诸多内部问题所困扰,彼此利益冲突较多,沙特难以代表所有逊尼派力量的价值诉求,这些都不利于它同伊朗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