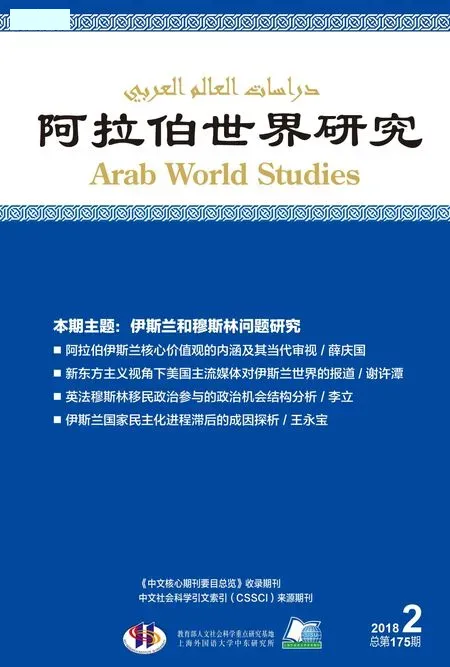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滞后的成因探析*
王永宝
长期以来,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不顺利,甚至在有些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后反而使社会治理恶化。2010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运动导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和叙利亚等国经历政权更迭或陷入长期内战,其溢出效应也波及土耳其和伊朗,从而引发学界对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以及对“伊斯兰教与民主能否兼容”的讨论。从更大范围来看,受教俗关系、政教关系、殖民统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伊斯兰国家目前民主化程度总体不高。本文认为,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滞后的成因主要包括“舒拉”协商制度解体和乌里玛阶层衰败、殖民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的影响、极端世俗化模式存在弊端、宪政体制趋于瓦解与议会制度面临失败,以及威权政体变异等。
一、 “舒拉”制度解体与乌里玛阶层衰败
如果说民主化的实质是公众在行使参政议政和对监督权力机构的权利,那么异曲同工的伊斯兰“舒拉”制度则强调国家和个人在宏观与微观事务方面的决策须经过所有相关者的磋商。《古兰经》要求穆斯林“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42:38)。*本文引用的《古兰经》经文均引自马坚先生的中文译本,参见《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尽管先知穆罕默德是天启的接受者,但真主还是命令他“当与他们商议公事”(3:159)。因此,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l al-Din al-Afghani)认为,根据“舒拉”制度,权力终属人民,在未得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统治者无权支配任何事务。*Muhammad al-Makhzumi, “Khatirat Jamal al-Din al-Afghani,” in Majid Khadduri, ed., Political Trends in the Arab World,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0.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其弟子艾布·伯克尔应众人推举成为国家领袖;其后,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成为继任者,后人称他们为四大正统哈里发,原因就在于他们行政透明,坚持“舒拉”制度且尽可能与他人保持意见一致,但绝非屈从于权势或不择手段地打击批评者和反对者。然而,自倭玛亚王朝起,哈里发制度被蓄意改为君主世袭制。这种政体不仅取代了“舒拉”制度,而且还使部分哈里发为压迫赋予合法性伪装甚至肆意操纵伊斯兰教,如关于前定相对自由意志的教义辩论等。虽然倭玛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替代,但“舒拉”制度并未得到恢复,而是依旧维持专制统治。不仅如此,在当时“维齐尔”(Wazir,大臣)和“库塔布”(Kuttab,书记官)的广泛影响下,依照伊斯兰教时代以前波斯帝国的君主制模式,阿拔斯王朝引入并形成了独裁政体和帝国体制,最终导致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这些军阀不甘心担任外省总督而自封为王,其中部分军阀在巴格达掌握实权、削弱哈里发的权力并逐渐使其沦为傀儡。这种状况在白益王朝(或译“布韦希王朝”)统治时期尤为突出。*参见[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上卷)第125-445页,(下卷)第634-644页。
为遏制内耗与加强民众的团结统一,阿里·本·穆罕默德·马沃尔迪(Ali bin Muhammad al-Mawardi)创制了一种“协议”,即哈里发承认篡权者对政策的控制权和对政府的管理权,作为回报,篡权者也对哈里发作为宗教事务领袖的权威给予认可。*Hamilton A. R. Gibb, “Al-Mawardi’s Theory of the Caliphate,” in Hamilton A. R. Gibb, ed., Studies on the Civilization of Isl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51-165.此后,这种“协议”逐渐被转化为“埃米尔控权制度”(Imaratal-Istila’)。至艾布·哈米德·安萨里(Abu Hamid al-Ghazali)时代,该“制度”已被广泛接受。作为伊斯兰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改革派学者,安萨里虽对该“制度”持批判态度,但迫于形势也只能妥协,其理由是伊斯兰法学中的“为势所迫”决定判断及其实践的合法性(Al-DharuratTubihual-Mahzurat)。*Abu Hamid Al-Ghazali, Al-Iqtisad fi al-I’tiqad, Beirut: Dar al-Kutub al-’Ilmiyyah, 1983, p. 151.然而,除顺应变革外,安萨里未曾考虑过,君主专制释放出了逐渐损害社会与国家整体结构且难以预料和控制的破坏力,因为该“制度”根本不具备吸纳其他良法善治的能力,所以安萨里所顾及的也只能是一再妥协。安萨里指出,就任哈里发职位,理论上有三种方式,即先知穆罕默德的任命、在任哈里发的任命、大众对某个在军事与政治上具有实力的个人或团体表示顺从的“选举”*Hamilton A. R. Gibb, “Al-Mawardi’s Theory of the Caliphate,” pp. 149-150.。但是,安萨里却只字未提“舒拉”制度可作为理论上潜在的第四种或首要方式,即统治者经被统治者选举产生。相反,安萨里却声明:“现如今就任哈里发职位完全取决于军权,因此(来自阿拔斯家族的)人,只要军权的掌握者对其公开表示效忠,那他便是哈里发……若军队的掌握者(军阀)公开宣称效忠哈里发……则所说的军阀作为一个合法苏丹理应予以认可,他的命令与裁决必须在王国各地得到遵从和执行。”*Al-Ghazali, Ihya’ ‘Ulum al-Din, 4th ed., Vol. 2, Beirut: Dar al-Khar, 1997, p. 110.
1258年,蒙古人入侵巴格达,推翻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政权。之后,马穆鲁克人在开罗建立了名义上的哈里发政权,并为武力夺取权力铺平了道路。确切地说,该道路是由马穆鲁克控制下的开罗最高法官伊本·杰玛阿(Ibn Jama’)铺平的。他指出:“为穆斯林大众的幸福安康与团结统一,(若)某人以武力手段和军权契约取得了伊玛目(国家领袖)权力,其后他人凭己之力和(掌控的)军队征服了前者,则前者便被废黜,而后者则将成为伊玛目。”*Hamilton A. R. Gibb, “Al-Mawardi’s Theory of the Caliphate,” p. 143.为支撑此观点,伊本·杰玛阿还引证了伊本·欧麦尔(Ibn ‘Umar)的著名格言“我们与胜利者同在!”(Nahnuma’aManGhalab)。于是,“舒拉”制度便被人为公开地废黜了。*Badruddin Ibn Jama’a, Tahrir al-Ahkam fi Tadbir Ahl al-Islam, 2nd ed., Qatar: Head Office, Shari’a Courts and Religious Affairs, 1987, p. 56.同时,“权力即权利”这一原则,也被当权者作为信条正式确立下来,而《古兰经》中关于“舒拉”的命令,则通常只会被当权者作为“座右铭”展示于会客厅的墙壁上。
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角度来看,“舒拉”制度的解体与乌里玛(‘Ulama,宗教学者)阶层的衰败有直接关系,因为穆斯林大众期望的乌里玛,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更是包括“舒拉”制度在内的伊斯兰法的捍卫者。安萨里留给后辈的警示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大多数乌里玛都沦为了“邪恶学者”(al-’Ulamaal-Su’),其表现是作为个人的乌里玛由于傲慢、贪婪、自私、虚伪而衰败,而作为整体的乌里玛阶层由于并未尽忠职守(即扬善抑恶)也同样失败。因此,安萨里认为,当乌里玛屈于世俗诱惑时,如对财富、权势的痴迷和追逐,就已沦为了腐败分子,而当他们被世俗的享乐诱入陷阱、走上歧途时,则履行自己应尽职责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甚至可能会变为犯罪分子。乌里玛尚且如此,何况那些王公贵族和当权者?以这样的统治者和乌里玛为典范,民众必然整体走向“灾难”而难以逃脱。*Muddathir ‘Abd al-Rahim, “Al-Ghazali’s Political Thought: Its Nature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Al-Shajarah, Vol. 11, No. 2, 2006, pp. 23-38.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学术界也随之急剧退化,尤其是伊斯兰法学的衰落加速了人们对“舒拉”制度的遗忘。而且自10世纪伊斯兰法“创制”(Ijtihad)大门的锁闭以及“仿效”(Taqlid)前辈的盛行,至19世纪,似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已普遍赞同追随某个法学派,而非曾经思想开明的学术和本着学术批判精神及实践原则对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持续的反思和更新。“有些人甚至更加离谱,他们不仅继续模仿这个或那个伊玛目……而且还仿效该法学派某个特定法创制者,例如马立克学派法学家哈利勒·本·伊斯哈格·君迪(Khalil ibn Ishaq al-Jundi),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某个特定创制者的偏爱,说明此人更胜于同一学派中的其他创制者。”*Ahmad Baba and Al-Timbukti, Nayl al-Ibtihaj bi-Tatriz al-Dibaj, Tripoli: Manshurat Kulliyyah al-Da’wah al-Islamiyyah, 1989, p. 171.在此氛围中,“创制”变得令人生厌,而“仿效”即便不是教义信条,也成了必须遵守的法规。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法学中,而且还渗透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因为根据“创制”的定义及其在早期穆斯林社会中进行实践的成功经验,发展是创新的果实,但穆斯林冷落“创制”和盛行“仿效”不可避免地导致“舒拉”制度的解体和传统伊斯兰文明的整体衰落。用阿尔及利亚思想家马立克·本·纳比(Malik bin Nabi)的观点来说,伊斯兰世界因此而沦为了适于列强开拓的殖民地。*Malik bin Nabi, Muzakirat Shahid lil-Qarn, Beirut: Dar al-Fikr al-Mu’asir, 1984, pp. 47, 319-320.
二、 殖民统治的结果与新殖民主义的影响
自13世纪后半叶起,伊斯兰古典文明开始走向衰落,因而伊斯兰世界在面对文艺复兴之后日益强盛的欧洲殖民者时完全丧失了抵御能力。令人深思的是,后者曾学习并受益于前者。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签订的《卡尔洛夫奇条约》导致伊斯兰世界进一步衰落。此后,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最亟需解决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应对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然而,由于此问题极为复杂,所以在被殖民的穆斯林团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分歧。例如,在被法国视为领地的阿尔及利亚,受法式教育的穆斯林在争取完全平等的同时也接受了同化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还于1912年组建了名为“青年阿尔及利亚”的政党。*John Voll, Isla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Syracuse: SUP, 1994, p. 220.但是,同化政策因伴随着对当地伊斯兰文化根基的破坏而遭到当地许多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界人士的强烈抵制。1936年,同化主义者代表法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在一次演讲中说:“若我发现了一个称为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我必将是这个国家的一名民族主义者。然而,我不会为这个阿尔及利亚祖国献身,因为这样一个祖国根本不存在……”*Muddathir ‘Abd al-Rahim, Bayn al-Asalah wal Taba’iyyah: Tajribat al-Isti’mar wa Anmat al-Taharrur al-Thaqafi fil Bilad al-Asyawiyyah wal Ifriqiyyah, Khartoum: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4-15.此后,“阿尔及利亚乌里玛协会”创始人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蒂斯(‘Abd al-Hamid bin Badis)回应阿巴斯的立场说:“我们研究发现,正如其他国家一样,阿尔及利亚这个伊斯兰国家具有宗教与语言的统一性,尤其是她那独具特色的文化与传统。的确,犹如其他国家一样,有些文化与传统是值得赞扬的,同时也有一些是应当远离的。最关键的是,这个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也不可能是法国,更从未渴望过要成为法国。她在语言、道德伦理、民族渊源和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完全有别于法国。”*Ibid., pp. 15-16.显然,巴蒂斯强调的是,阿尔及利亚具有的是伊斯兰特征,而非法国特征。因而有学者指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演变有效清除了同化主义者提出的“伊斯兰式世俗化个人主义者”的可能性。*John Voll, Isla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p. 222.
同样,在生活着大量穆斯林的印度次大陆*殖民时代的印度次大陆生活着大量穆斯林,印巴分治后,虽然独立后的印度不是伊斯兰国家,但伊斯兰教依然为第二大宗教;而巴基斯坦,包括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国,为伊斯兰国家。,1857年反英起义失败后,印度穆斯林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接受了英国具有支配地位的现实,而另一派则予以拒绝并继续寻求可替代方式。在亲英派穆斯林团体中,西化程度最高的是由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ed Khan)领导的团体。1857年起义前,艾哈迈德·汗不仅在与英国合作方面,而且在西方与伊斯兰思想一体化的立场上,以其忠实信徒的姿态公开亮相。他将许多西方作品译成多种印度文字,并对《古兰经》进行了注解,详述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并以宣传亲英政治思想为宗旨创办了“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学院”(Mohammadan Anglo-Oriental College)*John Voll, Isla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p. 112.。艾哈迈德·汗的多方尝试宁愿费尽周折求助西方思想,也不愿理会印度优秀的伊斯兰文化遗产。*Nikki R. Keddie, Sayyid Jamal ad-Din al-Afghani: A Political Bi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152-167.因此,阿富汗尼于1879~1882年在印度旅居期间对其予以了严厉批判。然而,尽管许多穆斯林对艾哈迈德·汗持保留意见,也有人对其提出的方案持绝对批判态度,但很少有人公开反对他或支持阿富汗尼号召的反英运动,因为受过教育的印度穆斯林当时还得依赖政府雇用,而且英印政府为制衡由印度教教徒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倾向于偏袒穆斯林,其实,英殖民者的最终目的是为挑起各宗教间和民族间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20世纪初,当反英情绪在穆斯林群体中再次被激起时,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开始公开表达了对艾哈迈德·汗及其方案的批判且毅然响应了阿富汗尼的反英号召,并与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英殖民统治者。*Nikki R. Keddie, An Islamic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Writings of 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54-154, 175-180.此外,当时印度还出现了新一代受现代西方教育的穆斯林,其中最杰出的是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伊克巴尔关于现代穆斯林的状况,特别是对“重构伊斯兰宗教思想”的思考极具魅力。尽管他赞赏凯末尔推行的土耳其世俗化模式的积极层面,但也毅然批判了凯末尔的极端世俗主义思想,因为欧洲的政教分离思想在伊斯兰教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不应当盲目引进和采纳。*‘Abd al-Wahhab ‘Azzam, Muhammad Iqbal: Siratuhu wa Falsafatuhu wa Sh’iruh, Lahore: Iqbal Academy, 1985, pp. 2-3, 234-235.
实际上,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其政治、经济、司法、教育以及文化体系经历了彻底变革,即使在成为民族独立国家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者仍停留于非常严重的心理奴役和文化隔阂状态中,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新旧殖民主义者的眼睛才能认知这个世界,包括认知自身及其传统。*[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3页。这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影响的具体表现,即以间接且更为隐蔽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从而将后者置于其控制之下,以便使之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并最大限度地榨取后者的财富。新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殖民统治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有学者指出,美国为其自身利益和霸权需要,通常会奉行双重标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民主问题上的两面性是借“民主”谋求霸权,又可以为霸权而抛弃“民主招牌”。*王林聪:《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及其前景》,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62页。因此,新殖民主义不仅给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并且还成了后者“民主化的障碍”。*丁隆:《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6期,第14页。
三、 极端世俗化模式的弊端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伊斯兰世界与世俗化相关问题需要理解世俗化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一,世俗主义形成于欧洲近代史的后期,在此期间,基督教教会与政权,以及教会与个别有现代思想的神父之间长期存在着激烈斗争,因而世俗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Muddathir ‘Abd al-Rahim, “The Islamic Tradition,” in William H. Brackney ed.,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Major Religions, London: Praeger, 2005, pp. 3-13.第二,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发展中,“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这一假设性推论使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至今仍具广泛影响的革命浪潮之中,即逐渐使人类脱离了传统宗教信仰,并使其只信赖理性、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西化与世俗化才是人类社会民主化的基本要素和先决条件。第三,以历史为本的理论研究方法来理解和处理社会与哲学问题的世俗主义理论,如今已被有效改变为一种无神论信仰。这种世俗主义以其各种形式与内涵,包括宗教怀疑论与激进无神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得到传播,特别是在前法国殖民地的伊斯兰国家,文化侵略与同化政策被视为是行政管理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宗旨和目标,甚至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几十年之后,极端世俗主义依然被视为是值得崇奉的基本信条。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和哈里发制度被废黜后的几十年中,世俗主义以各种形式在伊斯兰世界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被改造成了一个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极端世俗民族主义国家,因为他坚信,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即西方文明,一个民族要想进步,就必须成为这一文明的一部分。*Paul Dumont, “The Origins of Kemalist Ideology,” in Jacob M. Landau, ed., 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Leiden: E. J. Brill, 1984, pp. 38, 247.因此,凯末尔曾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推进西方化,其中包括清除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并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语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伊斯兰法也被西方法典所取代。*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85.
在埃及,阿里·阿卜杜·拉兹格(‘Ali’ Abd al-Raziq)主张,伊斯兰教关心的只是精神事务,与政治毫无关系。1936年《英埃条约》签订后,塔哈·侯赛因(Taha Husaein)在关于埃及文化前景的一篇文章中坚决主张全面接纳西方模式,“好的与坏的、甜的与苦的、引人注目的与令人厌恶的、值得赞扬的与应受谴责的,都一样”*Taha Husain, Mustaqbal al-Thaqafa fi Misr, Cairo: Muassasah Hidawi, 2012, p. 44.。此外,赛莱玛·穆萨(Salama Musa)出版了大量攻击传统阿拉伯文化的书籍,因为他认为这种文化贯穿着太多的宗教价值,并且还以凯末尔为榜样,积极推动以拉丁字母书写本民族语言的运动,因为这将对阿拉伯文化形成“一次大跃进”。*Muhammad al-Khayr ‘Abd al-Qadir, Al-Islam wa al-Gharb: Dirasah fi Qadhaya al-Fikr al-Mu’asir, Beirut: Dar al-Jil; Khartoum: Dar al-Sudaniyyah, 1991, pp. 58-63.同时,约瑟夫·卢森塞尔(Joseph Rosenthal,其主要支持者后来发展成为埃及犹太社团及其追随者)与其他人(大多数是本国的亚美尼亚与希腊少数民族)于1922年在埃及成立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共产党。同样,中东地区另一个共产党也主要是由犹太人与非穆斯林于1925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埃及共产党的最大成就则是吸收了一些苏丹学生为新党员,继而由后者成立了苏丹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是非洲与阿拉伯世界最大规模和最具影响力的共产党。*Muhammad al-Khayr ‘Abd al-Qadir, Al-Islam wa al-Gharb: Dirasah fi Qadhaya al-Fikr al-Mu’asir, pp. 59-60.
极端世俗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在伊斯兰世界的宣传工作主要由西化人士承担,其代表人物是伊斯玛仪·迈资哈尔(Isma’il Mazhar)和伊斯玛仪·艾泽姆(Isma’il Adham)。迈资哈尔通过在埃及创办的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等文献。*Majid Khadduri, Political Trends in the Arab World, pp. 57-58.受过俄式系统教育的艾泽姆,分别在土耳其和埃及成立了相关协会。然而,与宗教怀疑论有密切合作关系的极端世俗主义,受到了以伊斯兰为信仰与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包括已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穆斯林的强烈抵制,而且在看似已被无神论思想,极端世俗化和西化进程淹没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同时也伴随着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因此,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埃及穆斯林思想家和精英都试图重新诠释伊斯兰教,继而坚定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念。例如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Muhammad Husain Haykal)由于在伊斯兰思想领域著述颇丰而享誉世界,他于1935年首次出版的《穆罕默德生平》成为经典名著*该著作已由天普大学教授伊斯玛仪·勒吉·法鲁基译为英文,参见Muhammad Husayn Haykal, The Life of Muhammad, Islmail Raji al-Faruqi, trans., Kuala Lumpur: Islamic Book Trust, 2002.。同样,埃及著名思想家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Abbas Mahmud al-’Aqqad)以其代表作《伊斯兰教的民主》阐释了伊斯兰教与民主思想的关系,从而成为伊斯兰教最主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Abbas Mahmud al-’Aqad, Dimuqaratiyyah fi al-Islam, Cairo: Muassasah Hindawi, 2012, pp. 34-36.此外,随着有关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论争的深入,塔哈·侯赛因改变了其对埃及文化特征的原有立场,并创作了多卷以伊斯兰文化为题材的作品,而其他著名人士包括迈资哈尔和阿卜杜·拉兹格在内,则也都陆续响应了回归伊斯兰的趋势。
在伊朗,由于伊斯兰教既作为信仰又起到了政治改革的指南作用,所以西化知识分子提倡的怀疑论、无神论和多神论等思想均逐渐遭到了抵制。*Mehrzad Boroujerdi, Iran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The Tormented Triumph of Nativi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5.例如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Ahmad)先以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拥护者的姿态活跃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最终转变成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最重要的拥护者之一。艾哈迈德的代表作《无神论的西方》(Gharbzadegi,亦译为“西迷”)于1962年面世,而且还出现了多个英译本*Ali Mirsepassi,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Negotiating Modernity in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9.,如《西毒:一场来自于西方的瘟疫》(Occidentosis:APlaguefromtheWest)等。简言之,杰拉利把“西毒”界定为“生活、文化、文明、思想模式上无支撑传统、无延续历史和无梯度变化曲线事件的总和”*Mehrzad Boroujerdi, Iran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The Tormented Triumph of Nativis, p. 68.。艾哈迈德把民族的“无根性”状态描述成一种在环境中传播且易受感染的疾病,或者西化就是一种致使伊朗社会遭到“感染”并降低伊朗人民文化与生活价值的“病毒”。然而,艾哈迈德在批判那些抛弃自己文化和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们时,并未支持过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或情绪化反西方,因为西方思想与文明的某些方面对他的确具有吸引力。同时,他对于传统什叶派乌里玛阶层也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对较为缺乏“根基”的世俗化与西化精英而言,他仍坚持由传统乌里玛担当社会改革的领导者;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只是为了从殖民地掠夺资源,而且还想毁灭其语言文化、公序良俗、宗教信仰等。因此,伊斯兰教与什叶派乌里玛必然是伊朗抵制流行病“西毒”最为有效的“疫苗”。*Ibid., p. 72.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历史上第一个现代伊斯兰什叶派政权的成立对伊斯兰世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使人们对几乎被看作真理的“世俗化理论”产生了彻底怀疑。*Mohsen M. Milani,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 Boulder, Colo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8, p. 5.因此,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指出:“献身于西化不是民主的保证,而且伊斯兰法的应用也绝不是伊斯兰教内在独裁主义的证明。”*John L. Esposito et al., eds., Isla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0.
显然,穆斯林学者和知识分子以及许多曾是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其他主要来源于西方“主义”的拥戴者,对伊斯兰教的“再发现”已不再是个案,而是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一股明显且稳定上升的力量。因此,对于仍主张世俗化等同于民主化的人们来说,有些核心问题值得深思。首先,在伊斯兰世界,许多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政权、以强制方式推行的极端世俗化社会治理模式,是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伊朗的礼萨·汗及其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突尼斯的本·阿里等,这些世俗政体或领导者均缺乏民主精神,而且在当今类似政体与领导者中,也无任何迹象要超越所谓的“自由专政”状态。其次,实行极端世俗主义政策,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即便是在世俗主义发源地的西欧,政教分离的理论与实践也不一定走向极端,或者说西欧国家已认识到极端世俗主义的危害,所以就政治层面而言不断在世俗与宗教之间予以调和。这充分说明统治阶级在世俗主义与宗教思想之间给予积极引导,才是促使社会真正出现民主化的良策。最后,大多数世界性的宗教传统也都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运动,同时与之伴随的民主化运动也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而且并不关乎时间、地点,也不关乎政体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而是关乎民主化的实际进程。“不应在世俗与非世俗的世界观之间划界线,而是要在尊重与不尊重人类内在价值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世俗性或宗教性世界观之间予以区分。”*Katerina Dalacoura, Islam, Liberalism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Tauris, 2003, p. 39.因此,许多观察家和学者的结论是,伊斯兰国家的政体“必须是伊斯兰民主式的,否则只能灭亡”*John O’Sullivan, “It Must Be Islamic Democracy or It Will Die,” National Post, Nov. 11, 2003.,而且由于伊斯兰教面对民主主义体现出的灵活性和在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域中的有效性,以及伊斯兰民主本身的多样性,为了全球穆斯林的利益,有必要促进伊斯兰式民主的传播。*Noah Feldman, After Jihad: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Islamic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p. 38.
四、 宪政体制的瓦解与议会制度的失败
一个多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一直在思索和讨论人们关于历史、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然而,对这些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都被置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背景之下。在1867至1868年期间,哈伊尔丁·突尼西(Khayr al-Din al-Tunisi)撰写了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解国情最明确的道路》(Aqwamal-MasalikfiMa’rifahAhwalal-Mamalik)。他指出:“首先应激励那些满腔热忱和不屈不挠的政治家与宗教专家,尽最大可能去接受任何有益于伊斯兰团体及其文明繁荣发展的事务,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则是优秀的政府。其次,必须忠告穆斯林大众要谨防那些仍顽固紧闭双眼而不去观察什么是值得赞扬的、不去留意其他宗教信徒们的实践是否符合我们的宗法律事务的人们,因为在这些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即非穆斯林们的所有法律与规章制度都应被废止!”*Khayr al-Din al-Tunisi, Aqwam al-Masalik fi Ma’rifah Ahwal al-Mamalik, in Leon Carl Brown ed., The Surest Path: The Political Treatise of a Nineteenth-Century Muslim States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4.八年后,突尼西的思想受到了奥斯曼帝国最高维齐尔艾哈迈德·赛斐克·米泽特帕夏(Ahmed Sefik Midhat Pasha)的大力推广,并且于1876年由首次建立的议会政府颁布了第一部现代宪法,但该议会政府维持了约一年时间就宣告解体。随后埃及与波斯(现伊朗)分别于1881年与1905年成立的宪法政府,也未能逃脱同样短命的悲剧。
由于民族独立运动表面上的成功及其领导者们都渴望带着民族自决与自由逻辑进入各自国家的后独立时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许多阿拉伯国家(例如伊拉克于1921年、埃及于1923年、黎巴嫩于1926年、叙利亚于1928年)都采取了强制推行议会制的方式。但事实证明,这些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埃及、黎巴嫩和叙利亚建立议会制政府的尝试都相继以失败告终。苏丹1956年独立后首先推行的也是议会政体,但首次尝试的议会政府运行不到两年就于1958年11月宣告解散,后由易卜拉欣·阿波德(Ibrahim ‘Abboud)将军接管的军政府于1964年10月被民众运动推翻,其后恢复的议会政府又于1969年5月被加尔法·尼迈里(Ja’far Numairy)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并建立了第二个军政府,而尼迈里军政府于1985年4月被阿卜杜勒·拉赫曼·苏瓦尔·达哈卜(’Abdel Raman Swar al-Dahab)领导的政变推翻,其后恢复不久的议会政府又于1989年6月第三次被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Umar Hassan Ahmad al-Bashir)的现任政权推翻。
上述现象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都广泛存在。在许多以穆斯林为人口主体的国家,立宪政体与议会政府的失败原因错综复杂。首先,体制与组织的成功成长和发展缺乏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其次,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与政客倾向于将民主体制改造成寡头政治。再次,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采用西方制度方面缺乏成功的实证经验。最后,阿以冲突成为阿拉伯国家立宪与议会政体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连年不断的阿以冲突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一直具有毁灭与扭曲性的冲击,事实上阿拉伯军队于1948年耻辱性地被以色列挫败,是决定阿拉伯国家此后多年立宪与议会政体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从平民政治家那里接管政权的年轻军官受到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军政府最有可能恢复已是伤痕累累的民族骄傲,也最有希望实现人民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但最终却亲历了独裁带给他们的无限痛苦。*Laith Kubba, “The Awakening of Civil Society,”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and Daniel Brumberg, eds.,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xxiii, 29-30.
因此,无论伊斯兰国家采用了哪种政体,最后大都沦为了威权政体或独裁政体,而安全部队、警察与情报机构则成为各种政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要彻底控制政府组织和基层机关,而且还要完全控制教育、文化、媒体等各领域。冷战时期,民主在民族主义者和阿拉伯左翼人士眼中不仅是极其反动或一文不值的乌托邦意识,而且往往还会遭到他们的诋毁。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要提倡民主,也得等到阿拉伯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完成领土统一后。例如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将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统一解释为:“谁在所属国家中拒绝彻底消灭自我,有一天他将发现自己会被一个征服其祖国的同盟国毁灭。”*Elie Kedourie, Democracy and Arab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Frank Cass, 1994, p. 89.因而在埃及,为了对个人自由的支持者和对纳赛尔军管政权的批评者给予先发制人的打击,《国家行动宪章》包含了“对于自由的敌人,没有自由可言!”等具有挑衅性的声明。在利比亚和苏丹,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与加尔法·尼迈里参照纳赛尔主义建立的政体,对政治自由采取了同样的敌对姿态。此外,由于自由民主被统治者视为是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所以也遭到了全盘否定。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复兴党甚至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更为严酷的威权政体。在突尼斯,在其“终生”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Al-Habib Bourguiba)被取代后,新政府的路线虽不同,但政体却依然如故*Kamal Abu Jaber, The Arab Ba’ath Socialist Party: History,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7.,而且普遍存在的腐败堕落和政府压制伴随着广泛且肆意的侵犯人权行为,是整个阿拉伯国家政治的共同现象。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那些被关押在监狱或集中营里的人们(包括社会名流),也就不足为奇地成了统治阶级眼中的“极端分子”乃至“恐怖分子”,原因在于他们做出的政治抉择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如“埃及穆斯林协会”曾被统治者称为“定叛和迁徙组织”(Jama’ahal-Takfirwaal-Hijrah)。*Gilles Kepel,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The Prophet and Pharao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35-56.
五、 威权政体的变异
冷战开始以来,为赢得盟友和影响民众,西方国家自诩为民主的代言人。事实上,大部分西方国家出于自身战略与利益考虑而非民主原则选择支持各种威权或独裁政体。在1967年6月爆发的“六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军队被以色列第二次挫败后,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政体发生了戏剧性转变。这对该地区的军政府以及其他独裁政权产生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战败后阿拉伯国家议会政体解体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匮乏是阿拉伯国家遭到多次失败的主要因素,但此结果却为埃及总统萨达特颁布自己的“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而且的确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Muddathir ‘Abd al-Rahim, The Islamic Tradition, p. 109.然而,随着萨达特被刺杀,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民主自由”开始重新审视并严加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掀起的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几乎使“民主政体”国家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上升了3倍,而西亚北非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均未受到此次浪潮的影响。在政治权利方面,西亚北非不仅是世界上“自由”最少的区域,而且也是自1974年以来自由平均水平实际持续下降的唯一地区。*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and Daniel Brumberg, eds.,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p. ix.《经济学人》指出,阿盟22个成员国是全球范围内清一色实行寡头统治的国家。*“Freedom Calls at Last?” The Economist, Vol. 371, April 1, 2004, pp. 55-5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样指出,就政治参与而言,阿拉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由度最低的。*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4,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69/hdr_2009_en_complete. 登录时间:2016年11月7日。
面对不断增加的改革压力,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实行威权政体的伊斯兰国家逐渐衍生出一种“自由专制”的生存战略。*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and Daniel Brumberg, eds.,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pp. xiv, 35.通过接纳政治定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著名人士进入政府,新型威权政体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冠以合法和多元光环,而一些国家还形成了事实上的世袭模式。所有威权政体均被形容为“对异议和多元主义”持零容忍态度的政体,但为了“生存战略”的合法化,这些政体不得不促进并利用“多元主义”。例如在象征性选举和限制性政治参与中,有限的“自由”时常被用来抵消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执行紧缩措施时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阿拉伯威权政体在官方文件中至今仍保留着压制政策。*Laith Kubba, “The Awakening of Civil Society,”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and Daniel Brumberg, eds.,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p. xiv.
关于“威权政体”操纵民主运动,流产的《苏丹人权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可谓典型案例。苏丹“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于1989年6月30日军事政变成功后,为逐渐使社会正常化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其中部分政策涉及《宪章》的草拟工作。1993年11月,“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授权“过渡国民议院人权委员会”筹划起草《宪章》。该文件旨在以国民人权宪章的形式产生一份报告,使所有苏丹人民不分文化、宗教、政治倾向、种族背景,都能确认且赞同其中内容,其宗旨印证了伊斯兰教的著名格言:“真主将维护公正的国家,哪怕它是非伊斯兰国家也罢!真主不会对不公正的国家给予援助,即使它公开表明信奉伊斯兰教也罢!”*Taqiyi al-Din Ibn Taimiyah, Majmu’ Fatawa Ibn Taimiyah, Riyadh: Mujamma’ al-Malik Fahd, 1995, Vol. 28, p. 63.为获得国际认可,议长曾即时督促将该《宪章》作为苏丹官方文件送至联合国总部。然而,该《宪章》不久便销声匿迹或被人为搁置了。
同样,《阿拉伯人权宪章》(以下简称《人权宪章》)经阿盟多年辩论后于1994年才有眉目,但22个成员国无一正式批准过这部由自己拟定的《人权宪章》,这足以证明该组织成员国总体上对民主持有的消极态度。为挽回局面,阿盟经多次磋商草拟了一份《人权宪章》修正案,以便能在2004年3月29至30日于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上得到终审,但在此修正案进入议程前,会议就已宣告结束。1990年8月5日,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九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上曾声明要将《人权宪章》的修正案纳入《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开罗宣言》)。但其中模棱两可的措辞导致围绕《开罗宣言》的争论持续多年,并无果而终。此外,阿拉伯国家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由于来自以色列和美国连年不断的武装打击和对阿拉伯国家领土的侵占,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民主与人权的状况要比其他伊斯兰国家更糟糕、更悲惨。*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by Country,”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ttp://www.ohchr.org/EN/Countries/MenaRegion/Pages/MenaRegionIndex.aspx; Amnest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cerns: Palestine, Syria, Iraq, and Afghanistan,” https://www.amnestyusa.org/countries,登录时间:2016年11月8日。因此,“阿拉伯之春”以及随之中东发生的民主转型和变革,致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民众对民主化道路产生了质疑。例如在埃及,穆罕默德·穆尔西于2012年6月通过民主选举当选总统一年后,就被其亲自提拔的国防部长塞西罢免,自此埃及又重新回归于军权统治。
在威权政体编纂的各种法律文件中,虽然有时也会夹杂着一些在措辞上令人赞许的条款,但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受这些国家领导人欢迎的。实际上,在不同威权政体内部,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模式支配着整个民主化进程。因此,在国家、区域和跨区域层面,当政府机构所做的努力受到排斥时,当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个人与民间团体的偏爱和态度成为焦点时,不同的极端局面就会显露出来。有关调查数据显示,伊斯兰国家民众都极其重视言论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多党政治,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大多数穆斯林在其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对于拥护伊斯兰教和宗教领袖的突出作用表示支持。*Press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003, p. 4,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5/legacy-pdf/185. 登录时间:2016年11月8日。全球大多数穆斯林同样赞同伊斯兰教在民主治理体系中发挥突出作用,因为两者在根本上是兼容的。*Muqtedar Khan, “Islam and Democracy: The Struggle Continues,”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Vol. 20, No. 4, 2001, p. 68.类似趋势已存在于一些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其中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表现明显。民主社会尚未得到良好建设,但其领导者正通过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沿着民主化路线努力,而且这些领导者及其支持者们通常是从伊斯兰信仰中获取改革价值的实用主义者,而非那些在原始经文中寻找现成蓝图的保守主义者。*Muddathir ‘Abd al-Rahim, The Islamic Tradition, pp. 115-116.
六、 结语
客观而言,在许多伊斯兰国家,民众仍在推动民主改革和建设公正的社会治理体制。而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频繁受阻的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舒拉”制度的解体和乌里玛阶层的衰败致使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盛行,殖民主义者推行的同化政策以及穆斯林国家推行的极端世俗主义模式,加之新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国家策动政变、挑起内战、扶植傀儡,都致使其政体不断变异并对其民主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当今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威权政体及其既得利益集团,任何时候都不会情愿让那些长期被他们压制的民众参与国家治理。民主化进程导致的变革和转型是当今各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特征,但这些国家要想成功实现转型,仍取决于其所有党派对各种相关问题和事务的思考和理解程度,因为处于全球化时代,这些国家及其领导人注定要经历社会变革带来的各种严峻考验,并建立和增强基于本国国情的发展自信心,也唯有如此,伊斯兰国家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自身的发展前途,而不至于完全受制于外来势力的干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