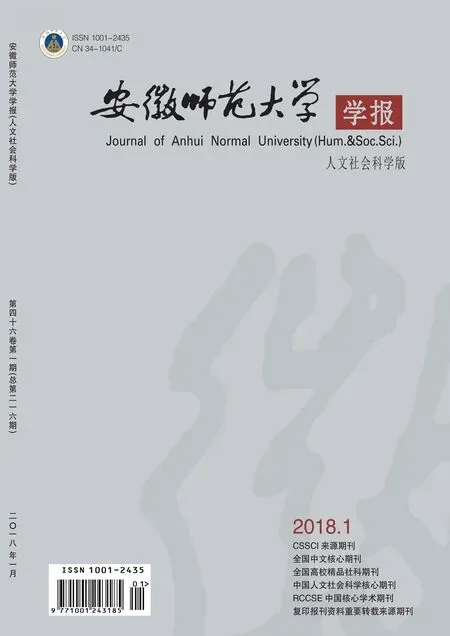社会治理视阈下西方警治模式的演变*
周凯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社会治理研究】
社会治理视阈下西方警治模式的演变*
周凯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警治模式;抗争政治;社会治理
西方警治历经的武力升级、协商管理、策略瓦解三种模式变迁,折射了西方国家抗争治理的理念转变。西方警治模式的发展既与西方社会“街头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又深受警察因素、抗争者因素、威胁性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中国社会的抗争治理虽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其警治行为中的模式演变、警察群体的角色定位、警治行为的法治保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近年来,各种抗争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抗争政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所谓“抗争政治”,是指普通民众联合起来对抗资本控制、权力精英、执政当局的集体行动,其形式涵盖革命、社会运动、示威游行、罢工抗议等。[1]2-6在抗争政治研究中,抗争者无疑受到了长期持续性的学术关注,其诉求表达、组织方式、动员策略、抗争手法等成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另一类人群也同样引发了学界的兴趣——这就是出现在每一次街头对峙之中并担当维护公共秩序职责的警察。
在西方,一旦游行示威或抗议行动爆发,警察担负着现场应对的法律责任,而其专业化处置抗争性集体行动的职业行为称之为“抗争警治”。在过去20年中,国内学界对西方抗争政治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探讨多从社会参与者的角度展开,对警治问题的关注相对不足。因此,评述西方警治行为的模式变迁和影响因素,对当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警察与社会治理
警察是实现统治阶级政治意志、维护统治秩序的强力手段和重要保障。从某种程度而言,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是警察行为的本质属性。“警察的限制实际上是代表国家对所有社会成员或组织进行规制、规范、约束直至惩罚……国家通过警察展现统治性、暴力性。”[2]56
随着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警察的暴力工具属性日趋隐性化,而其保障社会秩序、处理社会事务、服务社会需求的社会治理职能则愈发凸显。恩格斯曾指出,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523换言之,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其政治统治职能的重要基础,只有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及发展需要,政权本身才能稳固。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是国家履行其社会治理职能的核心机构,代表国家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维护公共安全、打击犯罪活动、展开紧急救助、提供便民服务等。特别是在西方社会,警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框架下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在其《基层官僚:公职人员的困境》一书中曾指出,诸如警察等处于社会治理最前线的公共权力使用者,虽然职级不高,却决定着宏观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基层官僚的即时决定、日常规则、应对不确定性和工作压力的手段,皆成为实际执行的公共政策。”[4]xiii如果忽视这一群体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政治家和决策者精心设计的政策或许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警察是国家和社会边界勘划中至关重要的连接点——它既为“国家-社会”互动提供秩序保障,又是国家与社会对话的重要媒介。一方面,警察作为国家的即时代表,必须对任何违背国家法律、政府法规及社会规范的行为实施有效处置,以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权威及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警察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的中介者,即在体现国家政治意志和坚持严格执法的同时,又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在现实中,警务工作往往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化解社会矛盾、打击犯罪行为,小到调解邻里纠纷、管理户口登记、处理失物招领等。作为国家和社会的连接点,警务工作客观上需要不断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紧张”,协调“法理情”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罗伯特·雷纳曾形象地将警察称之为“社会各种势力之间关系的调解者——‘一个街头角落的政治家’。”[5]105因此,警察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和理论探讨。
二、西方警治的模式变迁
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街头政治”。如何应对集体性的抗争行为、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成为抗争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抗争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绝非仅是一种政治环境或结构性背景,而是具备独立行为能力以应对抗争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必须将其视为独立一方展开深入研究。由于“国家”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多维的抽象概念,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将其具化(disaggregate)。在西方,警察被赋予了代表国家应对社会抗争行动、维护公共秩序的法定责任。西方警治经历了三种模式的发展与演变:即武力升级模式(escalated force)、协商管理模式(negotiated management)以及策略瓦解模式(strategic incapacitation)。
武力升级模式是西方国家应对抗争行动最早采用的警治模式。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警察在应对国内由于越南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时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处置方式——以强大压倒性的警力布置回应抗议人群的暴力行为或倾向。该模式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逐渐升级武力达到控制抗议人群、维护并恢复公共秩序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绝不姑息参与人群的任何过激行为或暴力举动。[6]371-389换言之,抗争者的暴力行为必然招致警察毫不留情的武力压制。然而,武力升级模式虽能快速有效地控制抗争行动,但却极易造成警察与抗议人群之间的暴力对抗,使得“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不断恶化。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国家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以暴制暴”的警务处置风格,寻找更为柔性的抗争治理方式。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协商管理模式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西方抗争警治的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例,警方改变了以往对待抗议群体和抗争行动的强硬态度,采取较为亲民的姿态,主动与抗议者协商对话,对策划中的抗议行动进行劝解疏导,对具体的抗议时间、地点、方式予以规范和限定。该模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充分沟通协商以实现对集体行动的有效控制,减小抗议活动对公共秩序的干扰和影响,并且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过激行为和暴力冲突。[7]总之,协商管理模式有助于扭转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警察充分尊重社会成员诉求表达的权利,民众亦理解和配合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所需。由此,双方开启了制度化的正向互动,降低了警民对抗的发生机率,形成了抗争治理的一种主导性范式。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愈来愈多的跨国界社会运动兴起。例如,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蔓延至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最终升级为全球性的“占领行动”。这些运动的核心组织者往往是匿名状态,通过现代通讯工具和社交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并迅猛扩展至社会各个角落,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产生极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一新变化,西方警治开始强调通过情报收集、提前预警以及空间控制等手段,在不侵犯公民表达权的前提下,倚重事前有选择性地使用武力而非事后惩戒性地处置违法行为,以达到维护公共秩序的最终目的,即所谓的策略瓦解模式。该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兼容了武力升级模式和协商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既策略性地运用武力(如使用非致命性武器、事先控制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超时或延期拘留、划定禁止抗议区域等),又保持与那些理性自律的抗议者进行及时沟通,以达成有效规制集体行动整个发展过程的最终目的。[8]636-652
西方警治的三种模式演变反映了抗争治理的理念转变。西方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历了基于价值理念诉求为标志的“新社会运动”,国家在应对民众表达非物质利益诉求的集体行动(如女权运动、同性恋身份认同运动等)过程中,逐渐从刚性强调社会秩序转向通过柔性协商互动来引导规范抗争行动。当全球化和新媒体带来愈来愈多的跨国界社会运动时,西方国家又开始采取抑制性策略以确保其社会控制力,即强调提前介入抗争行动的组织动员过程,对潜在的参与人群采取预防性的限制措施。总体而言,西方警治模式的变迁折射出其抗争治理的三种思维转变:首先,由武力威慑和强力压制转向将抗议活动纳入规范性的警务控制流程,实现由“堵”到“疏”的转变;其次,由封闭式单一治理模式转向开放式多元治理模式,即警察不再独揽维护公共秩序的重任,而是通过与抗议者协商互动达到共同对社会秩序负责的效果;第三,由被动式治理到主动式治理,强调利用情报收集、空间限制、预防控制等手段,对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或由社交媒体所发动的“去中心化”社会运动采取“先发制人”的规制策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三种警治模式在现实中依然被广泛运用。相对而言,协商管理模式和策略瓦解模式更为多见,而武力升级模式则是西方国家维护公共秩序的最后手段。例如,2014年美国弗格森小镇发生了非裔美国人组织的示威游行,当地警方通过不断升级武力的方式终止了这次抗议行动。此外,亚历克斯·维塔尔(Alex S. Vitale)分析了美国爆发过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十个城市所采取的警治模式,发现面对持有相似诉求的抗议人群,美国警察的处置方式极为不同:纽约市所采取的警治策略较为强硬,对任何违反法律规定和严重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均采取强制武力予以回应;相比而言,芝加哥、费城、波士顿、西雅图等城市则使用了较为温和的协商管理模式,通过与抗议人群事前进行充分沟通协商,确保了集体行动整个过程的可预见性和可控性;而洛杉矶、奥克兰等地采用了策略瓦解模式,对行动组织者及抗议活动的地域空间等进行了严格限制,最大程度上减小了集体行动对公共秩序的负面影响。[9]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在抗争警治实践中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那么,何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警治模式的运用与警治策略的变化呢?
三、影响西方警治模式的主要因素
警治模式的运用与警治策略的变化决非即兴发挥或随意“演绎”,而是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和内在逻辑性。概言之,影响西方警治模式及警治策略的主要因素有:警察因素、抗争者因素及威胁性因素。
(一)警察因素。所谓警察因素,是指警察及警务部门自身所具备的某种特质,如警察实力、警察知识、组织文化等,对警治模式选择构成了实质性影响。詹妮弗·尔海(Jennifer Earl)等认为,警察实力是制约警治行为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1968年至1973年发生在纽约州的抗议事件,他们发现具备较强警力配置和警务装备的警察机构往往并不急于压制抗议人群,而是倾向于在现场展示其“硬实力”,并辅之以协商劝说等方式平息事件;警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反而更倾向于通过升级武力(如更大范围内征调警员)来压制抗议者。[10]581-606另外,德拉波尔塔(Della Porta)提出了“警察知识”的理论解释,即执法者会自我总结职业角色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情况,并逐渐积累应对不同抗议人群及抗议方式的知识经验,从而形成其在抗争治理中差异化的警治行为。例如,西方国家的警察会对抗议人群进行标签化的“好”“坏”区分:“好”的抗议者通常是那些为了具体利益而参与行动的普通民众(如被解雇的工人、长期失业的妇女等),警察对这一类人倾向于采取比较温和的处置方式,甚至能够容忍其轻微地触犯法律;而所谓“坏”的抗议者则是指那些提出非物质性诉求或“职业化”的抗议群体,这些人受到某种抽象理念(如女权主义、绿色主义等)鼓动而走上街头,以破坏公共秩序为手段来引起媒体兴趣和社会关注,因而这一群体会受到警察较为严厉的管控和压制。[11]228-252此外,莎拉·苏尔(Sarah Soule)等学者认为,警察机构自身的制度特质及组织文化亦会对警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2]145-164例如,美国警察拥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且政治上保持中立,这种制度设计使得警察对于抗议行为相对宽容和耐心,然而美国警察又高度重视身处执法一线人员的人身安全,任何暴力行为容易引发执法部门的强力处置。
(二)抗争者因素。不同于警察因素,抗争行动参与者所具备的不同特质与禀赋差异也被认为是警治行为产生差别的关键诱因。一般而言,作为国家暴力工具的警察不会冒险尝试没有把握的强力行动——任何失败的压制,不仅是一次公开的“丢脸”行为,更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甚至危及政权的稳定。换言之,警察倾向于在抗议者比较“孱弱”、武力压制可以一蹴而就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运用武力终止抗争行动。那么如何界定抗争者是否“孱弱”呢?所谓“孱弱”(weakness),一般是指参与集体行动的群体不具备对政治体制进行惩罚或报复的能力。尔海等学者将抗议者的“孱弱”划分为两种类型:外缺性孱弱(weakness-from-without)和内生性孱弱(weakness-from-within)。[13]44-68“外缺性孱弱”是指抗议者无法寻求第三方力量(诸如大众媒体、社会精英、社会组织等)作为外部盟友加以依赖;“内生性孱弱”则泛指某一社会群体缺乏与政府实现有效沟通的制度渠道、关系网络及人脉资源。在抗争行动发生时,一旦抗议群体被标识为欠缺外部支持的“外缺性孱弱”,或与政治权力连通性不足的“内生性孱弱”, 则有可能遭遇警察的强硬对待。反之,当抗议者拥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或政治游说能力时,执法部门则会更加谨慎地权衡采用压制性策略的可行性与风险性,并倾向于运用协商管理模式或策略瓦解模式来妥善应对。因此,抗争者是否“孱弱”也成为影响警治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威胁性因素。随着抗争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愈演愈烈,警察在抗争警治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变数大大增加,其在现场处置中的威胁感知逐渐被视为解释警治模式变化的关键变量。杰克·古德斯通和查尔斯·蒂利(Jack Goldstone & Charles Tilly)曾指出,在抗争政治高度互动的演进过程中, “威胁”这一因素对深刻理解国家应对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威胁’是一个自变量,它自身的机制极大影响着冲突中抗议人群与国家的互动行为。”[14]181一旦集体行动对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冲击或对警治行动造成现实阻挠和安全威胁,警察势必使用武力予以终止。反之,当抗争政治的互动过程未对警察履职产生实质性威胁,则警治行为也会相对宽松。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将“威胁”视为客观因素,即抗争行动的某些特质天然性地具有威胁性,如规模大、组织程度高、抗议方式激烈、境外势力参与等;[15]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绝对“威胁性”的因素并不存在,所有因素都必须经过认知主体的识别和判定才有可能被赋予“威胁”标签,即任何因素都离不开执法者的主观感知、分析和界定。[16]换言之,所谓“威胁性”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和动态化因素,威胁与否取决于临场环境下警民双方的认知判断、政治信任与互动过程。
总之,警察因素、抗争者因素和威胁性因素被视为是影响当今西方社会警治策略变化和警治模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警察自身角度而言,其强制能力、警务经验及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区别是理解警治行为的主要维度;从抗争者角度而言,参与群体是否“孱弱”成为分析执法部门选择强力压制抑或沟通协商的解释变量;而威胁性因素则将警察因素与抗议者因素联系在一起,从临场互动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化地解读警治策略选择的理论视角。诚然,上述西方警治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政治文化背景,不能简单模仿或照搬,但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而言,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抗争治理创新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作为国家的暴力工具和公共权力的代表,警察不仅具有垄断性使用强制力的权力,而且掌握着是否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抗争行动的主动权和机动权。换言之,警察实际上拥有维护公共秩序、缓解矛盾冲突的能动性和主导性地位。抗议者是否“孱弱”或带来严重“威胁”,这些因素都必须通过警察的感知、权衡及判断来产生实际作用,即警察在现场处置中拥有对参与人群特质及其行为的界定权和裁量权。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民众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公民组织的快速发展,各类群体性事件开始日益增多。抗争治理已成为基层政权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之一。西方警治中的模式发展、警察群体的角色定位、警治行为的法治保障对推进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抗争治理模式。西方警治中的武力升级、协商管理以及策略瓦解模式皆源自西方社会自身的发展历程,其演化过程恰恰说明抗争治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路径,而是需要根据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境不断进行理念与实践创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基层社会的抗争治理也必须寻找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的有效模式。较之西方社会普遍警力配置完备的状况,“警力总数不足,一线警力紧张”是当下中国基层政权在抗争治理中遇到的严峻挑战。[17]然而,“警力有限、民力无边”——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而言,基层社会的抗争治理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形成警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模式,即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协同完成维护社会稳定和维系公共秩序的艰巨任务。从实践层面而言,可以充分借鉴西方警治模式的长处:如策略瓦解模式的重视情报收集和提前介入,特别是依靠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退休党政干部、社区积极分子等力量共同甄别社会不稳定因素并参与矛盾化解工作。此外,协商管理模式中的警民互动也是抗争治理的一个新视角,即警察应尊重和理解民众表达合理诉求的基本权利和强烈愿望,以平等姿态进行沟通协商,避免简单粗暴地压制群众的正当要求。最后,一旦集体行动出现暴力倾向,强力控制是任何政府为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须果断采取的应对策略。
其次,警察应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冲突的缓冲层。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处置社会抗争事件时,警察都必须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控制事态发展,调解矛盾冲突,恢复公共秩序。相比而言,西方警察往往以较为中立的姿态介入到民众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中。一方面,警察尊重民众的表达及集会自由,不会贸然终止集体行动;另一方面,警治过程体现了高度职业化特征,不受当地政府或官员的干扰。这种类似于“第三方”的角色反而使得民众较为信任警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判断,并乐于接受其引导和调解,让警察无形中成为“官民”矛盾冲突的缓冲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基层的警务工作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比如,一些地方干部动辄差遣警察参与各种非警务活动(如征地、拆迁等),并依赖警察权威压制民众正当诉求的表达,导致了警民关系日益紧张——警察充当了基层政权胡乱作为的“替罪羊”,成为民众怨忿情绪的发泄对象。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警察往往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挡箭牌”和“防弹衣”,或沦为某些基层干部的“打手”和“保镖”,根本无法有效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难以承担化解“官民”矛盾冲突的重任。为此,公安部曾三令五申严禁民警参与各种非警务活动,其目的正是强调警治行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特性。[18]从长远角度来看,基层抗争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强化警察的公共服务属性,提升警务部门的垂直化管理和职业化素养,塑造“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制度文化,使之成为调节国家和社会之间张力的“减压阀”。
第三,建构警治行为的法治保障。在西方国家,任何一种警治策略和警治模式都必须基于法律授权并符合既定的法律程序。警察对社会抗争的处置方式既严格按照现有法律的赋权进行实施,其警治行为又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樊鹏、汪卫华、王绍光等曾指出,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需要坚持“依靠群众、依靠基层”的群众路线,还须提升公安部门的法治化程度。[19]33-43从国家层面来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由此,警务法治化也是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警治行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而为,政治权力并非不能介入警务活动,但其介入过程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并受到法律制约。目前,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警治行为受地方领导的行政命令影响较大,非法用警现象屡见不鲜,警察滥用职权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依然严重,这都充分表明警务法治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该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大多数社会抗争事件并非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诋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其本质是民众为了表达某些具体的利益诉求而进行的非制度化维权活动。在处理这类人民内部矛盾时,一切脱离法治轨道的处置方式皆不可取(如“花钱买平安”或强力打压等)。因此,唯有推进警务法治化才是杜绝权力滥用、取得民众信任、创新抗争治理的重要保障。
最后,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显著的“规矩意识”,这构成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虽然中国民众的维权意识日益高涨,但群体性事件的参与群体大多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利而“无奈一搏”。在许多集体行动中,参与者会主动地拥护中共的执政理念和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并自觉地恪守一些政治“规矩”(如回避政治上的敏感议题、避免言语攻击或丑化国家领导人等)。这与西方社会抗争政治中参与者为了强调个人的价值理念或权利诉求,不惜突破体制束缚、法律规制和政治底线的行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基于西方社会背景而衍生出的西方警治模式决不能盲目套用或简单照搬,而必须对其进行审慎的学理分析与理性借鉴,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境况,从模式探索、机制设计、法治建构等维度提出有效应对基层社会治理挑战的“中国方案”。
[1] Tarrow S.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王智军. 警察的政治属性[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 利普斯基. 基层官僚: 公职人员的困境[M]. 苏文贤, 江吟梓, 译. 台北: 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0.
[5] 罗伯特·雷纳. 警察与政治[M]. 朱俊瑞,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6] Schweingruber D. Mob Sociology and Escalated Force [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00, 41(3): 371-389.
[7] Della Porta D.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Gillham P. Securitizing America: Strategic Incapacitation and the Policing of Protest Since the 11 September 2001 Terrorist Attacks [J]. Sociology Compass, 2011, 5(7): 636-652.
[9] Vitale A. Managing Defiance: The Policing of the Occupy Movement [DB/OL]. (2013-05-30) [2017-03-15]. http://perma.cc/A8UN-XFB4.
[10] Earl J., et al. Protest under Fire? Explaining the Policing of Protest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68(4): 581-606.
[11] Della Porta D., Reiter H.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2] Earl J., Soule S. Seeing Blue: A Police-centered Explanation of Protest Policing [J].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06, 11(2): 145-164.
[13] Earl J. Tanks, Tear Gas, and Taxes [J]. Sociological Theory, 2003, 21(1): 44-68.
[14] Goldstone J., Tilly C. Threat (and Opportunity) [C]∥Goldstone J., et al.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9-194.
[15] 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6] Boudreau V. Precarious Regimes and Matchup Problems [C]∥Davenport C., et al. Repression and Mobilizatio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33-57.
[17] 陈丽平. 解决基层民警警力不足问题[DB/OL]. (2013-07-05) [2017-03-15].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jdgz/gzjd/2013-07/05/content_1800220.htm.
[18] 新华网. 公安部: 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DB/OL]. (2011-03-03) [2017-03-15].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3/03/c_121146004.htm.
[19] 樊鹏, 汪卫华, 王绍光. 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 (5): 33-43.
EvolutionofWesternPolicingModel:FromPerspectiveofSocialGovernance
ZHOU Kai
(SchoolofMarxism,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policing model; contentious politics; social governance
Western policing model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generational changes, from escalated force model, negotiated management model, to strategic incapacitation model, which reflects the shifting rationale of tackling contentious action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olicing model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street politics” in the west, as well as deeply influenced and constrained by police-related factors, protester-related factors, and threat-related factors.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imitate western policing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ng model, the role of policema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cing behaviors are still important reference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0.14182/j.cnki.j.anu.2018.01.011
2017-01-23;
2017-03-16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16PJC061);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城市治理专项项目(16JCCS27)
周凯(1983- ),男,山东济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和抗争政治研究。
D035.29
A
1001-2435(2018)01-0086-06
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