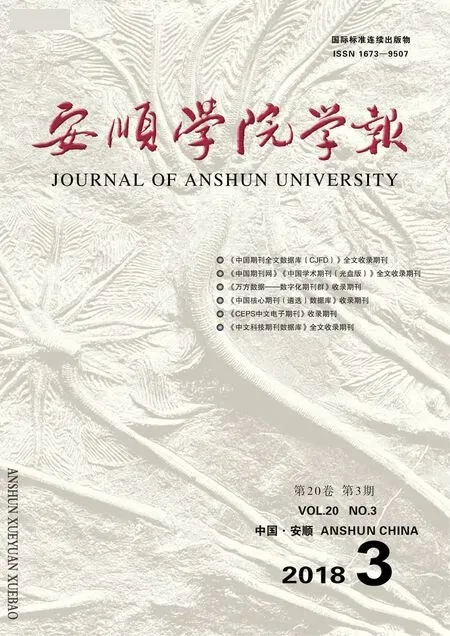以笔为旗:《金牧场》中的神性与人性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
《金牧场》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完成写作后他对作品进行了反思,认为“整个设计全错了”,并将这种错误的尝试归于对西方文体的模仿、对结构主义的追求。此后张承志对小说进行多次删改,后易名为《金草地》,但作为“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最富有震撼力的拳头作品之一”[1]的《金牧场》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正因《金牧场》的叙事结构,使作者的身份有了穆斯林作家、草原之子、学者等多重标签,张承志用复杂的笔调谱写出自己心中与众不同的“金牧场”。小说一经发表,纵使是以抒写草原闻名的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读过此书后也难以按耐喜悦之情,他说“我写了大半辈子草原,但我写草原没有写得像承志那么好”[1]。用浪漫的笔调表达对理想的追求,是张承志一贯的风格,在散文《以笔为旗》中他写道:“而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我的战旗。”[2]296《金牧场》正是张承志向世界宣示一个“以笔为旗”的“精神圣徒”的理想信念。
一、不朽的神性
《金牧场》中存在J与M两条叙事主线。J是英文日本(Japan)的首字母,所叙述的是主人公作为一个学者来到繁荣的大都市东京的生活场景,其间穿插了两个故事作为副线:通过主人公的回忆追溯西北所查访的故事;主人公的研究课题《黄金牧地》中五勇士寻找天国的故事。M是英文蒙古(Mongolian)的首字母,所写的是主人公在蒙古高原插队的知青生活,穿插了红卫兵重走长征路的故事情节。作者在整部小说中多点连线,将日本、蒙古高原、伊斯兰高原组合在同一部作品中,他不仅想表现自己人生经历的丰富,更多的是为了宣发内心的“世界主义”宗教情感。在小说中,张承志歌颂那些徒步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途中他们条件艰苦、衣衫褴褛,遇到同类向前道上一句“萨俩目”,遇到外人则不言不语,他们“不相信护照签证,不相信异乡异语,不相信天险的传说,不相信盘缠穷尽……前方纵有千难万险他也绝不可能回头。”[3]132与此相反,张承志在日本扮演了另一种“异乡客”,他心灵孤独,面对着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虽有物质条件的丰富,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向往的是给予他灵魂救赎的中国北方。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中必然导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对立,而宗教能给予世界性的关怀。张承志所推崇的宗教既是传统的一神教伊斯兰教,还有对自然崇拜的推崇,他热爱自然,无论是在苍凉悲壮的西海固,还是柔美的日本雪国,都能涌入他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与激荡。
在张承志笔下有一个神圣的“伊斯兰黄土高原”,它不是一个地理学名词,而是张承志为文学而命名的,在这片干旱荒寂的土地上飘扬着绿色的旗帜,就是中国穆斯林的“以信仰为旗”。主人公也曾对宗教发出过质疑,“宗教难道真的这样撼人心灵吗?”[3]126作为一个英雄主义者,主人公熏陶在“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环境中,突然受到了来自宗教的洗礼,他的内心世界是割裂、纠结的。如张承志笔下所反复强调的“西海固,你这无鱼的死水”,“无鱼”便是对内心痛苦的写照。在杨阿訇的带领下,主人公来到了无名死者之墓,这里位置隐蔽,外人难以窥探。凄凉的圣徒墓承接着张承志《心灵史》中的一段历史记忆——哲合忍耶教徒为了护教而英勇献身的信仰史,每一个读者无不动容,在穆斯林世界更是形成了一股力量。自古以来,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撞交互不断,一种奇异的悲观主义在回民世界流传起来,多年来他们前赴后继、向死而生,因此书中说“绿旗被染红了”。一旦出现牺牲与殉教,便成为一种“成全真主美意”的善举,在哲合忍耶教派中更是流传着“辈悲举红旗”的口唤。念“苏热”作为穆斯林礼拜时的仪式,承载了共同的情感与群体的共在,阿拉伯语穿透了一切差异,张承志在文中反复写到“从甘肃到土耳其,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这句话不但概念严谨,而且含义深刻,它象征着穆斯林“世界主义”的形成。因此张承志歌颂朝圣者,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到远方去!”虔诚是一种宗教的品格,超脱世俗,是一种盛举,在这群圣徒面前作者被完全的感动了,民族间的矛盾丢舍到一边,人类群体被深深的震撼,这是张承志意图向读者所展示的精神伟大之处。
20世纪80、90年代,社会格局发生着激荡的巨变,“人文精神”“崇高”与“清洁”这些词语是否行之有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张炜认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有些东西上帝必须让他们看管才好”[4]。张承志亦然,他与商业物质主义分离,指引他的只有真主与诗意,而诗意是通往神的,在神面前个人总是渺小的,因此每当谈及信仰时,他总是为之一振,在一瞬间“觉得自己血液中的一个什么精灵突然复活了”[3]160。
在《黄金牧地》的故事中,五勇士受众汗之汗委托寻找天国,他们年龄各异,翻越雪山、经历千辛万苦。过程中不断有人牺牲,最后仅剩一个孩子。在神的启示与心灵的引导下,孩子把代表智慧的长者推向火海,奇迹发生了,孩子突然蜕变成一个英俊的少年,从肉身中抽离出了永恒体验,他经死亡而找到了黄金牧地。在宗教世界,没有不朽的肉身,只有永恒的灵魂,作者认为要达到灵魂上的神性,就要抽脱出肉身的苦难,通过坚定自我意志,才能迎来神的眷顾。长成青年的孩子最后刺瞎了双眼、自断胳臂,伤痕累累。但正是这样他才内心宁静、毫无波澜,超脱肉身悟出真正的神性。西方的悲剧也给人类似启示,直视美杜莎之脸的人都会石化、聆听塞壬歌声的航海者都将触礁沉没,只有在与限制肉身条件的对抗中才能获得超越,这是整个人类所共通的宗教情怀。在张承志笔下,神性不仅是宗教性的认同,还有浓烈的民族自豪感。在杨阿訇的口中,主人公得知了先辈是具有反抗意识的民族英雄,激起了他沉睡的民族意识,这里作者不是在煽动民族分裂,而是用自身关照中华民族,呼吁全中华民族为理想活动而奋斗。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根基,得益于作者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多年的生活经历,在内蒙高原、天山谷地、青海,张承志发出了彷如回到昨世的感慨。这是一种血溶于水的真挚,饱含着对多民族国家的爱,同时闪烁着人性的光环。
二、 永恒的人性
人类的生命史是广泛而长久的,《金牧场》以生命为纽带,将形象细化,表达对人性美的歌颂。在草原上作者勾画出一副青年群像,首先是主人公,额吉给了他一个蒙语名字“土木勒”后,他便是草原里的一份子,当拥有自己的马后欣喜若狂。随着额吉迁向梦中的家乡“阿勒坦·努特格”,因为他的无限向往,义无反顾地踏上旅途。在草原上他喝奶茶、烧羊粪、抽旱烟、骑马奔驰……彻底地融入草原的生存环境,即使环境恶劣,作为城市来的外来者他欣然接受。而在迁移的过程中,风雪交加,他硬着头皮撑了下来,这时额吉口中的“金牧场”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吗?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牧人的“我”,早已明白了青春的意义,就是不停的颠簸、游走,事实上“金牧场”就是“我”的家,纵使艰苦也抵不上草原所带来的浪漫和希望。一众青年里还有称自己是将门之后的假公子哥李小葵、高云薄义的蓝猫、相貌姣好的姑娘小遐等人,他们都来自城市,在草原上过着贫苦的生活。十年浩劫锤炼了他们,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放弃了城市的舒适,草原将他们融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苦难哺育了他们,因此他们具有了比同龄人更坚毅的品质,在离开草原前主人公说到“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不能再摆出一幅北京孩子加额吉家知识青年那股赖劲了,我不能再不顾礼性地向额吉胡说乱问。”[3]401他们的青春在草原上得到诠释,他们读懂了草原的语言,这比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更有益。
草原上的蒙古牧民中,张承志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刻画蒙古额吉,透过额吉可以看到整个游牧民族的苦难与命运。另一方面,作者歌颂母爱,女性的天性让额吉成为“我”在草原上的保护伞,教他骑马、教他生存的本领,额吉成为了他的人生导师。作者美化了苦难的草原,实际上是受影响于额吉,她的存在即是人性美,遮掩了这个草原的悲痛与黑暗。额吉的前半生饱受了家庭的不幸,后半生又面临着政治的迫害,与传统的蒙古族人物形象不同,额吉不是一个命运的反抗者,她总是凝视草原,用沉默地面对厄运,她早已将生命融入了草原,因此能够使“我”作为一个闯入者过渡到本民族一员,引导“我”不断地吮吸着蒙古民族的文化乳汁。额吉的对立面是一群“内人党”,他们是草原上的恶势力,他们穷凶极恶地闯入额吉家里,并扬言要将额吉定为特务。额吉没有慌张,按照礼节将他们奉为客人,与额吉的从容不迫相比,反动派变得更加萎缩、懦弱,额吉的形象就变得高大起来。牧民过着纯粹古老的游牧生活,虽然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心中向往着圣地,在寒冷的时节执着向前,在苦难面前额吉从未屈服,张承志并没有歌颂某一个伟大的群体,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平凡的现实人物。
草原以其博大,修补了主人公残缺的青春,作为一个骑手,张承志对骏马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我”拥有第一匹骏马时,“我被一阵颤抖的热流淹没了。”[3]26这种欣喜之情近乎难以言表,这匹马象征了额吉与草原,它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着草原的洁净,纵情的狂舞更是张承志对自由的热烈期盼。草原的野性代表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品格:豪放、质朴、原始,在马背上这群青年人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主人公说:“我知道:我变成了一个牧人”。
张承志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于红卫兵,张承志是抱着复杂的情感的,一方面是英雄主义熏陶下的崇高意识,另一方面是饱有良知的反省。在大串联式的重走长征路途中,年轻的红卫兵身上传承了往昔的优秀品质,集体的团结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途中他们如当年一样情景再现,翻雪山、越草地,经历磨难,在生与死的考验下,表达他们对英雄的敬意。在旅途中这些年轻人高呼“革命”口号,然而对于革命是什么他们一无所知,凭借长辈与历史中对革命的描述,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我懂得的革命只有你,我懂得的革命就是你。”[3]317年轻的孩子们将崇高、伟大的事业理解为一种单纯的个人情感。张承志站在客观、冷峻的立场上审视红卫兵,虚妄的理想毁了一代人的青春,对于时代造成的伤害,张承志一直在反思之中。他借主人公之口道出自己是历史罪人的忏悔,在路上这群孩子碰到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兵,他们鞭抽了老兵,作者借此将红卫兵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庭。用皮鞭打人、用自行车链条武斗的情节,这些都上升到“人性恶” 的高度,然而在《金牧场》中这群孩子还是可爱的,他们对革命的追随,放置在那个年代,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许子东认为,同梁晓声的自白相比,《金牧场》主人公的红卫兵立场更痴迷更浪漫,其道德标准也能够一以贯之至少自圆其说。[5]由此可见《金牧场》中红卫兵的描写,并没有上升到历史性的精神批判。
三、神性与人性的迷失
在《金牧场》中,张承志采用了J与M的交叉叙述的手法,日本东京与蒙古草原的情节是各自独立的二重奏,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J与M之间没有线性因果关系,使读者阅读文本时感到强烈的不适,作者正刻意地构造出冰火两重天的效果,即J与M两主线上的强烈反差。作者采用的这种结构所构建出两个平行的世界:繁荣、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东京;悲壮、苍凉的蒙古高原。当“我”只身前往东京时,确实被大都市的繁荣所震撼,工业化的气息与开放的生活,主人公在新事物面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感,高楼大厦、灯火辉煌、洋味美女……作为一个学者而言此刻主人公是成功的,但他没有过早地沉醉其中,在接触之初就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对他而言这更像一场灾难,随着深入日本生活,他开始反感这种放纵与不负责的生活,起初感兴趣的“美人ing”也变得无趣,他开始怀念北方大陆那种雄浑深厚的“母体”。张承志认为这种繁荣的都市文明是一种过度的文明,就像一朵花一样盛极必衰,因此他写道“文明成熟得腐败、腐败得可憎”[3]39。张承志所呼唤的古老文明,是一片隔山跨海的信仰土地,对此充满了憧憬。但主人公发现来自古老中国的人们如张小星已完全融入异国生活,处处都充斥着糜烂的气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危机的信号。当“我”遇到一个下跪赎罪的日本兵,主人公的态度是漠然的,在这种俗世所谈的信仰是对信仰的丑化,甚至是后面所谓政治上的信仰:左翼与右翼的对垒,在主人公看来如笑话一般,无论是马丁·路德·金,还是“英特纳雄耐尔”。
转机发生于遇到小林一雄,一个被称为民谣之神的歌手,他的歌声充满了神性,指向灵魂和生命,尤其是那一首首极富画面感的歌曲,张承志形容他“揭开了历史的妆容”。小林引导“我”对现代社会的混乱与污浊产生了怀疑。作为“我”的同一类,小林发出了SOS的求救信号,“我”作为一个异乡客却不知道这个信号发给谁,这无疑加深了我的痛苦。当“我”听到小林的歌词如“人人都是孤独者”、“像孤儿一样无处驻足”时,一股酸楚直捣“我”的内心深处,流浪者怀念一方风土,在“小林一雄化”的日本风景前找到了共鸣。小林的出现在小说里起到了连接J与M的结构作用,从蒙古到日本,作者就是在寻找一种“绝望的前卫”,为自由、理想奋斗,反抗世俗的压迫,这是牧民心中的“阿勒坦·努特格”、五勇士寻找的天国、红卫兵心中的革命信仰。两个人之间感同身受的孤独感,让“我”有了清醒地认识、坚定了信仰。无论如何的喜悦,“我”作为一个学者,都将被任务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在研究中探寻隐秘的真理,在《黄金牧地》的审美幻象中,他看到了中国北方的景象。
最终,主人公生病了,这是“异乡人”的漂泊病症,从精神疲惫到高烧不退。作者将现代都市的优越条件与天山大坂、西海固的恶劣环境进行比较,在艰苦的条件下“我”反而安然无恙。张承志作为一个“精神圣徒”是无法忍受外界对精神的亵渎,尤其是在当时的那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张承志用《金牧场》书写了一个精神沦落的过程,它向世人表明必须保有灵魂上的清洁,世俗的污秽会导致人的毁灭。
张承志一直认为“神不在异国”,只有在生育他的中国北方才能找到自己的血脉与根,但这并不是说他排斥现代文明与异国文化。主人公在日本同夏目、平田、真弓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身体力行地传递了伊斯兰文化。他向平田学习蒙文、向真弓学习日语,不仅是研究《黄金牧地》,还形成了两种文明的沟通交流。张承志在《致先生书》中写道“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之类陈词滥调”[6],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不忍看到中华文化依旧固执己见,他希求用自己的方式使古老的文明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从而构建整个人类文明的新航线,对《金牧场》的主人公来说这无疑是困难的。真弓是一个负有才华的善良女孩,主人公与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真弓与他不能真正的相互理解,真弓宣称她信仰的是马丁·路德·金,而“我”内心更多的是宗教情怀,这导致了二人的疏远。平田虽然在学术领域与“我”有强烈的认同,然而他毕竟只是我的助手,很难达成思想上的共鸣。“我”依旧孤独,在与艺术的对话中,他与梵·高找到了契合,在崇高的信仰面前,所有的事物都是残缺的,在张承志看来梵·高的向日葵是被砍断了头的,只有梵·高割掉了耳朵才能体会到世界的意义,生命与世界融为一体,这就是神秘的生命力。由此作者转向了对生命的探索,通过与梵·高的对话,青春得以延续,在面对生命时他感受到了力量与净化。然而在高度现代化的纷繁复杂的东京,主人公是病态的,就像残缺的人一样,“我”通过残缺感受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四、神性与人性的归复
《金牧场》开篇写到“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3]5
首先,作为回民,他的生命是属于真主的。通过死亡,圣墓里的先烈达成了与彼岸世界的联系。自己母族所经历的苦难在杨阿訇的引导下完整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当他看到圣徒墓时,通过杨阿訇的念词,他被深深地震撼,作家血脉里的母族情绪被激活,他要为少数人而歌。殉道者是伟大的,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品格:“温顺地服从宗教教义和勇敢为圣战献身的人格美标准”。[7]这时,视线转向了整个伊斯兰高原,张承志想到了纵有千难万险也绝不回头的朝圣者,他们纵使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也毅然前行,只有同类才能理解“你们归之于安拉,你们服从安拉”的信念。普列汉诺夫认为“宗教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相当严整的体系”[8],张承志笔下的宗教是一面镜子,映射出现实世界的麻木与腐朽而创造出一个高洁的灵魂。
其次,作为个人,他的生命是自然的,张承志呼唤原始的、无污浊的民族空间。蒙古高原上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东京的刻板人物比较就是举目皆亲与举目无亲的差距,继续M一线作者运用了诗化的语言,与J线的平铺直叙形成强烈比照。诗性叙事将“我”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个人从群体的围城中走出,是“我”从“我们”中的撕裂分离。[9]当主人公回归祖国时遭到了警察的阻拦,而他的内心却是喜悦的,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回归梦中的草原了。小说中张承志时常“现身说法”,作为旁白讲述心路历程,读者很难不将主人公与作者合二为一,从而延至自身,反观全人类的时代病:对物质的过度依赖、对精神力的忽视。在内蒙高原恶劣的环境下,以额吉为代表的牧人们,凭借自身的精神力战胜了草原“铁灾”的暴虐,无法阻挠的是精神长旅,驶向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但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我”在都市的繁荣下一蹶不振,意志消沉,这是精神力的毁损,毫无生机可言。当主人公坐上飞机回国时,病疾不治而愈。
在《以笔为旗》中张承志写到“在异国的两脚连一块稳定的土都踩不住,何况作深刻的选择呢?我先迈回脚,踩住了大陆。”[2]296无论前景如何,在神示下必须回到中国北方。在“我”向往归复时,那些所谓的异国专家、学者的说辞是可笑无知的,因为主人公是一个同小林一雄、梵·高取得精神契合的艺术家。《黄金牧地》的开篇写到“世人都说尘世痛苦,世人都说在大雪冰的彼岸有天国”,在宗教的指引下,主人公找到了生命的栖息地。
文末,张承志写小女儿奔跑逐日,作为一个新生命,与文初对生命的敬重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构成,代表了对生命追求的意象,是张承志“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与勇气。神性与人性在生命里得到了同一与归复。张承志最后对九死不悔与自由自在的浓笔重墨,与《以笔为旗》中“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我的战旗。”[2]297遥相呼应,在神与人的交际中,一个精神圣徒跃然纸上。
此书发行之后,张承志已成为一个文学现象学引发广泛的讨论。木弓批评这部小说时说“一方面在赤裸裸地阐述理想主义的思考,一方面则让读者看到许多现代技巧的处理。这两种完全不同本性的东西被硬是揉在一起,成为《金牧场》现象。这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盘大杂烩。”[10]而张清华则认为张承志“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和捍卫”[11]。很显然张承志对这些评价是不以为意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失败的,但依旧视其为珍宝,事实即是如此,《金牧场》现已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拔地而起的一座高峰,延续了中国“神人以和”的传统,其成就是改写后的《金草地》难以逾越的。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