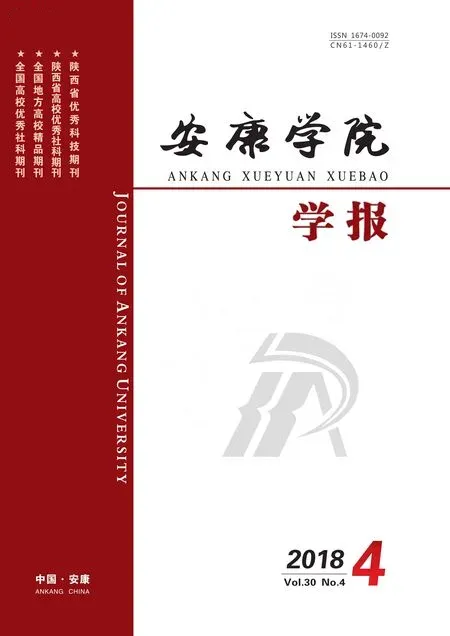《时代漫画》中的摩登女郎
曾江莉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时代漫画》杂志由鲁少飞主编,于1934年1月由时代图书公司在上海创刊,1937年6月停刊,三年共发行39期。该刊16开,每期刊载讽刺类、都市轶闻和连环漫画作品等。以往人们都是从新闻性、战斗性和技术手段去研究《时代漫画》,很少有人去关注占用大量篇幅的性别展示。在《时代漫画》中,多方面描绘了女性的生活风貌及生存境遇,为30年代上海女性形象研究提供了素材和资料溯源,特别是对代表时尚流行的摩登女郎的关注,对其生活方式、生存空间和社会想象的描绘,充分体现了在消费主义浪潮下,人们生活风貌的变化(包括衣着服饰、生活习惯、出入的现代场所等)以及在西方现代意识的冲击下,人们思想、价值观的塑造。从女性角度出发,全面展示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及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地位作用,为以后研究女性的现代性体现、生活境遇和两性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摩登女郎与生活方式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说道:“英文m 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在日常会话中有新奇和时髦之义,上海和‘摩登’自然就是一回事。”[1]5由于西方现代思想、生活方式的影响,30年代的上海都市人在丰富的物质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空间所带来的欲望和放纵中,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1]43,漫游的男性、堕落的女性成为现代的标志。而女性因其自身的特点,更易受到都市文明的冲击,她们身上体现的现代性、摩登性实则是男性欲望的设想,是城市物化的载体,也是女性自身社会空间的扩张。《时代漫画》中大量描绘女性生活、工作、家庭的漫画作品,生动地展示了上海社会女性的生活百态图,而对摩登女郎的描绘更是充分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新气象、新风貌,同时透过都市摩登的表象看到了其西化、物化的内核。摩登女郎作为一扇观察都市的窗,拨开重重华丽的帷幔,可以窥见中国现代女性的生发。
随着女性解放运动地不断深入,女性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使其能够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获得就业机会。都市女性就业者数目急剧增加,职业范围不断扩大,从《时代漫画》中可以看到女性就业者已经出现在政府职能部门、公共事业领域、文化教育、工商服务领域、娱乐演艺等几大领域,就连长期由男性所占据的事业部门,同样出现了女性就业者的身影(比如公务员、高级管理者等精英行业)。新兴就业的女学生、走出家庭的女性、城乡涌入的女性就业者共同参与到社会竞争中,而有限的职位无法满足全部的就业需求,由此产生了都市“漫游女性形象”——沉醉于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无法正常就业但又不愿离开,依靠皮囊周旋在声色犬马中,比如舞女、妓女、交际花等。这些群体,没有羁绊束缚,全身心投入到对现代事物的追求中,她们的身影穿梭在30年代的上海各处,成为都市摩登文化的代表。从她们身上可以发现最新潮、最前卫的生活方式,如:
(一)公共化的出入场所
从固有的家庭之地扩展到学校、职场、娱乐场所,从单一的闺阁到放射性辐射转变。通过求职、消费、娱乐等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观念的界限,实现从私化领地向公共场域位移。第1期中现代女性去应聘女职员,女性在大学任教;第20期中幼稚园的实习师,在茶馆里唱歌,还有频繁出入舞厅、百货公司、展览馆等现代化建筑。出入场所的公共化,同时也改变了女性的社会承担,不再仅限于传统的家庭角色而追求公共空间的社会身份认同。
(二)潮流化的衣着服饰
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浸润,传统保守的衣着服饰发生了改变,大量时髦的服装款式、材质、搭配出现在摩登女郎身上,服饰向功能化发展。《时代漫画》中,各种款式的旗袍、大衣、毛领、高跟鞋的搭配;华丽的舞裙、礼服;各式的内衣;性感的泳衣;摩登的制服,修身的款式、极富曲线美。除此之外,发型的式样也是多种多样,优雅的盘发加上精致的发饰;时髦的短卷发,斜分或齐刘海。在第1期中,详细的记录了摩登的条件:一个舞女生活费的微算、摩登女子最低的费用包括皮鞋、丝袜、奶罩、卫生裤、吊带袜、大衣、胭脂、包包、电烫发等。
(三)西式化的生活方式
西方重自我、重享乐的消费文化深深影响了摩登女郎的思想行为,使其沉浸于小我之中。《时代漫画》中,喝咖啡、喝酒、跳舞、交际、购物、打高尔夫、游泳、参观展览馆等西式行为习惯随处可见,也体现了摩登女郎们追求精致化生活的倾向。在第9期中充分展现了新感觉派女人们的生活方式。
(四)多元化的两性关系
挣脱出传统道德的枷锁,新式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使摩登女郎们摆脱了从一而终的伦理压抑,爱情和婚姻变得可有可无,她们只是沉溺于原始性欲的追求中。一对男女可以在公园接吻、约会,可以在舞厅共用一只酒杯喝酒,以往私密的交往活动向公众透明化展现,就连家庭都不再只是禁锢,而成为满足爱欲的场所之一。在《时代漫画》中可以看到,未婚的小姐们和男人们调情、已婚的太太们有多个情人,男性亦是如此。显然婚姻已然无法束缚两个男女,自身爱欲的追求成了唯一目的,由此在漫画中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家庭关系,如第6期的多妻主义者,第19期中丈夫将出远门、家里藏着几个男人等。
二、生存空间与社会想象
除了地理空间的扩大化(从家到社会公共空间的地理位移),还有精神空间的主体性转移,抛开传统的伦理束缚,在社会中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女性不再受限于厨房、客厅、小院等私人化地点范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公共地域,如舞厅、公园、郊外等。逃离家庭,从男性手中夺取自主支配权,在压抑的生存空间破裂之后,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生存欲驱使求职带来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情欲驱使交际带来自我意识的展示,个人主义在消费主义下得到宣泄,女性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由被动趋向主动。在传统社会、家庭中,女性总是沦为男性意志的牺牲品,就连爱情也是如此。男性主动追求爱慕之人,掌控着爱情的发展及走向,甚至决定了最后的结局。在情欲的游戏里,他们是胜利者,肆意操纵游戏规则,而摩登女郎则颠覆了此举,化被动为主动,成为情欲的操控者。《时代漫画》中多幅作品都呈现了摩登女性在众多追求者中肆意狭情,如趁着丈夫出门在外,与多个男性调情、纵欲,这显然深受西方享乐主义的影响。女性不再借助男性话语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而是以独立的个体彰显生命的意义。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从单一“被看”向互相“看”转变,由此悄无声息地夺取凝视的权力。“权力给予观者‘看’的能力,并以此确立自身主体地位,而被‘看’者则承受着观者目光所包含的权力压力,并在无意识中添加其价值取向、审美判断的印记。”[2]虽然女性还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但也让完全自傲的男性感到压力,因无法完全掌控女性而感到焦虑。
“社会赋予男女不同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当其思想规范和行为模式符合社会定位时,他(她)就会被社会所认同。”[3]不同时代认同的内容涵义也有所不同。长期由儒家统治的中国,贤妻良母的标签深深烙印在女性身上,这也符合女性温顺、柔弱的社会想像。如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的那样,社会想象总是屈服于权力话语,女性的形象认识总是构建在男性统治的话语中。以往妻子、母亲等家庭身份便是女性全部的生命标签,而摩登女郎却将之丢弃,不仅作为妻子、母亲,还是情人、社会分工后的主人之一。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民族的共同想象会形成一个同质的社会印象,这亦适用于摩登女郎的形象建构。由《时代漫画》可以总结出,摩登女郎形象在社会想象中的四种建构:一是具有现代思维的家庭女性形象(不安于现状的妻子、开明的母亲、新式家庭观的成员等),如第1期中给丈夫冷气受的妻子、第10期中指着丈夫骂的妻子;二是努力上进的职场女性形象,如第1期中去求职的女职员、第19期中记文书的女书记;三是健康有劲地劳动女性形象,如第11期中卖菜的女小贩、第15期中进城务工的保姆;四是游离的女性闲逛者形象,大多是舞女、妓女、交际花等非常态职业女性,如第9期中新感觉派的女人们、第10期中的黑羽之舞中的舞女。第四类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关注的重点,她们身上彻底的摩登性致使其更能随心所欲的生活,对物质、享乐的追求是她们唯一的生活中心,其发型、着装、生活方式被大众追捧,是潮流的风向标。在此,摩登的定义泛化,不仅指新潮的女性,还包括现代雇佣关系下的女性以及市场经济交易下的女性从业者。女性社会想象的变迁揭示了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阶段。但是,这种变迁也伴随着不良影响,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在大众消费中将女性作为商品物化等。
三、“摩登”名片与男性意识
期刊杂志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媒介,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商业化色彩,在《时代漫画》中登载了众多针砭时事的讽刺性漫画作品,“战斗性”极强。出于商业化考量,人们喜闻乐见的两性关系漫画作品占有大规模篇幅,除了规避大量政治漫画登载可能会造成的停刊,还因其迎合了大众的阅读消费习惯。简单的线条画面、图文叙事的结构模式、两性的世情俗事等都是大众最易接受的形式内容,购买力强的男性读者群加之新兴活跃的女性消费群便催生了各类杂志的繁荣。随着20世纪西方消费主义在都市的盛行,消费与享乐成为人生的主题,作为物质的商品也增加了许多非物质因素,“眼球经济”和“符号消费”操纵着消费趣味和消费时尚,人们不再只关注商品的功能属性,而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社会属性,甚至形成了躯体意象的定制标准。身体成为消费意象在社会中的解码,即身体商品化并作为承载社会愉悦的物质载体,通过物的堆积来完善躯体。而女性自然成为身体商品化的载体,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忽视女性的主体形式,女性的身体成为权力秩序规范下静默的牺牲品”[4]。女性身体商品化是资本市场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寻求增值的必然产物,需求影响生产,从而在《时代漫画》中有大量描绘女性形象的漫画作品登载。就拿封面来说,《时代漫画》共发行了39期,其中有16期都是用女性的形象作为封面设计,以吸引众人眼球。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在传统经济关系的压力下,作为主导地位的男性对现代都市女性产生了矛盾与焦虑。在都市聚合作用的影响下,使得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而又以男性迁移者为多,失衡的性别比例使得女性成为吹捧的对象,男性意识下的女性消费热情高涨,以此为内容的杂志不仅迎合了潮流,更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想象。处于消费主义和社会性别权力话语中的女性身体标准,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不管是古代的缠足还是现代的曲线美,都明显体现出文化偏见,这是由男性主导的伦理和审美霸权。时髦的短卷发、精致的妆容、前凸后翘的丰满曲线、流行的服饰、风情的形态、放荡的举止等迎合了男性的审美标准,具象成摩登女郎的符号名片。其中凝结了西方消费主义的审美意识,通过文学、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向都市蔓延,致使外国美女形象成为摩登的参照物,西化的卷发、服饰、大胸、细腰、长腿等成为衡量都市美女的标准,《时代漫画》中出现了大量此类美女形象,如第7期中男性询问细腰女孩的腰围等。
在后现代消费时代,“看”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动机,被符号化的女性身体自然作为男性窥视和观看的对象。根据布迪厄的说法,“看与被看”的关系体现出社会与政治的场域关系,权力总是凌驾于意识之上,并将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驯服。纵观整个《时代漫画》杂志,“看”的动作出现频率很高,直接画有男人观看女人的漫画作品就有42幅。女性被当作商品呈现,常与酒、金钱、交易等名词相连,有的更是直接作为演员、模特、展览品等成为男性视线的中心,大大满足其窥视的畸形心理。女性性特征往往成为视线的焦点,病态、色情的眼光充斥其中,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消费社会欲望宣泄渠道与寄托载体的扭曲。
在表现摩登女郎的形象时,有一部分则陷入了低俗、色情的泥沼,在欧美裸体运动的影响下,大量裸露身体的女性作品登载,39期封面设计中有7期直接选用裸露的女性作为封面女郎,而全部期刊中有26幅作品是裸露的女性身体。伯格在《观看的方式》中谈到视觉文化中被广为接受的性别政治时说:“世界是由男性领导的,而女性是作为物品来观赏的,裸露的女子是为了取悦男人,而男人是理想观众,也可能成为其主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5]穆维在《视觉快感与电影叙事》中认为:“媒体所表现的色情愉悦是基础性的,大众喜欢观看这种窥视性行为,男性在偷窥女性时会产生心理上的满足,这反映出‘男性家长专制’的社会现象。”[6]豪厄尔斯在《视觉文化》中深层次探讨了女性裸露的问题,他认为女性裸露总能在意识形态中找到各种理由,其实这根本就是内部主义的谬误。“女性身体成为男性欲望的投影,在挑逗中才能彰显存在的价值,通过贬低女性身体来张扬男性权力,使用裸体来建构情欲的意识形态,更强化了男性的绝对统治地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7]低俗色情化倾向是现代化进程中“大众化”与“商品化”的产物,大众文化中低俗、色情的阅读兴趣深深影响了各类杂志的刊载内容,《时代画报》 《良友》 《上海漫画》 《时代漫画》 等纷纷刊登含有色情的图片作品,受到读者群的追捧,杂志销量大、出版社盈利多,更加剧了色情现象的蔓延,形成一种环形盈利结构模式。裸露女性等含有色情的因素演变成资本的附加值,用以商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实现,这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摩登女郎”形象建构的最初商品化目的。
西化时髦的摩登形象是现代性在物质方面的体现,从摩登女郎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间和社会想象等多方面呈现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主义倾向,生动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现实。符号化的“摩登女郎”是性别政治下权力的体现,以具象化的形象塑造来彰显男性的统治权威。站在他者的角度,从外部(话语、大众媒介、社会场域、资本)规训女性的形象和心理,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完成内化的环节。出于商业目的一味追求低俗色情并非长久之举,健康持续的发展之道才是关键,善于运用大众媒介,在迎合大众审美趣味时引导其健康的发展,才能实现自身消费主张的最优化配置。两性关系的发展变迁凸显了时代浪潮中社会必然面临的矛盾与焦虑,如何正确处理两性之间的关系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