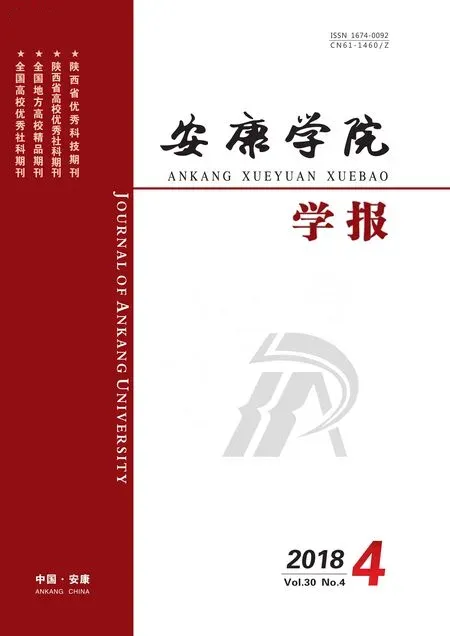明后期的西南卫所与土兵征调
颜丙震
(安顺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明初,在统一西南地区的过程中,统治者在险要之地广设卫所。这些卫所与诸土司错杂而处,有的甚至与土司治地同处一城,此即明朝统治者采取的“犬牙相制”之策,意在令卫所就近弹压诸土司,以维持其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但到了明中期尤其是后期,卫所制度因士兵缺额、屯田破坏、军纪败坏而日渐崩坏。有鉴于此,明廷一遇征战便征调土兵从征。明后期因战乱多发,土兵更是被大量频繁征调。在此情形下,西南地区卫所和土司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一是土兵已取代卫所成为地方平乱的主力;二是卫所不仅不能有效弹压诸土司,反而成为土官土目动辄烧杀掳掠的对象。
一、明后期的卫所及其崩坏
明代的卫所制度到了后期,日益废弛,军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甚至难以履行正常的军事职能。负责平定播州之乱的总督李化龙即称“迩来卫所兵疲敝脆弱,各省皆然。”[1]134从众多明史典籍的记载看,明后期西南卫所崩坏之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兵额不足
明后期士兵员额不足是卫所制度崩坏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以贵州诸卫所为例,万历《贵州通志》中对贵州诸卫所的屯城站铺官军、旗军、军器、操马等的原有及现有数额有确切记载。从贵州全省的状况来看,“各卫所原额旗军及铜仁、思、石等府,戍守汉土军兵通计一十五万八千七百零七名。万历二十五年,查存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名。各卫所原额操马通计二千三百九十一匹,万历二十五年,查存一千一百九十匹。各卫所原额军器通计一百四十三万六千零一十三件,万历二十五年查四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九件”[2]。从该段史料可以看出,万历间贵州诸卫所兵额缺失严重,已不足原额的两成。
到了明末,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川贵总督朱燮元平定奢安之乱后,上疏称:“至于黔省额军,承平不如国初,叛后不如承平。近查缺额官军,数可概见,乃议者曰,议勾补而隔省辽绝,缓不济事,矧勾一军,多一事之扰,而黔省且不胜勾也”[3]5364。又称:“二三年来,如龙里、贵州、贵前、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等卫,俱被残破,共集军九千六百九十七名。都匀、平越、新添、清平、兴隆等卫,黄平一所,虽未残破,止存军三千五百八十一名。迤西永宁、毕节、赤水、乌撒四卫,普市一所,残破更甚,已招回军三千四百六十名。”[3]5365按明初卫所制度的员额标准,每卫有兵额5600人,而奢安之乱后,整个贵州的十八卫二所士兵仅存16000余人,迤西四卫一所更是不及一卫之兵额数。由此可见,明后期贵州卫所崩坏之状。推之全国其他卫所,亦如此状。
(二) 屯田破坏
明初,由于常年战乱,经济凋敝,自养遂成为供养庞大军队的唯一办法。明政府在卫所实行屯田,力求实现军粮自给。但明中期尤其到了后期,屯田制度便已经遭到破坏,屯额已严重不足。仍以贵州为例,据正统年间王骥奏称,贵州十八卫二所屯田、池塘总数“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官军”[3]207。而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巡抚江东之修《贵州通志》之时,贵州“军卫屯田、陆地陆拾叁万肆千叁百伍拾叁亩零,屯科粮米壹拾万壹千捌百玖拾叁石伍斗壹升零”[4],减少近三分之一。
屯田破坏致使卫所粮饷供应成为一大难题。故明后期,一遇征战,朝廷内外官员即因粮饷匮乏而忧心忡忡。如万历间大学士朱赓提及四川欲征剿水西土舍安尧臣一事时深感忧虑地奏称:“顷边饷告急,户部求借太仆寺马价,明旨初许三十万,该寺与兵部连章极口告乏,姑令括老库及东西二库十五万与之,此区区十五万者,而其苦难已如此矣。加以处处水灾,处处空竭,即欲用兵,皇上试问川贵能自饷乎?抑将取之太仓乎?将再取之太仆乎?将令别省协济乎?”[3]4773
(三) 军纪败坏
明后期,卫所制度崩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军纪败坏,卫所几乎丧失基本的战斗力。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贪暴懦弱。这在明后期平定播州之乱和奢安之乱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李化龙在《平播全书》中对卫所官兵贪懦之状揭批甚多,如“当播州初发难也,四方畏之如虎,文武避之如虿,卢应亮以一参将调之从任,惧而自刃其腹,流肠而死,彼时事势居然”[5]。又有:“其时贼气张甚,川人畏之如虎,臣发成都兵,甫出门,欲投锦江,不复肯东。又闻綦江守城兵见贼来,噪而走,多投水者,止余二将与其家丁,遂及于难。”[1]286
在奢安之乱的平安中,卫所官兵贪懦之状更甚。天启二年(1622)二月,奢崇明兵至内江县龙泉山,卫指挥张恺“闻风即弃兵远遁”[6]。石砫女土官秦良玉在奢安之乱的平定中,亲率土兵奋勇平乱,援重庆,解成都之围。其对汉兵将领的懦弱妒功之状深感不齿,在天启三年六月的上疏中痛斥道:“行间诸将,未睹贼面,攘臂夸张。及乎对垒,闻风先遁。败于贼者,唯恐人之胜;怯于贼者,唯恐人之强。如总兵李维新,渡河一战,败衄归营,反闭门拒臣,不容一见。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静夜思之,亦当愧死”[7]6945-6946。
二是好事喜功。万历间,朱赓便极言武臣好事喜功之丑态:“武臣好事喜功,瞋目语难,乃其常态,如侯国弼、张神武辈,利在自封,计划未必可从,才勇未必可用也。即一二兵道不过儒臣文吏,临敌当几或非其所长也,则又谁与领此者乎。观此知安奢之事亦尚可收拾,后来纷纷无乃边臣挑激也”[3]4773。
平播中常见官兵争功之事。《平播全书》载:“访得招抚夷民,有先系此营抚出,至中途为彼营强者所夺,要去报功者。有赵甲招出人口无兵接引,为钱乙官兵撞遇,遂指为奸细,或擒或斩以为功者。人自为心,惟功是嗜。”[1]574在攻围海龙囤时,“诸军既合围,咸以囤后易攻,争走其后。总兵马孔英独壁囤前,已而皆前”[8]693。在奢安之乱的平定中,更是出现了四川总兵侯良柱与贵州总兵许成名争夺擒斩奢崇明之战功一事。
三是虚报军情与战功。卫所官兵虚报军情与战功之事亦司空见惯。万历年间,王士性言及对缅人用兵一事时称:“盖永以外将帅偏裨,无不乐用兵以渔猎其间者,故缅至,每每作虚报。如辛卯夏,余闻缅二千人渡江,而参戎报二十万也。永以内总戎大将又喜,一出兵则渠随路朘削人,以张皇其事”[9]。
平播诸将领杀降冒功之事亦多见。李化龙称:“访得有等领兵将领,及土司官目,明知零星贼级必系杀降,希图冒赏,乃竟不行严禁,佯为不知。甚或通同故纵,匿不发觉,伤天理,灭良心,莫此为甚。”[1]567-568
奢安之乱中,“时寇乱久,里井萧条,贵阳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将士多杀降报功,苗不附”[7]6444。总督朱燮元亦对卫所官兵杀降、冒功、争功等多有揭露,疏中有云:“其地方最为害者在于零星小功,缘各将坐耗廪饩无可搪塞,有虚报贼级而杀顺苗以送验者,有一将已经抚定而一将乘隙掩杀者,有本来投顺而诡称设伏缚献骈首就戮者”[3]5355-5366。
二、明后期的土兵征调
因卫所制度日益废弛,战斗力明显下降,明统治者从中期便开始大量征调土兵参与平乱。如正德间,王守仁奏称:“卫所军丁,止存故籍”,“是以每遇盗贼猖獗,辄复会奏请兵,非调土军,即倩狼达”[10]。王守仁平断藤峡,亦调永顺、保靖土兵,“计前后擒斩凡三千人,两江底定”[11]92。正德十四年(1519),田州女土官瓦氏,奉调往苏州抗倭,“瓦氏提二竖孙,并狼兵数千应之,日索有司捕蛇槛犬为军储,然颇有纪律”[11]94。嘉靖三十三年(1554) 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7]7993。
到了明后期,因卫所崩坏,且战乱多发,土兵征调更多且频繁。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川黔楚三省毗邻地区红苗为乱,兵部尚书黄嘉善上疏建议道:“遇苗出劫,在湖广即令湖北道行永、保二宣慰司,在四川即令川东道行酉、平、邑、石四土司,在贵州即令铜仁道镇,可抚则同抚,可守则同守,可征剿则同征剿”[12]。在明后期大规模土司叛乱的平定中,土兵征调更是规模巨大。如万历年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中,即大量征调土兵协剿。这在李化龙的《平播全书》中多有记载,如:“施州卫散毛、容美等土司各土兵,宜调用一万名;……保靖司、麻阳等土兵,宜调用一万名”[1]68,“其三省所调土司兵,酉阳、石砫、永宁、天全、镇雄、平茶、邑梅、水西各久在防守,乌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顺、保靖、乌罗、独山等,各报已起行”[1]106等等。奢安之乱、沙普之乱的平定中亦有众多土兵应调从征。
在辽东战事中,亦有较多西南土司土兵应调从征。万历二十五年(1597),“总督邢玠议调川东施州卫,酉阳、石砫土司,邑梅、平茶二长官司,湖广永顺、保靖土司兵万人,不足,再调叙泸、马湖所辖土司,土妇奢世续兵,分三营”[13]。四十六年(1618),“调酉阳兵四千,命宣抚冉跃龙将之援辽”[7]8058。
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亦有大量土兵被征调。如崇祯七年(1434),李自成破夔州,石砫女土官秦良玉“统土兵出战,劫其众,使自成无西志”[11]45。其后,张献忠入川,秦良玉又率数万土兵抗击。
三、明后期土司与卫所的关系
(一)土兵取代卫所成为地方平乱主力
实际上,征调土兵从征在明初即已有之,如洪武二十八年(1396),都督杨文平定奉议、南丹,曾“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7]8269。永乐四年(1406)七月,明成祖北征,宁远州土知州刀吉罕“以土兵四千随征”[14],但此时仅是偶尔为之。从明中期开始,随着卫所制度的日益废弛以及战事规模的不断扩大,卫所官兵渐已无力承担。明廷除采取募兵的方式以作卫所士兵不足的补充外,越来越多地征调各地土司土兵参与征剿。到了明后期,征调之土兵甚至取代卫所士兵成为地方平乱的主力。
万历间,内阁首辅朱国桢称:“两广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后四川、云贵亦如之,在制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15]。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中,李化龙兵分八路,“每路三万,官民三之,土司七之”[7]5985。播乱平定后,播州旧民吴洪之乱,贵州路苗、皮林苗诸乱均靠征调水西土兵方得以平定。天启间奢安之乱爆发后,由于辽东战事吃紧,各地卫所官兵被大批调往辽东,明廷不得不大量征调四川石砫、酉阳,湖广永顺、保靖,云南阿迷州、安南、元谋、景东、石屏州、嶍峨、宁州等土兵协剿。
对此,清朝人亦有同感,如毛奇龄称,明廷初创“土兵相制之法”,目的在于“以蛮治蛮”,“而其后展转假借,凡议大征者,无不藉狼兵、土兵,远为驱遣”[11]1。孙承泽则称明代贵州“每一梗阻,滇南中断。朝廷遣将征讨,多借土司之力”[16],四川更是“兵弱,每征调只调土司”[11]39。
(二)卫所屯堡成为土官动辄烧杀掳掠的对象
对于明廷在西南地区广设卫所屯堡,当地土司是极富排斥心理的。但因明前期卫所实力强大,土司对其仍存畏惧心理,故土司虽有杀掠,基本上限于内部仇杀。但到了明中期尤其后期,随着土司土兵大量被征调,这些土司在从征过程中熟知卫所崩坏之状,遂对卫所产生轻视心理。明后期,西南土司土目焚劫卫所屯堡、杀掳卫所军民之事已是司空见惯。
如万历年间,在永宁宣抚使的承袭纷争中,土妇奢世统与沙卜、土目胡迁乔、汉目袁初等兴兵攻打奢世续。奢世统怀疑世续逃往白沙所,便率兵攻围卫所屯堡。总兵郭成勘处之时,又因把总郭天心等索取财物,土妇奢世统遂绑缚指挥使禹嘉绩和郭天心二人。沙卜亦兴兵杀把总黄希忠、王惟镇、朱秉等人,并欲攻打永宁卫所以泄忿。而在明廷勘处奢崇明承袭后,又因四川都司张神武与永宁参将周敦吉集兵掳掠奢世续及其积聚、子女,遂有土目阎宗傅等带兵烧劫杀掳永赤二卫、普摩二所一事。
在土司叛乱中,卫所屯堡更是成为土官土目杀掠的主要对象。如杨应龙叛乱之时,皮林苗酋吴国佐、石纂太聚众为乱,“掠屯堡七十余,焚五开南城,陷永从,围中潮所”[7]6407。奢安之乱中,乌撒土知府安效良攻围乌撒卫、毕节卫,水东土司宋万化则率九股苗攻陷龙里卫。经历沙普之乱洗劫的西南卫所更是残破不堪。
四、余论
土兵征调有利有弊,明廷在倚其协剿平乱的同时,亦不得不承受土司土兵沿途剽掠、恃功自傲、邀求厚赏、虚名冒饷,甚至如水西安氏土司在协剿杨应龙之乱中观望成败、通敌助逆等弊端。有鉴于此,明廷部分官员对征调土兵持反对态度,如万历间沈德符认为:“土司兵最不宜调,其扰中国甚于胡虏。嘉靖间倭警,调麻阳兵,调瓦氏狼兵,俱贻害东南最惨,而终不得其用”[17]。天启元年,朝议征水西土兵一万戍辽,贵州巡按沈珣便极力反对,疏称:“水西胜兵不过二万余人,决不肯轻发,势必将夷民逐户佥定,但图充数,卖富买贫,安计勇怯”[8]629。又称:“楚地去京稍近,前年永、保土兵四千,到关惟七百余人,行粮犹如飘海,此三千三百人者,大半为盗,不能御寇而为寇,何况于黔。……至沿途抢掠作乱,意外之变,又不可言尽。”[8]661但因明后期卫所制度崩坏、财政匮乏,再加上内忧外患的政治困境,大量征调土兵参与地方平乱成为明廷维护统治的常态。因此,土兵征调实为明廷的不得已之举,若卫所制度能够较好地贯彻于明代始终,便不会出现应征土兵“大征居其十八”的状况。
频繁的土兵征调令明中央对于土官的威慑力大大降低,且在协剿过程中,这些应征土司往往借机壮大实力,变得日益桀骜难驯,反而为下一次大规模的土司叛乱埋下了隐患,明后期播州之乱、奢安之乱、沙普之乱的先后爆发便是明证。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