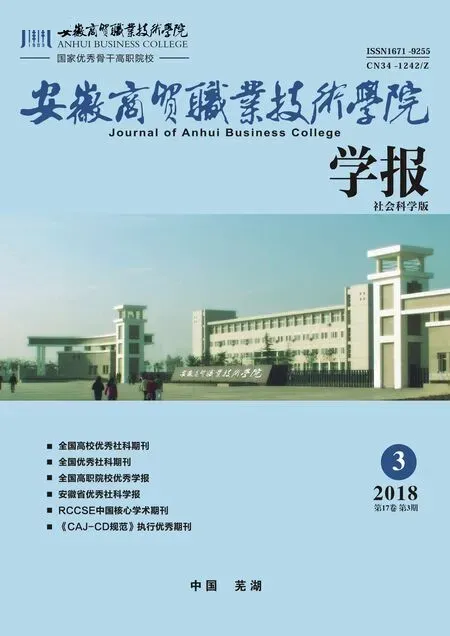对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及实践反思
查 浩
对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及实践反思
查 浩
(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 反贪局,安徽 芜湖 241000)
对危险驶罪中涉及的“道路”、“机动车”等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司法执法机关在实践中能够对危险驾驶罪有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判定。在刑法触手扩张的同时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权,避免其受到片面和偏颇的消极评价,适度采用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方法也能够更好地体现危险驾驶罪立罪的本意。
风险社会;道路;机动车;行政处罚
危险驾驶行为入刑是我国刑法在定罪和处罚上的一次革新。对于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危险驾驶行为性质的确定、危险驾驶人主观状态的考量以及危险驾驶侵害客体的论证都不同于以往对实害犯造成法益侵害后果的认定方法。危险驾驶罪一经刑法确认并施行,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背后出现的问题或者说潜在的危险值得更多地考虑和反思。这不仅关系到将来我国刑法在人权保障、国家权力运用、对公民自由限制、司法裁量等方面的变动和走向,更关系到每一个中国公民在今后社会生活中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以及公权力机关对其真实状态的评估。
一、危险驾驶罪设立的背景——风险社会理论
支持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学者多以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论述前提,认为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刑法应该对危险驾驶这样的高风险行为提前介入,以利于保护法益,更好地控制交通运输领域中的风险,从而体现出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立法特征。因此,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刑法立法应具有超前性,我国有必要将危险驾驶规定为一种危险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1]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风险、环境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信任风险等各种风险正在逐渐增多、增大。近年来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我国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危险犯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危险犯逐渐增多的立法背景,而且我国学者对风险社会及风险的论述外延较之于贝克提出的风险明显扩大了,将传统社会已经存在的一些社会危害行为及其威胁也纳入风险之中进行论述,其合理性还有待考证。从基本立场看,风险刑法理论侧重安全(秩序)而非自由,侧重行为无价值而非结果无价值。从具体主张看,风险刑法理论试图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层面的扩张来控制风险,化解风险社会的危机。刑事立法层面的扩张主要体现为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比如增设预备犯、着手犯、行为犯、持有犯、危险犯,预备行为的独立化,未遂行为的既遂化。刑事司法层面的扩张主要体现为归责原则和因果法则的扩张。比如严格责任的适用。客观上,这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层面的扩张使得犯罪圈全面扩大。可见,较之于传统罪责刑法,风险刑法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具体主张都有了明显的突破。
因此,风险刑法理论实际上披上了新式的外衣来解决原先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现有的社会架构和法律制度下是可控的,并非是风险社会中出现的“风险”概念。危险驾驶行为通过刑法修正案得以入刑并不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推断,而是以传统社会危害性作为理论支撑。
二、对危险驾驶罪相关概念分析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刑法理论的争议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危险驾驶行为入刑已经是不争事实。因而对危险驾驶罪的讨论需要转向对其科学性的修正上来,以期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并维护我国整个刑法体系的稳定和正义。
(一)危险驾驶罪主观形态的争议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一直是学界争论所在。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的危险驾驶行为会给公共安全造成一定的危险状态,却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一危险状态的发生。[2]也有少数论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例如,冯军教授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针对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饮酒后,虽然行为人事实上已经因为醉酒而处于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状态,却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自己的醉酒驾驶行为会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或者已经预见自己的醉酒驾驶行为会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却轻信自己还能够在道路上安全驾驶机动车,轻信自己的醉酒驾驶行为不会危害公共安全,因而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了机动车,却过失地造成了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
从认识部分来看,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员在驾驶机动车前必须通过系统学习取得交管部门核发的驾驶证,因此危险驾驶行为人完全应该认识到其危险驾驶行为一定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危害后果。
从意志部分来看,对危险驾驶行为人主观状态评价的时间点应回溯至行为人开始实施行为的时间点。既然行为人应该认识到其危险驾驶行为一定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危害后果,并在清醒的认识下仍然让自己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实施刑法规定其他危险驾驶行为,那么其对社会危害后果的发生至少是一种放任的状态。
(二)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危险犯是指以实施危害行为并出现某种法定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刑法之所以将危险驾驶罪规定为危险犯正是因为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公共危险性,一旦实施完毕就有可能对道路交通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侵害。
就危险驾驶罪而言,其理应属于抽象危险犯。理由是:具体危险犯是以发生刑法条文规定的具体危险作为其构成要件的。一般而言,构成具体危险犯不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要求的危险行为,而且还要求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认定该危险行为是否足以造成刑法条文规定的某种特定的危险状态。而对于抽象危险犯而言,这种特定的危险状态及其程度基本上是由立法者加以判断的。法官在通常情况下只需要认定存在符合构成要件的危险行为,而无须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是否实际发生了特定的危险状态,从而直接认定抽象危险犯的成立。
(三)危险驾驶罪中“道路”概念的厘清
“道路”一词规定了危险驾驶行为的空间范围。只有在道路上实施的危险驾驶行为才构成危险驾驶罪。关于“道路”范围的界定存在着广义上和狭义上的解释。从对公众法益保护和约束危险驾驶行为出发,需要扩大道路的解释范围,将更多的通行场所纳入“道路”的范畴。从刑法审慎和正义出发,则需要严格界定道路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我国交通的实际情况,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具体来说,危险驾驶罪入罪标准中的“道路”应该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1.通行人员和车辆的不特定性
通行人员和车辆的不特定性体现了道路作为公共交通方式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就是任何人和车辆都可以在道路上通行而没有特殊的限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表现在空间范围上,也表现在时间范围上。由于交通通行状况复杂多变,对一条道路上通行人员和车辆的不确定性认定应当结合具体的情况来看。
2.公共性
公共性一方面表现为公众具有使用和通行的权利,另一方面表现为其公共服务性和公共权力的参与。公众使用和通行的权利与不特定性重合,指的是不特定的公众和车辆可以在道路上通行。公共服务性是指其本身的作用是服务于不特定的公众和车辆通行需要的,这里的服务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公共权力的参与性是指其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子,即公权力对其施加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3.具有一定的通行流量
具有流量性是在指供不特定人员和车辆通行的公共道路上,通行的车辆和人员应该具有一定的流量。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由于地势、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段的道路常年没有任何人员和车辆通行,其通行流量为零(这里忽略掉极其少数的通行情况而作一个总体的估算)。在这样的路段上,如果当事人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其行为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后果,但是这种社会危害后果几乎不会对不特定的人员和车辆造成损伤,也不会危及不特定人的法益。对这样的通行流量基本为零的路段,不能认为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
(四)危险驾驶罪中“机动车”概念的科学界定
危险驾驶行为中的驾驶都必须是驾驶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常见的有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同时该条还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使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电动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GB1776——1999)(以下简称“电动自行车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不大于20 km/h,整车质量不应大于40kg。根据这项电动自行车国标规定,实践中也有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以危险驾驶罪进行了处罚。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危险驾驶罪的设置情况,超标电动车不适宜纳入机动车的范围,理由如下:
1.机动车法律界定标准不明确
危险驾驶行为入刑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刑法上的不利后果带给当事人的不仅仅是人身自由的丧失还有一系列的社会负面效应,实施刑罚制裁更需要谨慎。如果仅凭规范性的文件而法律上没有足够的依据,就将超标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的范围,无疑是不合理地扩大解释了修正案中机动车的含义,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其法定性和正义性难以令人信服。
2.社会对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认定属于非机动车
对于电动自行车,不论超标与否都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准入程序。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不同的省市有各自不同的规定。但在全社会对电动自行车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之前,根据电动自行车国标就将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的范围让社会公众难以接受。危险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在实践中也没有认识到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而又故意为之的主观故意。让其承受刑罚上的危险驾驶罪后果是不恰当的。
三、对我国设立危险驾驶罪的反思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将追逐竞驶、醉驾等四种危险驾驶情形纳入了刑法的规制范围,其社会效果不言而喻。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刑法更是一柄双刃剑。惩治恶和侵害善总是相伴相依的。
(一)对危险驾驶罪法定刑的反思
对危险驾驶罪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法定刑上,认为法定刑偏轻。刑法修正案是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法学理论的演进而科学制定的。危险驾驶罪的入刑的确为人们出行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由于是新增罪名,规定不免过于简单、粗略,特别是在刑罚上,只有“处拘役,并处罚金”及“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与其所保护的法益——公共安全不相适应,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立法,我国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设置确实过轻。大多数学者主张提高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以保证处罚的力度和罪名设置的合理性,保持整个刑法量刑体系的合理性。
(二)危险驾驶罪与行政法的衔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认为,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要与修改后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防止可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同时公安部却出台相关文件直接规定对于符合危险驾驶条件的一律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也采取和公安部相近的态度,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一般都向法院提起公诉。我国危险驾驶罪界定的性质是抽象危险犯。行为人一旦实施立法者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就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
1.行政处罚在程序和消极后果上的优势
在危险驾驶行为入刑之前,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适用普通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相比,行政处罚程序快捷、高效,能够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从消极后果上来看,刑法施加的消极后果远远严重于行政处罚,这是与刑罚的严苛性和惩治犯罪的严厉性密不可分的。虽然行政处罚也可以暂时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但是其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和刑法施加的消极效果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受到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可以在处罚之后继续融入社会而不会遭受很多的压力,而受到刑事处罚的当事人则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会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压力,而且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交叉感染的风险。
2.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适用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于危险驾驶罪是否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适用。虽然在立法过程中,学者提出对于醉酒入罪增加“情节严重”的限制条件,但是没有被采纳。刑法修正案八为了避免出现歧义还特意调整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表述顺序。但这些并不能说明立法者就排斥了危险驾驶罪适用“但书”的规定。
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后果不大且当事人认罪态度较好的,可以适用行政处罚程序,而不是千篇一律以危险驾驶罪入刑进行处罚。虽然这些做法目前只是个别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但也是各地在适用危险驾驶罪时做出的有益探索。
结语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虽然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公众的期许,但并不是风险社会理论下我国刑法向风险刑法转变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公民自由权保障都是首要的。危险驾驶罪的设立还存在不少概念模糊不清的问题,为司法实践带来了一系列的操作问题,还需要对该罪名进行一定的补充和修正,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并不是一味地加大处罚力度,通过刑法的威慑力来遏制危险驾驶的行为,而是让刑法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在公众脑海中形成不会触碰的红线。鉴于刑法的严苛性和其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在一些情况下还要充分发挥行政处罚的优势,针对危害不大、情节轻微的危险驾驶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从而更好地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回归危险驾驶罪设立的本意和初衷。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6-17.
[2]赵秉志.“醉驾入刑“专家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7-151.
(责任编辑 杨卫宏)
Understanding of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and Reflection on the Law Enforcement
ZHA Hao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road" and "motor vehicle" involved in th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author’s views are put forward, in the hope that the judicial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s can judge th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more reasonably and scientifically. In enforcing the criminal law,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protect citizens' rights of freedom, avoiding biased or negative evaluation on them.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appropriate us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instead of the criminal penalty method can better reflec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formulating the law related to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risk society; road; motor vehicl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2018-06-26
查浩(1990- ),男,安徽宣城人,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科员,硕士。
10.13685/j.cnki.abc. 000355
2018-09-18 10:23:2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242.Z.20180917.1443.001.html
D924.3
A
1671-9255(2018)03-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