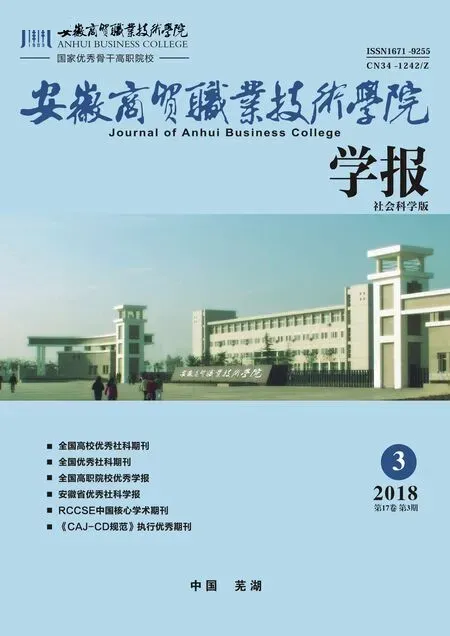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制度研究
董再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制度研究
董再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学院,广州 511365)
免征额是个人所得税税制要素的关键变量,其标准确定和每次调整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免征额可以采取起征点式、固定式和递减式三种形式,具有维持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支出、减少税收管理成本以及维护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功能。通过梳理我国个税免征额制度的调整历程和调整逻辑,发现目前我国的免征额制度存在标准确定依据不科学、调整时间不及时、调整缺乏严肃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根据基本生活支出需要和个税征税面、实施免征额指数化制度、建立专项扣除制度、建立以已婚和未婚纳税人为纳税单位的免征额制度的政策建议。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专项扣除;指数化
免征额作为个人所得税实现由调节性税种向大众性税种转变的关键变量,在2018年的“两会”上,再次受到高度关注。全国工商联提出将免征额提高到7000元,将最高边际税率从3%~45%降至3%~30%;致公党中央、农工党中央提出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并在税收优惠中增加生育二孩家庭的税收激励;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2018年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1]
一、免征额的主要形式和理论功能
(一)免征额的三种形式
免征额是个人所得税必不可少的税制要素,所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都设置了免征额。理论上,免征额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起征点式免征额,即应税所得没有达到起征点时不纳税,一旦超过起征点,需就全部所得征税。这种形式的缺点是当应税所得额达到起征点时,边际税率超过100%,这样,收入的少量增加导致税额的更大增加,收入高的纳税人税后收入反而减少,从而产生“收入禁区”。收入禁区的存在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同时也刺激纳税人采取各种方式避税,从而加大管理难度,因此,实践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起征点式免征额制度。
二是固定式免征额,即应税收入没有达到免征额时,无须纳税,一旦超过免征额,仅对超出部分征收个税。这种形式避免了个人的“收入禁区”,维护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取了固定式免征额制度。
三是递减式免征额,即当应税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免税额逐渐减少,直至为0。不少国家同时实施固定式和递减式免征额制度,如美国联邦个税2015 年个人免税额为4,000美元,单身报税应纳税所得额从 258,250 美元( 起点阈值) 开始,每增加 1250 美元,个人免税额就减少 1%,当个人收入达到 380,750 美元( 终点阈值) 时,免征额为0。[2]
(二)免征额的基本功能
1.维持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支出。维持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是免征额的核心功能,实现纳税人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不纳税是免征额的基本价值。因此,如果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支出发生变化,客观上就要求免征额也随之变化。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支出是不断增加的:一方面,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层次的提升,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的项目不断增多,在物价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不断增长也使原先免征额的实际货币购买力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原先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服务改由主要依靠个人提供。这都导致居民个人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不断增加,进而客观上要求免征额应该适时调整,决不能固定不动。
2.减少税收管理成本。免征额的实质是为个人所得税制增加了一个零税率的税档,相当于免征额的应税所得适用零税率。这就意味着,只有收入高于免征额的纳税人才需要进行纳税申报,进入征税机关的管理视线和范围,接受征税机关的税务管理。这样,国家就可以通过免征额这个阀门的调整,将申报者的数量控制在征税机关的管理能力范围之内,而将那些数量众多但税收贡献小、征收成本大的纳税人排除在税务管理范围之外,从而达到减少征税机关的管理压力、提高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目的。就我国而言,工薪阶层数以亿计,2016年城镇就业人数高达4.2亿人,如果不论收入高低,全都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资源、征管能力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通过设置免征额这个门槛,可以将收入在免征额以下的低收入阶层排除在税务管理之外,进而使税务管理重点聚焦于免征额之上的纳税人。
3.维护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公平原则是制定税法应遵循的最高原则。对税收公平的理解,有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受益原则是根据纳税人的受益来决定缴纳的税收,但由于纳税人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收益难以量化,因而受益原则很难执行,实践中依据受益原则制定的税种很少。能力原则是根据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来决定纳税,纳税能力强的多交税,反之则少缴税,衡量纳税人能力高低的指标主要有纳税人收入、财产和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因此实践中主要有对收入征收的所得税、对财产征收的财产税和对支付能力征收的商品税。税收公平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具有相同收入的纳税人应当缴纳相同的税收,纵向公平是具有不同收入的纳税人应当缴纳不同的税收。显然,免征额制度将社会划分为纳税阶层和非纳税阶层(个人所得税),使得收入在免征额以下的纳税人免于缴纳所得税,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实施累进税率征税,从而维护了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二、我国工薪所得税免征额的调整历程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工薪所得税免征额的调整历程
新中国刚成立后,全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了《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设置14个税种,包括具有个人所得税性质的薪给报酬所得税和利息所得税,但薪给报酬所得税事实上没有开征,利息所得税由于收入极为有限,也于1959年停止征收。自此之后直到1980年,我国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
1980年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免征额为每月800元,根本目的是调节来华工作和开展业务的外籍人员的过高收入,实质是针对外籍个人征税。因为当时中国居民月工资不到100元(1981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4元),对于每月800元的免征额,完全没有纳税之虞。因此,个税征税面小,收入甚微。[3]
1986年,国内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开始扩大,一些个体工商户、企业经营者、演员等特殊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干部、职工。在此背景下,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前者的纳税人为城乡个体工商户,以收入总额扣除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之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适用7%~60%的十级超额累进税率;后者的纳税人是在中国境内居住、取得达到规定纳税标准收入的公民,免征额为400元/月,各地根据经济发达程度略有差异。
1993年,中国实施了全面税制改革,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税制体系。全国人大合并了上述“三税”,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分类课征制,共设置11个税目,工资薪金所得实行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免征额从每月400元提高到800元。
2006年为缩小征税面,将免征额从800元/月提高到1600元/月。此次调整争议很小,一方面是因为酝酿时间较长,从1993年到2000年,居民消费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免征额没有相应调整,致使纳税人数从1994年的956.5万人次上升到2000年的6000多万人次,增加了6倍多,因此2000年就开始出现调整免征额的呼声。[4]另一方面,发达地区事实上上调了免征额,2004年和2005年时,东部主要城市免征额都超过了800元,如江苏、浙江分别是1200元和1500元,广州、深圳、南京是1600元,厦门、嘉兴是1500元,等等。[5]
2008年,政府仅时隔2年就将免征额提高到2000元。此次调整的背景是,2007年我国CPI同比上涨6.9%,创下10年来历史新高,如果不相应调高免征额,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会随物价上涨而加重。而将免征额确定为2000元,依据是保证纳税人基本生活支出的需要。
2011年再次将免征额提高到3500元。此次调整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第一次审议确定为3000元,是按照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及就业者人均负担系数,再参考前几年的增长比例确定的。第二次审议确定为3500元,进一步考虑了前瞻性和因未及时调整而对居民造成的损失,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面。调整后,工薪收入者纳税面由28%下降到7.7%,纳税人数由8400万人减至2400万人,约6000万人将不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我国免征额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工薪所得“免征额”历次调整过程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免征额的设定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免征额是参照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平均消费支出和赡养系数、并适当考虑征税面和前瞻性确定的;二是对所有纳税人实行统一、相同的免征额扣除,而不区分纳税人家庭负担、所处地域以及其他个体特征;三是相对固定,不逐年调整,而是将若干年应当调整的免征额数量集中起来一次调整完成。这种模式虽然计算简单、征管便利,但必然危及税收公平,完全不利于发挥免征额的内在功能。
1.免征额标准的确定依据不科学,难以实现免征额的基本价值。首先,免征额具体由哪些项目组成、各项目的内部结构是什么,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来支撑,只能根据“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来估算。其次,免征额的基本价值是实现“基本生活费用不课税”,因此免征额应该考虑每个纳税人的实际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情况,覆盖全部生活成本,而不应以人均平均消费支出和平均赡养情况来确定,因为平均数可能掩盖了纳税人真实的基本生活费用支出,纳税人实际的基本生活费用必然大于或小于根据平均基本生活费用支出确定的免征额,从而导致在收入水平相同情况下,基本生活支出需要少的纳税人的消费支出得到了完全甚至超额扣除,而基本生活支出需要大的纳税人的消费支出却没有得到充分扣除。尤其是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纳税人实际基本生活费用对平均数的偏离更大,超额扣除和未充分扣除的现象更加严重,这既违背了免征额对“基本生活费用不课税”的基本价值,也违背了按能纳税的税收公平原则。
2.免征额的调整时间不及时,难以及时反应纳税人基本生活支出的变化。免征额第一次从800元/月调整到1600元/月,经过了13年;第二次调整到2000元/月,经过了两年半;第三次调整到3500元/月,经过了3年。2011年之后至今经过了七年,免征额一直保持在3500元/月。这种累积式调整将多年应该调整的免征额集中以来,通过一次调整完成,必然出现一些年份基本生活费用支出超额扣除,而另一些年份又出现扣除不及时。比如,2008-2011年免征额为2000元/月,而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却由1845.71元/月上升到2011年的2451.0元/月,前两年出现超额扣除,而后两年则扣除不足。
3.免征额调整缺乏严肃性。我国个税的免征额经历了三次调整,但是否调整以及调整多少,均缺乏严格依据,基本上受舆论影响很大。而从世界各国来看,一般都建立了个税免征额的自动调整机制,即一般随着CPI进行年度自动调整,因为通货膨胀会使所有货币形式的收入或支出“虚增”,因而导致在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将原本不需要纳税的低收入阶层推入到纳税的行列,原本适用低税率的纳税人推入到高税率级次;同时,通货膨胀会使累进税率表级距的真实价值降低,即税率表级距狭窄化,纳税人将会有更多的收入被推进至其原本不适用的高税率档次,税率表的总体累进程度会提高。
三、完善我国免征额制度的建议
虽然我国早在“九五”发展规划中,就提出了“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目标,但时至今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除了税制要素设计的困难外,更大的困难来自操作层面。当前,自然纳税人单一纳税号码制度、全国统一的自然人涉税信息系统、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甚至尚未启动建设,可以说,在现有的税收环境下,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依然困难重重,短期内只能通过完善包括免征额制度在内的各种微调改革,来最大程度地发挥个税的内在功能。
1.根据基本生活支出需要和个税征税面,确定免征额。免征额的确定,一方面要使纳税人基本生活支出需要不纳税,另一方面要考虑税务机关征管能力。首先,应完善规范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目前,我们主要以“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来反映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水平,但这一数据目前存在不少问题,如其中的住房支出与大众感受明显偏低;有的省只公布该数据的平均数,没有公布不同收入级次的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个别省甚至没有公布等,因此,应对这一数据库进行完善规范后,作为制定免征额的参考和依据。其次,以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最高的地方为参照物,在全国实施统一的免征额标准,以确保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不纳税。再次,要考虑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并据此确定征税面,进一步确定免征额,防止免征额过低、纳税人数过多导致税务机关无法应对,或者免征额过高、纳税人数过少而浪费征管资源。
2.实施免征额指数化制度,包括免征额的指数化和税率等级收入阈值的指数化。理论上的免征额应因人而异,按照纳税人实际基本生活费支出予以确定,但囿于当前税收环境,仍然采取固定免征额制度,同时按照通货膨胀率指数化对免征额和税率等级收入阈值进行调整。为了避免调整的随意性和过于频繁,可设置调整阀值,只要通货膨胀率累积达到一定水平如5%时就予以调整免征额。同时,为了避免提高免征额导致个人所得税的累退性,可借鉴美国做法,对高收入者实施递减式免征额。如考虑对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0000元/月的纳税人,每超过1000元,法定免征额减少2%,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30000元/月时,免征额递减少至零,这就避免了免征额调整时的“双刃剑效应”。
3.建立以专项扣除制度为补充的免征额制度。专项扣除制度是指对法定的基本生活项目支出,准许纳税人据实申报扣除。显然,专项扣除制度是对固定式免征额缺陷的矫正,体现了纳税人基本支出的个体特征,维护了按能纳税。目前,虽然我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专项扣除制度,但许多基本支出项目如五险一金、国债利息收入和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收入、慈善捐款(应纳税所得额的30%为限)、商业健康保险支出(2400元/年)等,允许纳税人据实申报扣除,具有专项扣除的性质和功能。但是,目前这些扣除项目和标准都应进一步优化。对扣除项目应设置最高扣除限额,超过限额的专项支出不允许扣除,这既维护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也挤压了纳税人纳税筹划空间。
4.建立以已婚和未婚纳税人为纳税单位的免征额制度。建立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课税模式,虽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但税制设计复杂,税务部门需要采集、核实纳税人家庭信息,这在当前我国人户分离的流动家庭逐渐成为家庭类型重要形态的背景下,难度很大;另外,由于家庭合并申报比个人单独申报获得的税收利益大,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课税模式可能对个人的婚姻选择产生影响。因此,当前权宜之计可以在总体上将纳税人分为已婚和未婚两大类,既不按家庭的真实规模进一步具体化,也不采取家庭联合申报这种相对复杂的操作。在这种大致分类下,对于已婚纳税人,假定纳税人为四口之家,可按照标准的1.5-2倍扣除,未婚单个纳税人则按标准扣除。[6]
5.在统一免征额的基础上,考虑省域差异。在全国统一的基础上,运用其他扣除项目来缓解地区不公。目前我国可以并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政策工具的就是住房公积金政策。如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12%,免税缴存基数不得超过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照此计算,2016年免税公积金为每月5288.4元;杭州市从2017年7月1日起,单位和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税前扣除限额为每月2638元(年平均工资为87921元),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因此,灵活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制度可以平衡个人所得税地区差异。
[1]牛绮思.个税起征点怎么调?得找一个平衡点[J].中国经济周刊,2018(10):76-78.
[2]曹桂全.美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4):84-96.
[3]赵仁平.近现代中国个人所得税功能的历史变迁[J].现代财经,2010(10):86-92.
[4]李林君.中国个税工薪所得“免征额”调整逻辑及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16(11):83-88.
[5]罗昌财.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11):58-62.
[6]余显财.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制度化调整:长周期、固定式[J].财贸研究,2010(5):84-89.
(责任编辑 夏菊子)
Research on the System concerning the Exemption Amount of Salary Income in China’s Personal Income Tax Collection
DONG Zai-ping
Exemption amount is the key variable in personal income tax system. Every time the criteria for the exemption is re-determined or the exemption amount is adjusted, it will arouse widespread attention. Technically, the exemption amount can be decided upon the minimum threshold, or according to fixed percentageor be diminishing. It has functions of maintaining taxpayers' basic living expenses, reducing the cost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aining horizontal as well as verticalequity. By combing the adjustment process and adjustment logic of the system of personal income tax exemption amount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ystem, such as the unscientific determination standard, the untimely adjustment time, the lack of seriousness in the adjustment,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xemption amountshould be determinedbased on the needs of basic living expenses and the number as well as type of taxpayers,an exemption amount indexation system as well as a special deduc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taxpaying units should bedivided into married and unmarried taxpayers.
personal income tax; salary income; exemption amount; special deduction; indexation
2018-07-03
董再平(1970- ),男,湖南衡阳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财政税收理论与实践研究。
10.13685/j.cnki.abc. 000360
2018-09-18 10:27:4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242.Z.20180917.1450.008.html
F812.42
A
1671-9255(2018)03-00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