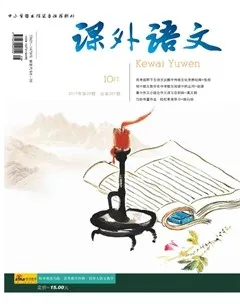方东树《解招魂》析论
【摘要】方东树有《解招魂》一卷,收于其晚年完成的诗学理论著作《昭昧詹言》中。方氏认为前人对《招魂》作者以及所招对
象的争论,均未能深究其本事,探寻其旨意。方东树认为,《招魂》是用意隐曲、“全用比兴体”的假托之作,即屈原因楚国之将亡,而托“招魂”之名比其“冀陈忠谏”而望楚国复存之意,实际上是受其自身诗学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方东树;《解招魂》;楚辞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自号“仪卫”,是继“三祖”之后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昭昧詹言》是其晚年完成的诗学理论著作,被称作是桐城派诗话的扛鼎之作。桐城方氏学术文化积淀深厚,楚辞学是其家族传统家学之一。方东树之父方绩,著有《屈子正音》,是楚辞音韵学著作,书中有“东树按”,为方东树辩证之说。方东树有《解招魂》一卷,收于《昭昧詹言》卷十三中。方东树盛赞屈原云:“屈子以忠清之志,发哀怨之思,上览黄虞,下骖箕比,蔚为千古词宗。岂特楚国之良,实系斯文之寄。《离骚》二十五篇,历世作者奉为方圆,并驱六经,藐世独立。”
方东树指出《招魂》篇“数千年文义瞢暗,曾未有确揭其本事者。故或以为原所作以招怀王,或以为宋玉作以招师,是皆泥题目字面而滞会之也。又或以为施之生前,或更执‘去恒干’‘像设’等语,以为确施于死后,尤为寱语不悟。既题曰《招魂》,则此等言句皆本分料语,岂可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而不寻其全文作旨本意邪?”(卷十三/二)方氏认为前人对《招魂》作者以及所招对象的争论,均是拘于题目而仅停留在表层的无稽之谈,而未能深究其本事,探寻其旨意。方东樹在总结批判前人观点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窃意“招魂”者,古之复礼,所亲死而冀其或反,尽爱之道,祷祠之心,甚盛意也。屈子以楚之将亡也,如人将死而魂以去身,冀陈忠谏而望其复存,忠臣之情,同于孝子,故托“招魂”为名而隐其实。其称名命意,乃以比体为赋体,犹荀子《请成相》也。陈季立略悟其旨,而又以确为招原而兼托讽,则犹惝惚弗察也。且以为宋玉招师,则中间所陈荒淫之乐,皆人主之礼体,非人臣所得有也,况又可谓玉之有所讥于原乎,益非事实矣。若以为原之招怀王,则前后一起一结,辞意安传安施而不可通矣。吾以为此确为原所作。(卷十三/二)
方东树认为《招魂》是屈原因楚国之将亡,而托“招魂”之名比其“冀陈忠谏”而望楚国复存之意。方氏指出太史公所云“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正是《招魂》之旨。方东树所云“且以为宋玉招师,则中间所陈荒淫之乐,皆人主之礼体,非人臣所得有也”,确为别具只眼之见。郭沫若先生提出《招魂》中“文辞中所述的宫廷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能够相称的”;钱钟书先生指出《招魂》所招的是为猎于云梦为青兕所慑而丧之魂,“《招魂》所夸宫室之美,声色之奢,非国君身份不办,特未必即属楚怀王”。二人的看法显然是受到了方东树的启发。“陈季立”即明人陈第,他在《屈宋古音义》卷三《招魂》题后引张凤翼之言云:“古者人死,则以其服,升屋而招之。此必原始死而玉作以招之也。旧注皆云施之生时,欲以讽楚王,殊未妥。”
陈第认为《招魂》是宋玉招其师屈原之亡魂,他在《招魂》篇后论曰:
《招魂》作于屈原既死之后,张凤翼之言是也……玉慜其师沉于汨罗,其魂必散于天地四方矣。故托巫阳招之,无非欲其魂之反也。其危苦伤悼之情,可想矣!然叙怪诞,侈荒淫,俱非实意,直至“乱曰”数语,乃写其本色。意以原之南征,值王之畋猎,欲引之通途,而王方射兕淹留也。以致道途荒秽,不可以归。江水草木,极望伤心,此江南之可哀者也。原生而惓惓楚国,死而不动心于危乡乎?故以哀江南终之……是此篇之作,悲其师之不用,痛其国之将亡,而托之招魂。意谓外又怪诞,内又荒淫,怪诞暗指张仪辈之变诈吞噬,荒淫则楚之所以乱也。
方东树所说的“陈季立略悟其旨”,即是指陈第此段文字中“叙怪诞,侈荒淫,俱非实意,直至‘乱曰’数语,乃写其本色”;“痛其国之将亡,而托之‘招魂’”。方东树当是受陈第的启发,提出《招魂》非真招魂,而是假托之作,是托“招魂”为名而隐其实的见解。然而,陈第和方东树对于《招魂》所隐之“实”的看法又不同,陈第认为所隐之“实”为宋玉悲屈原之不用,痛楚国之将亡;而方东树理解的欲隐之“实”是欲复存君兴国的忠谏之思。方东树在《解招魂》中进一步结合诗句分析:
其起曰“长离殃而愁苦”,结曰“哀江南”,一意贯串,文义隐晦而又极明豁。“长离殃”者,已永谪于江南也。“愁苦”者,非为一己,乃哀国事也。其哀其愁苦何也?哀其外多祟怪,内有荒淫,其死征如魂已去身而不知反归也。此原放于江南,浮夏上沅时所作,故望其复存;而已在江南,目极江枫千里,抱此哀痛也。既讽其荒淫,而复以荒淫招之,何也?曰:此于言为从顺,理体当然也。王者之居,非同俭陋,既言其外之害,则不得不陈其内之乐,题面当如是也。而极其奢靡,则荒淫意亦在言外。此文用意既隐曲迷离,全用比兴体,岂可以寻常正言直谏之义例之乎?(卷十三/二)
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方东树认为《招魂》是用意隐曲、“全用比兴体”的假托之作,实际上是受其自身诗学观念的影响。其《昭昧詹言》多次以“魂”“魄”论诗:“所谓魂者,皆用我为主,则自然有兴有味。否则有诗无人,如应试之作,代圣贤立言,于自己没涉”;“魂气多则成生活相,魄气多则为死滞。”(卷十八/二)方东树认为有“魂”之诗是主观之性情蕴藏于客观之中,是有象外之兴、言外之味的诗;而有“魄”之诗则是客观的典故、藻饰掩盖主观之性情面目的诗。可见,其所谓诗之“魂”“魄”乃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而其所云之“魂”,即是强调诗的比兴手法。方东树还多次强调“情有余味不尽”的“兴在象外”,即在具体的比象之外有所寄托,言在此而意寄于彼,才能尽余味不尽之妙。缘此,方东树认为《招魂》之作并非是真正用于招魂的应用文,而是屈子所作托兴寄意的文学作品。其《解招魂》又云:
意原初放时,适值王之猎梦,即事寄意,兼著其时也。其曰“引车右旋”,古者右为正为贵,左为邪为贱。故王制诛左道,秦汉发戍卒,取闾左。原自言右骋先驱,欲抑其邪骛,顺若以通于荡平正直之大道,即所谓‘来吾道夫先路’也。惟“君王先发兮惮青兕”,以一句当猎事一大段。虽古人笔力强,文字不拘,究似迫而不备。详思未解,疑有阙文。“朱明承夜”,欲其就明去暗,弃秽改度,而不可再稍淹缓。假使“皋兰被径”,则大道芜没不可复识矣。又即其所见“江枫”“千里”“目极”“伤心”,即“邱夏”“芜两东门”之意,而终以七字结之。七字作两层:“魂兮归来”,言望王改行率德;“哀江南”三字,言己所在之地,以致意也。此指顷襄王,非怀王也。(卷十三/二)
方东树认为《招魂》乃是顷襄王即位,放逐屈原后不久,适值楚王涉猎云梦,屈原即此事作此篇以寄存君兴国之意。方氏此说当是受陈第之启发,即上所引“意以原之南征,值王之畋猎,欲引之通途,而王方射兕淹留也。以致道途荒秽,不可以归”。此外,方东树又因篇中于射猎一事仅书一句,疑此处有阙文。
清人管同《因寄轩文集》初集卷三中有《读招魂》一文,与方东树之见解颇有相类之处。其文曰:
旧皆谓《招魂》为宋玉作,太史公赞屈原曰:“予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亦原之为耳,岂玉作哉?其文之旨,首言魂魄离散,盖谓故国难安,亦尝有九州相君之志矣……孝子之于亲,天性也;忠臣之不忍离君,亦天命而已矣。其文之中至乱辞之首,乃盛陈楚邦繁盛,则意讥顷襄,犹庄辛论幸臣之旨,父死于秦不思报复,而乃逞声色纵猎游侈陈之,正以见王之不道,而难与有为也。其文辨博闳丽,殊不易晓,故于篇终明见其意曰:魂兮归来,哀江南。君子之居季世也欲他去,则于义难安;欲不去,则其忧不可解,在位而极言之,犹冀其君之一悟也。而为君者,必屏弃放逐,遏其身而杜其口,虽不去,亦何能为哉?则戚戚焉,惟日忧故国之将亡而已矣。”
与方东树《解招魂》一致,管同亦认为《招魂》并非“招魂”之作,而是屈原“忧故国之将亡”所作,意在讥讽顷襄王不思为父报仇。管同指出《招魂》篇文辞“辨博闳丽”,旨意“殊不易晓”,与方东树所云《招魂》篇“用意隐曲迷离”正相一致。管同所云“孝子之于亲,天性也;忠臣之不忍离君,亦天命而已”,与方东树所云“忠臣之情,同于孝子”之语亦如出一辙。管同与方东树同为姚鼐弟子,关系甚笃。从二人对于《招魂》之看法如此相似,可以看出同门学友之间的交流和切磋。
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指明《招魂》为宋玉作之后,直至明代中叶之前,楚辞学者们对此几乎无异议。至明代后期,黄文焕《楚辞听直》首先发疑,林云铭《楚辞灯》发挥黄文焕之说,举司马迁在屈原本传中之论赞:“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定《招魂》为屈原自招其魂。此后从者甚众。清代学者吴世尚、蒋骥、屈复、陈本礼、胡浚源等翕然响应,定《招魂》为屈原所作,直至近世陈子展、姜亮夫等均持此说,可见此说影响之巨。
方东树步遵宋学,标榜朱熹,以卫道自居。其《解招魂》云:“余生平遵信朱子,如天地父母之不敢倍”;“朱子之注《楚辞》,其义理所存,比于孔子删《诗》而无让也”,甚至已将朱熹注《楚辞》与孔子删《诗》等同起来。方东树云:“诗以言志,如无志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若又不解文法变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达意,即成语录腐谈。是谓言之无文无序。若夫有物有序矣,而德非其人,又不免鹦鹉、猩猩之诮。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尝读相如、蔡邕文,了无所动于心。屈子则渊渊理窟,与《风》《雅》同其精蕴。”(卷一/六)方东树指出正是因为屈原内在的“精诚”之志,才能写出如此具有“精蕴”的文字来。方氏又云:“屈子、杜公时出见道语、经济语,然惟于旁见侧出,忽然露出乃妙;若实用于正面,则似传注语录而腐矣。”(卷一/三四)方东树所云“见道语”主要指忠君孝亲,“经济语”则是经世济民,对此要“旁见侧出”,即通过艺术手段委婉曲折地表现出来,否则就是“传注语录”的陈腐说教了。方东树《昭昧詹言》云:
屈子之词与意,已为昔人用熟,至今日皆成陈言,故《选》体诗不可再学,当悬以为戒……夫屈子几于经,浅者昧其道而袭其辞,安得不取憎于人。朱子论柳宗元对《天问》,以为学未闻道,而夸多衒巧之意,犹有杂乎其间。柳此文乃以证屈子者而犹然,况不及柳者乎?(卷一/三三)
方东树认为“诗文以避熟创造为奇”,“熟”即是指人们所习见的。他倡导的“学诗之法”特别强调避熟:一曰“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言语,却又非以艰深文浅陋,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三曰“选字”,必避旧熟,亦不可僻。四曰“隶事避陈言”。(卷一/二八)又,方东树曰:“去陈言,非止字句,先在去熟意:反前人所已道过之意与词,力禁不得袭用;于用意戒之,于取境戒之,于使势戒之,于发调戒之,于选字戒之,于隶事戒之;反经前人习熟,一概力禁之,所以苦也。”(卷九/二)方东树认为《招魂》篇即是非“熟意”的创格之作:“吾读屈子他篇,未暇悉论,窃以创意创格造言,未有佹于《招魂》者也。”(卷一三/二)
综上所述,方东树《昭昧詹言》对楚辞的地位十分看重。方氏认为前人对《招魂》作者以及所招对象的争论,均未能深究其本事,探寻其旨意。方东树认为《招魂》是用意隐曲、“全用比兴体”的假托之作,即屈原因楚国之将亡,而托“招魂”之名比其“冀陈忠谏”而望楚国复存之意,实际上是受其自身诗学观念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郭沫若.屈原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陈第.屈宋古音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管同.因寄軒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0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附 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ZW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欣,女,1983年生,黑龙江萝北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