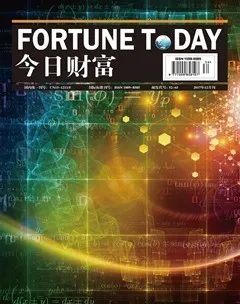现今中国民法典编纂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的法制实际都是在借鉴和继受大陆法系法制,特别是德国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梳理罗马法的法典编纂观念后,结合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发展,不难得出中国民法典编纂应遵循重体系化建构、重逻辑的法典观念的结论。
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历经近百年,之后经久不衰,其影响意义无与伦比。在当前中国制定民法典之际,重新回顾德国民法典编纂和发展历程,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民法与德国民法的历史关联性
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德国法律制度为模式建立的。当我们回顾德国和中国法律自继受异国法律以来的发展过程时,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其继受的历史意义是何等的深远。
(一)近代中国法律对德国法律的继受
近代中国法制对德国法律的继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翻译德国法律。本世纪开始,在清政府准备法律改制之初,曾大量地翻译了欧洲各国的法律,其中主要是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的法律。如沈家本主持法律修订馆一开始,就翻译了德国的《德意志裁判法》。 这种法律文献的翻译工作无疑对当时中国的法律改制进程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是一种积极的准备。
2.民法典编纂采取德国模式。法律改制后的中国民法编纂最终采取了德国百科全书派模式,即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总则(含人法)、债法、物法、家庭、继承五编制,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民法以德国法律制度为模式发展的基本方向。
3.民法典的主要内容基本来自于《德国民法典》。法律改制后的中国民法典不仅在形式上追随了《德国民法典》,而且还在内容上广泛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内容,特别是总则、物权和债权部分。后者许多规定,包括概念、形式及内容,其实就是完全或部分地取自于前者,其中有些甚至就是直接的移译。
(二)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格局
必须明确,中国大陆法律制度自清末民初以来,始终是循着大陆法系法制的模式构建发展的。虽然1949年中国发生了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废除原国民党政府法律,但这只是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层面采取的必然举措,而法律制度本身的基本取向已无法消除;同样,本世纪初中国法律改制所确定的法律制度模式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故当代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路仍然透着德国民法典的影响。
二、关于法典编纂观念
虽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可以追溯到作为欧洲大陆法系之历史基础的罗马法时代。罗马法上丰富的法典编纂经验,深刻影响了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基本思路和模式。
罗马法上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法典编纂是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所开展的法典编纂。这一法典编纂运动中所产生的法律文本,是奠定欧洲大陆民法秩序的基础性材料。但查士丁尼法典编纂运动中产生的三大法律文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究其原因,是法典编纂活动中贯穿的两种不同观念。
以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为中心的编纂思路代表了一种汇编式、重述式的法典观念。它为法律的实践活动提供“法律在哪里”的答案。而以《法学阶梯》为中心的法典编纂思路,它所要解答的是“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德国民法典在其制定过程中,经过了激烈的学术讨论之后,最终选择了潘德克顿体系。虽然其是建立在在《学说汇纂》的体例基础之上,但是学者们采用抽象的概括式的表达方式,使用的语言相对艰深晦涩但很少存在歧义和疏漏,以追求更加完善的民法体系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严谨的法学概念和高超的法律语言成为了德国民法典的标志性特点。所以潘德克顿学派具有强烈的体系化和学理化特征。这一近代大陆法系所共同强调的体系化和学理化特征的法典编纂观念的精神渊源,则正是自于《法学阶梯》的强烈体系化特征和隐含在这种体系化之后的法典的教科书功能。所以,德国民法典只是采用了《学说汇纂》的体例,而其法典观念,更多地吸收了《法学阶梯》的指导思想。故在德国民法典第一稿草案出台之后,有人评价:这一法典更加像是一本潘德克顿法学教科书而不是法律。对比于中国,我们对德国民法典的继受不仅仅停留在法律文本上,更是影响着我们的民法思维,这显然是延续了德国民法典的教科书特征的法典概念的传统。
应当说,结合前文所述的历史传承的基础,在大陆法系的大背景下,我们仍然应当坚持体系化的民法典编纂理念。就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来说,如今欠缺的,只是一个合适的、严谨地体系,从而能够将现有单行法律结合起来。(作者单位为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