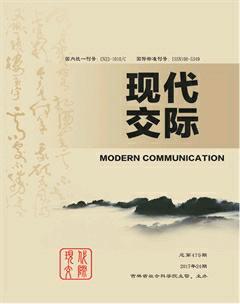鲁迅《墓碣文》的别一种解读
黄权壮
摘要:鲁迅身处大变动、大危机的历史时期。当时绝大多数民众没有受过精神洗礼,而先知先觉如鲁迅者自身也存在某些不足,因此异常孤独、彷徨,这深刻地体现在其前期的作品中。本文以《墓碣文》为基础文本,聚焦“坟” “死尸” “本味” “微笑”等散点,兼顾中国近现代史与鲁迅的人生经历,结合鲁迅其他作品尤其是《野草》部分篇章,作互文式解读,希望从中窥探鲁迅早期的精神状貌。
关键词:“坟” “死尸” “本味” “微笑”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24-0102-02
《墓碣文》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比较短小的一篇,写得很隐晦。从全文来看,它是有情节的:“我”梦中到达一处“孤坟”,坟前有墓碣,碣前碣后均有文字。前面写墓中“死尸”(是一个象征物,并非无生命力),离奇的思维与深切的观察,还歇斯底里般“自啮”,以致“胸腹俱破,中无心肝”,但脸色“绝不显哀乐之状”;碣后写“死尸”“抉心自食”的目的——“欲知本味”,但它陷入悖谬当中:要知道“本味”就得趁新鲜,可是“创痛酷烈”,痛感掩盖了“本味”;若痛定之后则“心已陈旧”,似又变味了。“死尸”似乎认定了别人不能解开它的死结,所以前后碣文都以“离开!”之语驱逐路人。作为平常人的“我”自然希望赶紧离开;就在“我”逃离之际,“死尸”却坐了起来,“口唇不动,然而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1]
梳理文句后,下文聚焦“坟”“死尸”“本味”“微笑”等散点,兼顾中国近现代史与鲁迅的人生经历,结合鲁迅其他作品尤其是《野草》中的一些篇章,作互文解读,希望从中窥见鲁迅早期的心魂。
一、“坟”
鲁迅比较喜欢“坟”。他曾在厦门大学附近的坟丛中拍照,神情自若;第一部杂文集起名为《坟》,“后记”中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2];《野草·过客》里,“过客”执意走向的也是“坟”;除此之外,其他作品还散布着各种各样的“坟”,比如“夏瑜”与“华小栓”各自的坟(《药》),“吕纬甫”那夭折的“小兄弟”的坟(《在酒楼上》)等。至于与“坟”相关的人与事就更多。鲁迅为什么那么青睐这个鲜有人迹、生死交界的地方呢?我觉得原因至少有五个:
第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生命太容易毁灭,而鲁迅的身体又不好,死亡的幽灵常萦心头。
第二,这里安静、孤寂、远离尘嚣,能够让他安抚身心、好好思考。
第三,“坟”常为世人所避忌或遗忘,鲁迅反叛的个性很自然地倾向于与之为伍,而创作上,还可以借助其阴森恐怖的气氛强化作者与周围环境决裂的决心。《墓碣文》主要体现这三点。
第四,“坟”代表死,在特殊心境下,还意味着苦难的终结与人生的解脱。比如《孤独者》里,当“魏连殳”死了之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3];《过客》中,“过客”深有感触地说,“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4],因为“同我有关系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5]。因此,“坟”成为那些他关心、同情却无力助他们掌握命运的人的收容所,成为他艰辛探索路上种种沉重包袱的暂时解脱的中转站。
第五,死与生是辩证的,“坟”代表死,却也意味着生,当旧事物被埋葬之时,正是新事物诞生之日。所以,即便“过客”的路的终点是“坟”,可仍要探寻“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6]
鲁迅消灭旧世界的决心是彻底的。他一再表示,连自己也应该像旧事物一样,随旧世界一同消亡。“过客”说,若给他布施的人不灭亡,便要“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7];《野草·题辞》里,他欢呼,“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8]。马克思说过,哲学的消灭正是哲学的实现。[9]从这个意义上说,“坟”暗含着鲁迅作品及其自身价值的实现。
二、“死尸”
将人格由“一”分拆为“二”或“三”的模式在《野草》中普遍存在,比如“我”与“影子”(《影的告别》),“我”与“死火”(《死火》),“我”与“蜡叶”(《蜡叶》)等。这让人联想到精神分析法中有关“自我”“本我”与“超我”的观点。以此来解《墓碣文》,可以设想,“我”“死尸”和化为尘土时微笑的“死尸”分别对应着“自我”“本我”和“超我”。
首先,“我”是一个略显怯懦的凡人形象。这不能说跟鲁迅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单从作品来看,类似的形象活躍在鲁迅的作品中。比如《祝福》里用模棱两可的话搪塞“祥林嫂”的新派知识分子;《故乡》中那个面对“豆腐西施”表现得拘谨尴尬、支支吾吾的回乡知识分子;甚至在鲁迅晚年写的半散文半小说《阿金》中,“我”也是一个既讨厌麻烦制造者“阿金”那副洋奴相却又选择忍气吞声甚至自责多管闲事的都市知识分子;等等。生活中,鲁迅孤僻傲立,不善交际,面对生人尤其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下层群众时,常表现得很拘束、木讷、卑弱,找不到共同话题。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鲁迅早年跟工农阶级离得比较远。
其次,“死尸”眼光独特、思维怪异,“欲知本味”而“抉心自食”以致“胸腹俱破”,但又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这很符合鲁迅个性中沉郁、内省、隐忍的一面,算是鲁迅的“本我”。将“死尸”这个恶心形象加以正面塑造,以丑为美,除了受波德莱尔散文诗的影响,更是鲁迅的个性使然。
不奇怪的是,在鲁迅的作品中,凡是跟他精神相通的大多是些世所难容如猫头鹰类的“枭蛇鬼怪”[10],比如“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11]的“范爱农”(《范爱农》),“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目光如“两点磷火”的“黑衣人”[12](《铸剑》),“眼光阴沉”[13]、穷困潦倒、满身伤痕、状若乞丐的“过客”(《过客》),“两眼在黑气里发光”[14]的“魏连殳”(《孤独者》),等等。
最后,据“死而有灵”的说法,化为尘土时微笑的“死尸”应是“死尸”的灵魂。从广义来说,人的劳动成果就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于作家而言,人走了,作为其精魂的凝聚——作品会长存。“死尸”相信自己在灰飞烟灭之后会获得世人的认可,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超越懦弱的凡俗的“自我”和焦头烂额、身心俱创的“本我”,成就“超我”。
让人感慨的是 “自我”和“本我”是如此背离,而“超我”的实现又是以“本我”的消灭为前提,现世的幸福被推到了身后,这是鲁迅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
三、“本味”
“本味”指什么呢?应是“死尸”对自身精神特质的认知。只有知道“本味”是什么,才能探寻“为什么”,然后寻求自我解救之路。可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鲁迅难以解答的。
第一,“死尸”身处人间边缘,它是孤独的,自我封闭的,人间的很多信息很难真实地充分地抵达荒冢。现实中,鲁迅真正接触的大都是一些底层小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彷徨中的一群;对于工农阶级,虽充满同情,但有较大隔阂,对于如何激发他们潜藏着的“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的能量,也不清楚。鲁迅还难免带着知识分子的孤傲和“驱逐旁人”[15]的心理;整个一部《野草》就是一个发挥到极致的精英文本,弥漫着的虚无、感伤乃至颓靡气息,高度晦涩与私人化的措辞,让人望而却步。因此,他是难以将理想安放在现实基石之上的。
第二,它的思维方式是两极生硬对立的,比如文中的“狂热”与“中寒”“天上”与“深渊”“一切眼”与“无所有”“无所希望”与“得救”“不以啮人”与“自啮其身”“答我”与“离开”等,没有中间状态。这当然表示它独特的视角、深邃的思考和彻底的品格,可是,非此即彼的思维也令它时时翻卷在动荡不定的情感海洋中,掏空自我,终至“殒颠”。
第三,它认为,所谓“本味”就是自己“抉心”瞬间的“味道”,要求精准。其实,“本味”应是相对的。套用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定理”,要绝对真确地体尝“抉心”瞬间的“味道”,不管是剧痛之中,还是痛定之后,都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7]。因此,即便真能获取“本味”的官能感觉,不突破个人主义藩篱,缺少先进阶级的历史视角,还是得不到“真味”。
四、“微笑”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句话是全篇乃至整部《野草》阴冷沉闷的气息中罕有的闪光。虽然,鲁迅并不知道自己的“本味”是什么,但他知道每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总会产生一些先知先觉先行者;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他们难以摆脱的命运。鲁迅所推崇的“摩罗诗人”“旧轨道破坏者”[18]如尼采、卢梭等,往往生前都得不到认可,死后才响遏行云,成为民族精神的独特标记。
鲁迅隐约明白到自己跟这些杰出人物有亲缘关系,隐然树起衡量自己价值的历史坐标,从而在孤獨的人生中存留一份希望和信心,默默领受人世加诸身的种种哀伤苦痛。只是,这种预约式的慰藉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孤独的境况与不断过度损耗的身心,这篇短小的《墓碣文》预示着伟大的鲁迅终难免早逝!
参考文献:
[1][3][4][5][6][7][13][14][18] 鲁迅.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10][11][15] 鲁迅.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8] 鲁迅.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9][16][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鲁迅.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