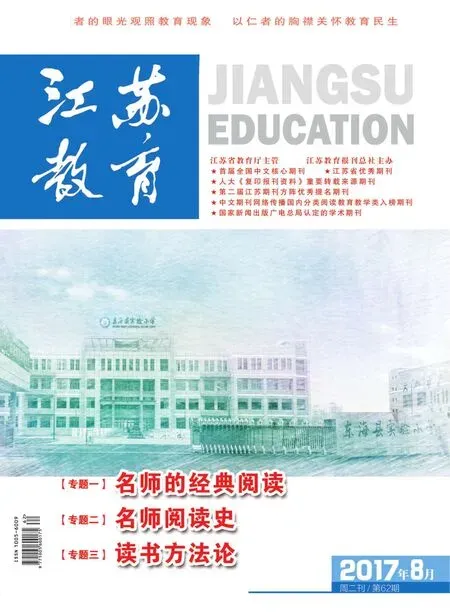重构儿童的博物学精神
——读乔治·布封的《自然史》
曾宝俊
重构儿童的博物学精神
——读乔治·布封的《自然史》
曾宝俊
·推荐理由·
《自然史》是一部传世博物志,全书包括了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在《自然史》中,乔治·布封综合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做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破除宗教迷信,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布封对现代科学的一大贡献。法国思想家卢梭对《自然史》这样评价:“布封那纯艺术家的人生态度,在《自然史》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他用异常平静、悠然自得的语调,歌颂自然界中所有重要的品物,呈现出造物的尊严和灵性。”
这本书在物种起源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布封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而变异,这些观点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着最直接的影响。《物种起源》的作者、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称布封为“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坚持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指出地球与太阳的许多相似之处,地球是冷却了的小太阳,地球上的物质的演变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最后有了人类。《自然史》这部丰碑式的著作,是启蒙运动中的一把利剑,给神学阴云笼罩的欧洲天空一道强有力的闪电。
布封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皇家植物园的主任。作为法兰西学院破格提拔的院士,他毕生精力都花在经营皇家花园上,闲来无事,就用40年时间写成这么一部巨著。在书中,乔治·布封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了地球、人类以及其他生物的演变历史。乔治·布封一生游历、观察、实验、演讲,他如同造物主委派的使者,把万物本原尊贵和神圣的品性展现给世人。
博物学是探究人与大自然关系的一门古老学问,如今已经随着学科的细分而衰落,但它在人类科学文明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很多博物学著作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人应当向自然致敬,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着生命和演化的传奇!万物闪烁灵性,生命演出大戏;每一种动物、植物,如同人类,都在生命大戏中扮演着轻重不同的角色。对于地球的演化和生命的起源,我们因为不了解而倍觉其神秘,可是在布封的笔下,我们阅读之余留下的却是生命最深刻的快感,在此特别推荐这一部历久弥新的《自然史》。
·阅读体验·
新课改以来,小学《自然》课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成了《科学》课。因为冠以“科学”一词,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了,真的是这样吗?这些年来,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科学教育有了大踏步的前进,但那些最优秀的“科学课”似乎和过去的“自然课”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下,很多科学教师对于“博物学”这个词好像还是有点陌生,总以为,博物学就是讲点儿花花草草、鸟兽虫鱼的知识,不过是了解大自然物种的学问。其实,并非如此。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指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由于博物学所涉及的科目纷繁复杂,需要学习的知识看上去似乎永无止境,所以,一个“博”字让大多数的人对于博物学总是抱着高山仰止的态度,不敢亲历其境去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当家长们本身都对博物学望而却步,就更不会去鼓励孩子涉足这门学科。
在西方历史上有三种科学传统:希腊理性科学传统、博物学传统和近代实验科学传统。其中,博物学传统倡导的是人和自然的沟通。孩子的天性就是对身边的一切抱有无止境的好奇,这种好奇会推动他们勇于求知和尝试,从而培养出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孜孜不倦地投入其中。其实,小学阶段的科学教育说到底还处于启蒙阶段,启蒙阶段的科学教育的内容并未跳出“博物学”范畴,依然属于“自然课”,所以,最好的“科学课”和最好的“自然课”当然没有什么区别。
但,如果真要了解博物学,那就得回到200年前了(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那个时候,博物学是一门显学,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布封的《自然史》付梓面世。《自然史》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随后各种译本相继出现,在科学界、文学界和哲学界受到一致好评,当时法国贵族基本是把它当必读书来收藏的。
在《自然史》中,布封以大量实物标本做推论,对当时的自然世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其中,首推他的“唯物论”思想。当时人们以“创世纪”的观点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布封却用科学的笔法把宇宙的历史描绘了出来。书中,布封论述了宇宙、太阳系、地球的演化史。他认为,地球和太阳一样,是由炽热的气体凝聚、冷却而成,地球诞生的时间比《圣经》中的时间要早得多,布封认为地球的年龄至少在10万年以上,而生物则是在地球自身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各种变异现象。他还大胆地提出,人是动物的一属,他在书中说:“如果只注意面孔的话,猿是人类最低级的形式,因为除了灵魂之外,它具有人类所有的一切器官。”
与此同时,他观察大地、研究山脉、考察河川海洋,寻求地表变迁之根源。布封曾经营一座炼铁厂,在离炼铁厂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露天铁矿。工人们在岩层中发现大量完整的菊石、箭石的化石,那些远古时代的海洋物种早已灭绝。大量化石的发现,意味着地球海陆曾发生变迁,这也提供了地球气候变化的证据,由此,布封开地质学研究之先河,当时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对物种起源和地球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布封在他的这本书中写道:“当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的时候,他们确实感到那儿的一切都是新颖的,四足兽、鸟、鱼、昆虫、植物等全都是不认识的,全都是与人们在那之前所见到的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对新物种的命名,成了博物学家首要的任务。布封书中这些真实的记录,为人们了解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料。
如果说,一百年后的《物种起源》奠定了进化论的科学基础,那么布封的《自然史》则为“系统进化论”的形成和发展铺平了道路。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以全新的进化思想挑战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提出了震惊世界的论断:生命只有一个祖先——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而来的。我们如果翻开布封的《自然史》,读一读其中的论述,你会发现,布封虽然没有详细描述物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进化方法,但是他指出:物种是变的,古代物种没有现代多,弱者被强者淘汰,物种受环境、气候、营养而逐渐改变,或者变质,或者变形,或者变异;旧的物种总会被新的物种所取代;物种总是在经历不断消灭和更新的循环过程中……你看,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已然隐约发现了自然界生物之间和物种进化之间“物竞天择”的规律。毋庸置疑,这些观点对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除了极具科学价值之外,《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同样备受瞩目。翻译家郭宏安为本书的中译本写了一则序——《科学与诗的融合》,他说:“如果说布封的《自然史》在科学性上多少已经过时,它在文学性上却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格的壮丽、典雅和雄伟,还有它的细腻而富于人性的描绘,特别是一幅幅洋溢着诗意而又细致入微的动物肖像。”乔治·布封那敏锐、客观、稳健的文笔,准确、简单、清晰、生动的创作风格,经久地矫正着我的文字创作。
我特别欣赏布封对动物形态的描绘,极富艺术感。他介绍这些动物的态度并不完全客观,而是带着一种特殊的主观情感,布封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是那么生动具体、饶有趣味。在布封的笔下,大象温和憨厚、小松鼠善良可爱、鸽子夫妇相亲相爱……他还赋予动物以各种人格:马是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海狸之间和平共处毫无争斗,狼凶残而怯懦,是“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而美丽而优雅的天鹅则被描绘为和平、开明的君主。
在现行的中学教材中有一篇课文《马》,就出自布封的笔下,原文的出处就是《自然史》,布封在文中写道:“人类曾经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他和人类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殊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险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交接时的铿锵之音,喜欢并追随这种声音;在狩猎或赛马时,它则以出众的表现给主人带来种种愉悦。他不会肆意地表现出自己的烈性,而是懂得克制自己的行为,不但屈从于驾驭人的手下,任他操纵,还仿佛懂得察言观色,总能按照主人的表情来选择奔腾、缓步或停止,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你看,优美典雅的语言将科学与文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布封的《自然史》涉及18世纪自然科学的广博领域。我们今天阅读这部200年前的著作,仍然可以从书中透露的细节,从字里行间,体会当时的科学家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发现,而激起的探索热情和难以抑制的喜悦,也包括对于尚未探明的自然现象的困惑。
当然,说到这儿,很多科学教师会说,你说的可是《自然史》呀,跟博物学有啥关系?其实“自然史”和“博物学”是一回事!“自然史”和“博物学”这两个词对应的英文是同一个词,叫natural history。英文history(历史)来源于古希腊语,原本有研究、探究的意思,所以nature history的意思是“探索自然”或者 “对大自然的探究”。近代,日本人将“natural history”翻译成“博物学”这三个汉字,这个词其实更贴切“natural history”的本意。
现代社会虽然科学昌明,知识爆炸,但是知识的性质变了,变成了生产工具,不像200年前那样,是人类纯粹的好奇心的产物。牛顿研究万有引力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个规律能够用于让卫星升入太空,牛顿纯粹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学问而做学问。现代所谓“科研”,只要不是为了推进生产力、不能直接或者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门学科基本上就属于冷门。说得好听点儿,叫“学以致用”;说得不好听,就是科学变成了“经济的婢女”。
从古希腊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是宗教的婢女。后来,科学这个宗教的婢女从宗教里独立出来。但是独立不久,科学就投入了经济和政治的怀抱,成为它们的附庸了。虽然,目前还有科学家在从事一些基础科学研究,看起来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提供研究经费的人很清楚——这些研究发挥用途是迟早的事。说到底,研究科学还是因为有用!
200年前从事博物学研究的那些学者就不是这样。当时人们研究鸟兽鱼虫、花花草草,观察、鉴别,给它们分类、编目,除了陶冶情操,或者专业工作者的职业需要,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为研究而研究,因为好奇而研究,因为喜欢而研究,基于兴趣而研究。正因为如此,博物学渐渐地没落了。
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人类并非靠科学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科技而存活,在其漫长的进化和发展历史中,靠的是博物学知识和传统技艺。从理论上讲,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但近代以来,人类的文明则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以展现强力和征服为荣耀。在信奉科学力量的同时,渐渐熄灭了对自然与生俱来的敬畏之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相依相存慢慢转变为对抗角力,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之下,在显微镜、望远镜和开山机械的巨力之下,博物学慢慢地变成了科学研究领域的边缘学科,即使真正的科学家也难以真正理解这个概念。这也是今日在各门学术均十分发达的状况下,依然要重启古老博物学的一个理由。
小学的科学课是对儿童进行早期科学启蒙教育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培养孩子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科学的好奇心、求知欲,能引导孩子们主动获得有关自然界和自身生活的科学知识,帮助他们体验科学的过程与方法,从小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行为习惯和进行科学创造的潜能。
我提倡在科学课上重构孩子的博物学精神,反对像当代教育体制一样,填鸭式的塞给孩子关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等既空洞又乏味的书面教条理论。孩子们对大自然和科学的探究具有天然的兴趣,早期的科学启蒙教育对一个人科学素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真正的博物学是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拿起画笔和工具,用眼睛和心灵去感受和触碰,让大自然去打动他们,这将比书本上的知识更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让孩子们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兴趣,主动去探索和创造。
从小培养博物学家,让我们的儿童像博物学家一样成长,首先就应该培养像博物学家一样广博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们从爱好出发,养成主动博闻、建立博识、拥有博爱的博物家情怀。如果一个孩子的知识注意力,能有一部分回到自己的身边,能至少培养出一项兴趣;不管是做手工,还是对某一类物品的痴迷,或者对某个没有什么现实用途的领域,能够深入钻研,那这个人一定是可爱的、有意思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博物学精神”的复兴就有意义了!
1777年,法国政府给布封铸了一座铜像,基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对布封的崇高评价。他一生热情地赞美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秘密,也对人类的智慧和才能倍加称颂。所以成为博物学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艰深困苦,只要我们不断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从周围的生命、环境开始探索,点点滴滴积累知识和经验,说不定我们的孩子已经成为小小博物家了。

·名师自述·
我出生于江苏扬州,游历于江浙两省,体察苏浙教育,如今任职于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担任苏州大学基础教育教师发展学院科学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育部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学课程标准》修订组专家、苏教版小学《科学》教材编写组核心成员,曾主持“无锡市小学科学名师工作室”工作,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无锡市名教师。
从村小教师到国家《课标》组成员,我长期扎根于一线课堂,曾应邀在江苏省“教海探航”征文竞赛颁奖典礼、浙江省“千课万人”研讨会、杭师大“浙派名师课堂展示”以及全国各大学国培项目和教材培训会上示范讲学。有人惊叹于我师承科学教育前辈路培琦后教学技艺的飞跃,也有人折服于我对科学教材穿透性的理解,更有人陶醉于我对科学课堂理性和诗化的演绎……但我知道,因为热爱和执着,所以才会在科学课堂上不断呈现自我的超越。
(作者系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高年级部主任,江苏省特级教师)
·拓展阅读·
《万物简史》〔美〕比尔·布莱森
这是一部有关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书,作者用清晰明了、幽默风趣的笔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繁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一一收入笔下。惊奇和感叹组成了本书,历历在目的天下万物组成了本书,益于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无穷奥妙,掌握万事万物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