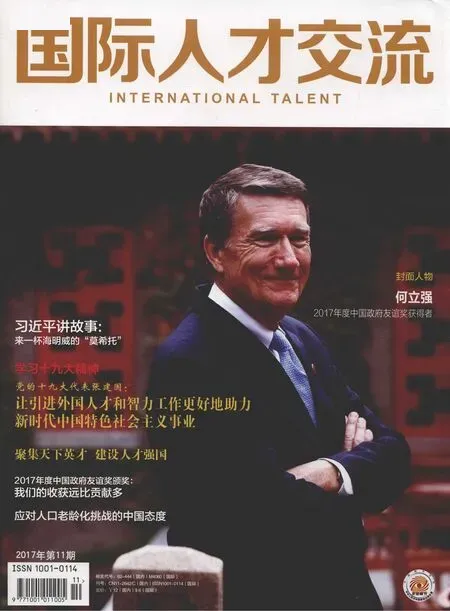迈克尔·麦尔:中国大地上的“游荡者”
文/林颐
迈克尔·麦尔:中国大地上的“游荡者”
文/林颐
《东北游记》不是旅游记闻,译者当时也怕人误会,和作者商量。但是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中文名梅英东)是个“中国通”,坚持这样命名,他说这是“关于他在东北游荡的记录”。
我认为这样取名很恰当。虽然作者、译者都没有进一步解释,但我猜想,老梅的用意来自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一个核心命题——游荡者。本雅明把自己比作现代城市的游荡者,通过“对现代这样一个大废墟的洞察与揭示”,得到发人省思的觉悟。
老梅是中国大地上的“游荡者”。2013年,他出过一本书,叫作《再会,老北京》,有关2008年奥运会之前北京拆迁的百姓日常记录。为了写这本书,老梅在北京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安家落户,花了两三年与老胡同的居民们一起吃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记叙“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江城》《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何伟)这样评价老梅:“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活在一部作品里,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让这种探究走向深处。”
这一次,老梅作为“中国人的女婿”,来到了妻子的家乡,吉林的一个小村庄。
在北京的时候,老梅住在拥挤嘈杂的四合院里,吃大娘水饺,喝燕京啤酒,倾听老胡同百姓的各种烦恼,帮助他们解决拆迁的难题。到了东北,老梅同样像是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一条鱼,很容易就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他爱吃东北乱炖,买菜时也会为了毫厘讨价还价,东北人大多“话痨”,村长、三姨、三舅等人让他收获了一兜篓的故事,他爱走街串巷,爱逛图书馆,另外又搜集了东北的很多事儿。
老梅的身份是极其有利的。在这座人烟密集、各种元素并置的东北村庄里,老梅作为外来者适时转化成了部分的当地人,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他有技巧的引导又常常会引发谈话者对沉寂已久的往事的追忆。
刘博士打开了话匣子,一个穷困潦倒的司机和一位不得志的农学家,如何从无到有创建了“东福米业”。老梅说,“这个故事堪称现代中国的商业寓言”。 跟随老梅纪实风格的淡然叙述,仿佛有一架无形的摄像机在悄悄转移。
另一边,则是三姨深切的担忧。她并不想当东福米业的租客,可是在轰隆轰隆的机器面前,她的虞美人和小菜园已经没有了,她的小产权房即将并入集体,而集体会把土地租让给企业。尽管三姨并不情愿,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安排。就算仍然保有自己的土地,抛荒与低效生产也是大问题,有机农业的高昂成本是目前个人无力承担的。
书中除了日常故事,还有对“金人建城”“日本移民拓荒”等历史的叩问,老梅游历在这陌生的土地上,试图触碰这片土地的真实与来历。如果说北京代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那么,东北可能有着历史悠久、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
《再会,老北京》聚焦大都市的死与生。任何大城市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独特的社会创造出相应城市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长达几百上千年的人类居住形成都市风光,这风光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并使人们意识到,毁掉老建筑带来的损失,不仅仅是肉眼所看见的拆毁古老砖石那么简单。
《东北游记》让老梅作为“游荡者”,拥有与现实隔开了距离的视角,更易于梳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隐秘线索。对于东北每天发生的正在改变的生活事实,以及这些事实背后的悲喜纠结,人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当老梅在博物馆里看到梁思永的《远征日志》,他说,“我突然热泪盈眶”,我想在那时候,在那以后,他都会被东北这块土地深深牵绊。
通过老梅的双眼,我看到:即便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很多空间仍然相当的“农村”;而在同一时刻,中国的广大农村不管是否自愿,都已被迅速地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东北是“天下粮仓”,又是工业重镇,东北的城市化道路比之他处有着更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往往让人感到一种旧时生活的粉碎,仿佛本雅明眼里的“废墟”。老梅要比本雅明乐观,他没有被历史紧紧包裹,而是通过当下的叙述者的思绪更多地指向未来。
——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