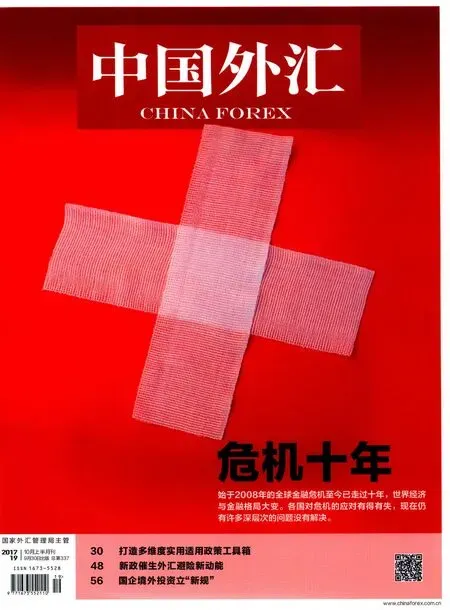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
文/谢亚轩 编辑/孙艳芳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
文/谢亚轩 编辑/孙艳芳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从高位大幅回落,呈现出六大特征。未来有望稳步走出当前的低谷。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倒闭,将美国次贷危机推向顶点,并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导致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剧烈波动。本文将通过回顾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全过程,找出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征,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并研判其未来的走势。
呈现六大特征
第一,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活跃度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
次贷危机以来的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形势就像“飞人”博尔特在退役之战上的表现一样:高位急跌后踉踉跄跄重新起步。根据麦肯锡的有关统计,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达到历史高点,年资本流动总规模高达12.4万亿美元。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从高位大幅回落。2009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达到低点,略超2万亿美元;此后,在2010年虽低位反弹至6.4万亿美元,但其后在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下再次一蹶不振,直到2016年,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可能仅为4.3万亿美元,是2007年高点水平的三分之一。
第二,债务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大起大落。
国际资本流动一般分为四种主要方式:直接投资、权益类证券投资、债券类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以银行借贷和商业信贷等债权债务资本流动为主)。其中,直接投资和权益类证券投资被归类为股权性质的资本流动,而债券类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被归类为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股权性质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较低,稳定性较强;而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波动性高,大起大落,缺乏稳定性。这次也不例外。危机前的2000年至2007年,债务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在资本流动总规模中的占比平均高达64%;危机后,其在国际资本流动总额中的占比大幅下降至31%,仅为危机前的一半不到。其规模也显著下降,从2007年高点时的近8万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低点时的1万亿美元。从结构上来看,债务性质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显著回落,是危机后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活跃度远低于危机前的重要原因。
第三,欧洲商业银行是国际资本撤回的最主要源头。
这一点再次表明,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低,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又由于欧洲的商业银行传统上就在国际信贷市场非常活跃,所以,危机后当这些银行不得不收回大量国际银行信贷时,就成为全球国际资本撤回的主要“宗主国”或来源地。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欧洲商业银行对外发放的信贷余额由2007年的23.4万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13.9万亿美元,下降了9.4万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商业银行发放的国际信贷余额则由2.3万亿美元上升到3.9万亿美元,增加了1.6万亿美元;美国商业银行发放的国际信贷余额一直维持在3万亿美元。从中不难看出,欧洲商业银行是国际债务性资本流动规模显著下降的主要源头。
第四,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出现国际资本净流出。
次贷危机之后,相对于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下降(比如银行间的拆借和债券交易活跃度明显降低),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45个样本新兴经济体的统计,76%的经济体在最近数年出现了国际资本净流入(流入减流出)规模的显著下降。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特别是2014年以来,部分新兴经济体从过去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国转为国际资本净流出国(注:笔者将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视为国际资本净流出)。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地区包括:部分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俄罗斯和中国。以中国为例。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规模在2007年为911亿美元,与GDP之比为2.7%;至2010年分别增长至2822亿美元和4.7%。但从2014年始转为逆差并持续3年,逆差与GDP之比分别为0.5%、4.4%和3.7%,逆差规模在2015年甚至一度高达4856亿美元。
第五,新兴经济体增加持有国外资产的规模呈上升趋势。
国际资本流入被定义为非居民投资者增加购买某国的资产,资本流出被定义为居民增加购买国外资产。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净流入规模的下降乃至由顺差转为逆差,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资本流出规模的上升。为便于理解,笔者将前者比拟为“外部矛盾”,将后者比拟为“内部矛盾”。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净流出基本是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下降所致,即主要是“外部矛盾”。而次贷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居民部门增加对国外资产的购买和持有是一个新现象,“内部矛盾”正在成为造成资本净流出的主要原因。同样以中国为例。2015年4856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中,增持对外资产带来的资本流出为3920亿美元,贡献度高达81%;而2016年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入由负转正为2441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出现4170亿美元的逆差,则完全是因为国际资本流出大增6611亿美元所致。
第六,新兴经济体所受冲击不小但危机不多。
次贷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所受到的冲击不小。如前所述,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国际资本净流入规模的下降,有些经济体甚至出现比较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出。与此相伴生,多数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出现显著的波动。2014年以后,部分货币的贬值幅度和波动幅度巨大。以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为例。受次贷危机的冲击,该指数从2008年9月112.5的高位快速回落至2009年3月初的83.9,跌幅超过25%;此后反弹到2011年4月底的108.6之后,又开始一路下跌,到2016年1月底最低时达62.9,下降幅度超过42%;目前该指数虽已回升到71左右,但仍较2011年下降近35%。虽然不论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下降的幅度还是从汇率下跌的幅度来看,新兴经济体在次贷危机后所经受的外部冲击都不能算小,但是爆发危机的次数却较上世纪90年代显著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仅出现了13次外部危机;而在1990至2003年,新兴市场出现外部危机的次数高达20次。
波动原因探析
造成次贷危机后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巨大变化的原因多样,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既有国际性因素也有各个国家自身的国内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一些非经济因素。
第一,全球风险因素解释了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快速下降。
我们可以用VIX指数来衡量全球市场恐慌与波动程度或者说全球风险因素。该指数在2008年雷曼事件爆发和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期间,均出现过显著的上升。研究表明,全球风险因素上升期间,各个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入出现下降,资本撤回的情况也非常普遍,特别是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收回。对外负债头寸比较高的国家和信贷扩张及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捷克等东欧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全球风险因素的变化解释了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在2008至2009年以及2011至2012年期间的快速下降。
第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显著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向。
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国际清算银行何东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通过货币政策渠道、全球金融市场渠道、汇率渠道、国际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组合再平衡等多个渠道影响其他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估算,美联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操作,向全球其他经济体“泵出”超过4.3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9至2011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低位反弹。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清算银行Eugenio Cerutti、Stijn Claessens 和 Andrew K Rose 2017年8月合写的工作论文《全球金融周期有多重要?来自国际资本流动的证据》认为,国际银行信贷和债券发行有关的资本流动,在次贷危机后,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显著上升,并在2013年联储宣布将退出量宽时,出现的“消减恐慌”(Taper Tantrum)时达到极点,导致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规模显著下降。这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另外一种体现方式。
第三,欧洲商业银行大规模撤资主要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所致。
首先,欧债危机严重影响到欧洲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得这些银行不得不撤回之前在全球投放的银行信贷。其次,2010年以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同时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出现所谓的“长期停滞现象”。这使得国际银行业务的风险上升,利润率下降,也导致欧洲商业银行重新发放国际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下降。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资本大举涌入的情况下,采取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控制短期债务性国际资本流入,也使得欧洲商业银行的国际信贷规模增长乏力。这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3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3〕20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制度性改革对于次贷危机后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影响显著。
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多个新兴经济体汇率弹性的提升有助于缓冲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认为,之所以次贷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净流出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出现外部危机的次数却低于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多个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弹性提升(如巴西、南非等),有效缓冲了外部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证检验也表明,2010年至2015年,汇率下跌幅度超过20%的新兴经济体,其国际资本外流规模与GDP之比平均为2.3%,要远低于汇率弹性相对低的经济体4.5%的平均水平。其二,新兴经济体国际储备资产同样有助于平滑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2007年,全球国际储备规模为3.9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25%。在美联储等发达国家央行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全球国际储备规模进一步上升,到2013年达到7.5万亿美元的高点,与GDP之比为27%。此后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导致多个新兴经济体出现明显国际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国际储备资产开始下降,发挥了缓解外部冲击、稳定汇率的作用。2016年,全球国际储备的规模下降到6.6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下降为24%。此外,多个国家实行的通胀目标制、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政策,以及旨在防范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措施,也都功不可没。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多变性
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动形势呈现出多变性。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力巨大,资本和金融账户虽仍保持顺差,但与GDP之比由上年2.7%的高位回落至0.9%。此后,一方面由于美联储开始实行非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多项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恢复了较快的增长,所以2009年至2011年中国吸引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快速反弹:2010年,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规模与GDP之比达到历史高点的4.7%。此后,欧债危机爆发,2013年,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叠加中国国内杠杆率持续上升,经济增速逐步下降,国际资本净流入的规模也逐渐下降,甚至在2012年转为净流出。2012年年底,欧债危机风险显著下降,2013年,中国加快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这两个因素将2013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入规模推高到创纪录的3430亿美元。从2014年开始,中国国际资本连续3年出现净流出,其中2015年的外流规模高达4856亿美元。
危机后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形势的多变性需要多维度加以解读:一是国际因素。比如由于欧美经济复苏速度差异和货币政策分化,导致美元在2014年至2015年快速走强,使得国内企业和个人增加持有外汇资产,加快偿还外币负债的积极性上升,导致国际资本外流。二是国内因素。比如2015年6月和7月股票市场剧烈调整,导致投资者出现严重的恐慌情绪,对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广义中国资产失去信心,购汇和持有外汇资产的需求显著上升;又比如,中国对外投资战略调整,“走出去”步伐加快等。三是周期性因素。比如2014年至2015年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四是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比如2015年“8·11”汇改带来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放大了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波动性等。
预计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活跃度处于低位的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仍然会发挥作用,包括欧洲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中国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的高杠杆率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等等。此外,一些周期性因素似乎也还在对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负面影响,如美联储加息进程的快慢,缩表操作可能的节奏及产生的溢出效应,欧央行何时开启退出量化宽松操作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经过次贷危机后的调整,全球系统性风险已呈下降趋势,预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收缩也将会以较慢的速度推进;此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逐步恢复,而中国国内投资者对于“8·11”汇改的理解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认识也在加深。据此预判,未来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有望稳步实现总体平衡。在此条件下,中国的宏观决策层宜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立场,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对因私人部门增加持有海外资产而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不应加以限制;同时,应以中国债券市场开放为主战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以利于在资本更为自由流动的新层面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作者系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