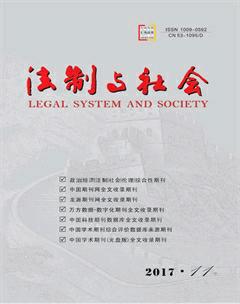管窥债权物权融合理论之合理性
摘 要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民间有关物权债权融合理论的争鸣不绝于耳。该理论对现行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认识基础提出质疑,并从物权和债权的历史起源、形成原理,以及二者性质、效力的角度论述融合的合理性;主张者认为物权与债权区分的二元结构论固步自封,应当适时修正现行民法理论和民法体例,以使我国将来的物权和债权立法更具超前性。不可否认,这种理论的提出对于立法前瞻性具有跨时代的积极影响,但本文认为,现阶段融合理论关于物权债权在涉他性效力和排他支配性方面仍缺乏合理论证。
关键词 物权 债权 合理性
作者简介:苏名远,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1.129
持债权物权融合一元论观点的主张者认为(以下简称为“主张者认为”),债权和物权并不具有绝对的界限,传统观点所主张的物权与债权的理论基础也不应该作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区分,而应该模糊二者的界限,从而使“债权物权化”、“物权债权化”。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民事权利涉他性效力的正当基础
主张者认为,具备涉他性效力最典型的权利是所有权。以所有权作为代表性物权,从所有权为何能够具备涉他性效力,以及这种效力的正当基础何在来展开论证。该观点认为,涉他性效力并不是物权制度的天然属性。涉他权利涉及一个权利人和不特定多数的义务人,权利若要具备涉他性效力,其正当基础在于该权利能够被第三人知晓。所有权如果单凭内在的、观念性的因素就可以左右他人行为,是不公平的。
主张者提出,中世纪的日耳曼法中,“对物权”原本也不具有排他性、优先性效力,只有经过公示的对物权才具有排他性、优先性效力,这种物权被称为物权性对物权。因此,这种权利如果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就应该通过某种外观的标志彰显出来,对外人提供一个权利人具有所有权的明确信息,并为公众所知悉。罗马法在对物诉讼中,就是通过法官对存在于物上的法律关系这一事实的公开确认,使观念上的所有权成为可识别性强的具体的所有权。在对人诉讼中,是因为案外第三人理应知晓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权利——尽管第三人并不需要积极协助权利人实现权利,但至少不得妨碍第三人实现权利。
于是,根据上述理论,主张者解释了权利涉他性效力的来源:一旦权利人的权利为公众所知悉,社会公众就应该尊重该权利,不得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公示后明知他人具有权利而依然妨碍的,主观上具有恶意,不符合一般的正义观念,不应得到法律认同。
笔者认为,并非一切物权人的所有权都需要履行书面登记的公示手续,只有少数诸如房产的特殊物权才需要登记公示。从现代商品经济来看,抛开物本身的属性,强调任何物都要有被第三人所明确知悉的外观标志——登记或公示,显然不现实。不但有碍于物的正常流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所有权人行使权利,降低了物的流通效率,无益于交易的简单便捷性。而主张者认为,我们理应通过合法手段将自己对物的所有权公之于众,权威判决或官方证明是获得物权不被侵犯的前提,甚至坚持这是物权受到保障的唯一权利来源。但笔者认为,就物权的代表性权利——所有权来说,只要外观上可被推知为权利人,则第三人不应该以不符合一般社会评判标准的行为加以妨碍。所以,无论权利人的物权是否公示,从自然法角度讲,第三人作为自由意志人,都不应该有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的行为。
二、物权未必都具备涉他性效力
主张者认为,传统理论区分物权与债权的主要依据之一是物权属于对世权,具备涉他性效力;债权是对人权,效力只能拘束于债务人。从康德的“集体意志”形成的“共同占有理论”和卢梭的“人民公意”理论结合起来解释物权的排他性、对抗性效力。康德認为,物权人在取得物权前,与其他人之间处于一种集体意志形成的“共同占有状态”之中。
通俗的说,康德认为,权利形成的前提是集体共同占有,只有在国家形成之后,根据公共意志的认可,个体才真正享有权利。这里的公共意志即卢梭所称“人民公意”——法律。该理论大意为:当每个人都希望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而自己又不想吃亏时,彼此就会打消占对方便宜的想法,结果形成了他们的共同意志——每个人获得他应当获得东西即可。这种反映一般民众意志的众意,理应以公意(以国家之名制定的法律)固定下来。主张者将集体意志和公意结合起来,论述所谓物权具有排他性、对抗性效力的前提是“隐含了人民必须是彼此熟知的群体的集合”,即转让只是在熟人之间,交易过程能够被其他人所知悉,因此对新所有权人的“对物支配”给予尊重。主张者列举了《日本民法典》第176、177、178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转移需要以交付为对抗第三人要件的规定认为,标的物交付之前,买方就取得了物的所有权,而交付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进一步得出在交付前物权就不具备涉他性效力的结论。
笔者认为,《日本民法典》如此规定仅仅是日本在法律上限制了尚未对物取得占有的新所有权人的权利。确实,此时物权的涉他性效力受到了限制,但不能因此说明,物权不具备涉他性效力,只是基于特定的法律前提,涉他性效力受到了限制。相反,假设恶意第三人意图通过交易取得物的所有权但未能得逞,物权的涉他性效力就得以体现,保护了原权利人。因此不能说物权不具备涉他性效力,在某一具体的法律规定下,仅仅是物权的涉他性效力受到限制,不能因此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已。
三、债权也能产生涉他性效力
通说认为,债权的请求权属性决定了债权是一种只能针对特定主体的相对权,以同一个物为标的可以设定多个债权,各债权之间平等且不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性。物权是支配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因而具有优先性。
主张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传统理论中债权是单纯的相对权、不具备涉他性效力的理论根基已经动摇,债权在现代民法中已经在很多情形中具备了涉他性效力,列举了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责任、买卖不破租赁、债权的预告登记等规定。endprint
尽管这种效力在债权人的代位权、撤销权等权利行使的形式上表现相似,但需要注意的是,债权的此种形式效力与传统理论中物权的涉他性效力是不同的。根据传统理论,物权的涉他性效力体现为绝对权、支配权,拿债权人的撤销权来说,债权人行使这项权利的前提是通过法院请求撤销债务人和次债务人间恶意或推定恶意的交易,而这种权利虽然表现为债权对抗主债权债务之外的第三人,但此种由债权产生的对抗性、涉他性效力实际上具有的依然是请求权的属性,而不是物权支配权的属性。因为次债务人即便不听从债权人的指示解除与主债务人的交易合同,债权人自身也是不能直接施加影响而变动交易结果的。而物权人的权利则通常具有绝对性、支配性,主张者的观点只是混淆了二者形式上的效力,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效力的本质特征。并且,主张者认为作为代位权、撤销权具有针对债的关系之外的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但实际上这种第三人是确定的,根本在于该第三人何时出现——第三人通过积极作为的侵害行为妨碍债权人的权利时起确定,并在确定时产生了债权意义上的请求权,而非针对任意第三人。
因此,该类权利本质上依然是针对特定的第三人,所以不能因此否定债权的相对性。而物权人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绝对权权能,是指任何人都需要避免对物权人行使权利产生妨害,负有消极不作为的义务,与债权的相对性有本质上的区别。
四、是否具有支配性不能成为物权与债权区分的依据
首先,主张者认为以是否具有直接支配权为标准是不足以区分物权与债权的。他们提出,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物权都具有直接支配标的物的性质,他们以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为例认为,物权人不能直接支配物本身,而是支配物的交换价值。笔者认为,尽管抵押权并不能直接支配标的物,但不能否认抵押权的支配性。支配权是指主体对权利客体可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同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对于抵押权,其权利客体是担保物的财产性利益,而不能仅从表面认为客体是标的物本身。作为物权所体现出来的支配权,在于享有对抵押物的财产性利益享有支配权以保障债权实现的可能性,不在于如何具体的支配担保物本身来取得利益。
另一方面,主张者认为债权同样具有支配性。根据合同法理论,债权人基于租赁契约而享有的以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为主要内容的租赁权是其债权的具体内容,这种对物的占有、使用本身就是对物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不仅可以对抗原所有权人,并可以基于租赁关系对抗新产生的所有权人,主张者因而认为债权和物权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权利人同样可以凭借其债权支配标的物,因此说债权人不能直接支配标的物且以此为依据区分物权和债权的观点是不可靠的。笔者认为,债权人基于租赁契约产生的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权,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使用之后所产生的物权,而此时对抗第三人或者说新所有权人的效力依然是对基于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的对物在事实或法律上的控制的权利,本质即占有权,以及依照约定的相应使用权,因此这种权利从本质上依然是物权的特征,而并不是债权本身所产生的支配性效力。
主张者还提出,作为债权,权利人自然可以免除或减少债务人的债务,难道债权人对债务人债务的减少和免除不是在“任意决定”债务人的债务吗?所以这种“任意决定”是债权存在支配性的必然体现。
笔者认为,作为债权人对债权的任意处分,明显是行使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包括且不限于债权,任何权利人都具有对自己权利在合法范围内任意处分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自由处分性不应该作出“债权具有支配性”的误读。
五、对物权债权融合观点的重新审视
不难看出,债权与物权存在本质区别。尽管任何理论的构建都并非牢不可破,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元性也使得“债权物权化”和“物权债权化”现象的出现,二者之间区分的临界点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变得模糊,但这并非意味着二者间的界限就应当完全打破。从哲学角度看,万物都非绝对割裂的,说二者毫无联系自然是欠缺综合考量的形而上学观点,但也不可片面将二者的融合一元化,持有合二为一的绝对主义论调。
理论的创新固然对立法工作的前瞻具有指导意义,但更应考虑对立法行为的尊重和敬畏,创新要符合法学工作的实际需求,不但要目标高远,更应当立足现实。通过科学的立法实现理论指导的前瞻性非一蹴而就,其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金可可.私法体系中的债权物权区分说——萨维尼的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6(2).
[2]刘德良、许中缘.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质疑.河北法学.2007(1).
[3]王轶、关淑芳.物权债权区分论的五个理论维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
[4]温世扬、武亦文.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再证成.法学家.2010(6).
[5]冉昊.“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基本成因.江淮论坛.2014(4).
[6]季蓉.物权债权区分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分析.法制與经济.2011(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