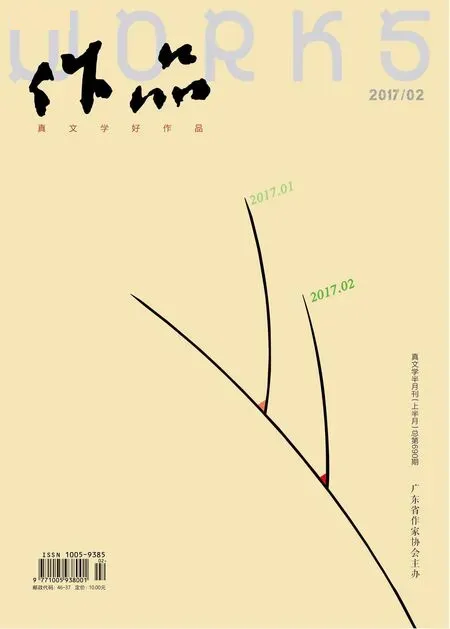蚕头燕尾
文/周李立
蚕头燕尾
文/周李立
周李立女,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多次入选各选刊及年度选本。出版小说集《欢喜腾》 《透视》 《八道门》。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朔方》文学奖、《广州文艺》双年奖等。现居北京。
银针整齐列在专用塑料盒里。每根针都被卡扣固定在专属位置。冷医生每天都用酒精灯为这些银针消毒。他从医多年,知道消毒工作多么重要。
如今冷医生每天上午最重要的事就是给妹妹做针灸按摩的康复治疗。一般来说,夏末秋初这时节,开始针灸前他会先调高房间的空调温度,因为针灸时妹妹得脱掉上衣,而她又那么怕冷。冷医生之后会点燃三炷香,插在五斗柜上的香炉里,看一会儿,直到青烟平稳着上升——这自然也是“标准程序”的一部分。何况焚香与针灸,是多么合适的搭配。他当然还会仔仔细细洗手,用纱布擦干,戴上医用橡胶手套,然后为避免碰触任何东西而只能半举双手,来到妹妹床前。
装银针的塑料盒,在洗手前就需打开,端正放在床边桌上,好拿的位置。
妹妹怕疼,冷医生开始针灸前总是需要哄哄她。“妹妹,一点儿也不疼,我现在技术已经很好了。”其实他不说,妹妹也明白他的技术早有进步——他认为自己从她的身体读出这样的信息。
冷医生帮妹妹翻身。她的身体轻盈得像少女。她确实永远是少女,在他心里。
这样的日子从妹妹五年前坐上轮椅开始。冷医生和妹妹的生活,从那时起就发生了转变。医院工会开始偶尔给他们送来粮油蔬菜,冷医生开始笨拙操持自己和妹妹的一日三餐。有一天,对着自己弄出的难以下咽的食物,他终于忍无可忍。他扔掉手中正在削的苹果,用水果刀在窗帘上戳出了那几个耻辱的破洞。他记得那也是一个上午,阳光瞬间就从那几个破洞倾泻入他们朝南的房间。那光线让他惊讶,光线中漂浮的粉尘密集得像室内刚下过一场浓雾,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拉开过窗帘了——从前这都是妹妹每天做的事。这时,他回身,看见轮椅上的妹妹老泪纵横,浑浊的泪滴砸在她不由自主始终颤抖的手背上。
“妹妹,我会治好你,我不应该失去理智。”他蹲下身,替她擦眼泪,向她作出无用的承诺。她那时只能发出一些含混的“咿咿呀呀”的音节了。那些音节,就像婴儿的话语,除了他们自己,其实无人能懂。
他艰难地起身,并意识到自己的膝盖已经老化,软弱得几乎无法支持他完成蹲下又站起的动作。那时是他六十五岁的时候。
冷医生就从那时开始接触针灸按摩。这与他多年信奉的西医可算完全不同的领域。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病急乱投医,因为“我们五床的病人,情况比你夫人严重,刚中风时只能躺着,但现在,至少可以坐起来了”,曾经的同事这样告诉冷医生。冷医生从医三十五年,一直在内科门诊,所看病症无外乎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冷医生做人并不冷,其实还很热心,其他医生三五分钟就解决的病人,他能耐心看上三五十分钟。尤其早年,对那些远途步行来城里看病的乡下人,他总不忍心一言不发用一张简单药方就把人家打发掉,虽然最终,大多数时候,他不过也是飞快开出一张字迹潦草的单子。但嘘寒问暖多说点什么,随便什么,他知道,对病人都是安慰,对病情有益。这被冷医生认为是一种无法解释却行之有效的医患逻辑。他相信没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医生,恐怕无法领会其中道理。
三十五年来,他从未遇到过疑难杂症,这是奇迹。这让冷医生在退休时倍感荣耀,或者是幸运。他收到的锦旗,甚至铺满家里一整面墙。不过,那些锦旗现在已经不见了。两年前,一个秋天的早晨,他把锦旗都从墙上摘下来,剪碎了——他生气的时候总喜欢拿刀子破坏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分了三次才把那些猩红的碎布条搬下楼,塞进楼下那几个大垃圾筒。垃圾筒的盖子敞开着,像几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那么多布条扔进去,仍然空空荡荡。
冷医生给妹妹翻过身,是为方便脱掉妹妹身上那件红色上衣。这曾是妹妹最喜欢的衣服,蝙蝠袖套头衫,当年最时髦的样式。妹妹很多年都不穿它了,因为太时髦,“我是老太太,怎么能穿这么红呢?”妹妹这样解释,眼神里却都是惋惜。红色衬衣如今已褪色成粉红,毕竟冷医生操持家务,就无法像妹妹那样,让他们的衣服永远保持干净、整洁和平整的完美状态——也许都怪他洗衣服时用了太多消毒水。他一度迷恋消毒水的味道,因为妹妹当初也如此——“消毒水的味道,我太喜欢了”,她亲口告诉他的。他曾愚蠢地以为妹妹是因为消毒水的味道才喜欢上当医生的自己的。那也是他爱上妹妹的时刻:四十多年前的医院,还是那座两层的老楼。爬山虎的叶子盖满老楼每扇窗户。木质楼梯的扶手都是殖民风格的彩色油漆。虽然油漆脱落严重,曲线形的扶手暴露出的褐色木纹,如今在冷医生的记忆里依然美得惊心动魄,一如妹妹靠在楼梯扶手上的身姿。
妹妹——他从那时开始叫她妹妹。妹妹叫他冷医生。多年来他们对对方的称呼从未变过。妹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的庞大家族在那个年代声名显赫。她的姓氏在这座小城几乎像皇族姓氏般让人不敢冲犯。
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的家人都这样叫她,妹妹。他喜欢她发出妹妹两个字时嘴唇的形状,像那些年医院大院里那口小池塘边夏季雨前时常飞过的蜻蜓的尾部,纤细、有弹力,充满慌张的生命力,仿佛随时都会从他眼前飞走、消失。
银针准确扎入穴位,妹妹没有发出一丝呻吟。“如果疼了、不舒服了,一定告诉我啊。”冷医生向来钦佩妹妹的勇气和毅力。但也许,她只是不愿意告诉他,她有多么难熬。毕竟妹妹一生都很安静,她说自己不喜欢说话,但喜欢写字。冷医生相反,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写字。医生就是有不必工整写字的特权。只要药房的姑娘们认得,就没什么大碍。
喜欢写字的妹妹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作家,她还真的写过一些冷医生无法理解的诗歌。那都是他们还年轻时,有些夜晚,冷医生依次抚摸她手指每个关节,温和地,似乎想要抚平她冰冷的手指突起的每一毫厘骨节。这时,妹妹会念叨她的诗,她缓慢的呢喃,像小尼姑背诵尚不熟悉的经文。妹妹为他这个“小尼姑”的比喻生过气,继而将自己的手从他的手掌中拔出。她生气的时候,两手一般会在胸前以一种复杂的形态相握,仿佛魔术师酝酿着奇迹般的变化——那相握的两手间,似乎会突然溢出某种东西,让他惊讶的东西。最终、然而,没有东西被变出来。她并不是魔术师。
她说,我才不是小尼姑。
冷医生总是陶醉于这样的时刻,因为他知道她并非真的愠怒。他只好佯装认错,向她说明“小尼姑念经”仅仅是一种比喻。诗人,诗人是会理解比喻的。当然。
妹妹躺在床上,两手在胸前握得更紧,泄露出她其实并不放松的心情状态。她严肃地说,我是你爱人,不是小尼姑,如果我是小尼姑,你就是小尼姑的爱人。但是小尼姑是不能有爱人的,所以,我不能是小尼姑。
冷医生会去掰开她紧握的手掌,那并不真的需要太多力气。因为她总是配合他,松开自己,像他们多年来共度的每个夜晚一样。是的,是的,那真的是很多个夜晚。
所以,冷医生如今非常习惯妹妹的沉默。他每天醒来,都能看见妹妹平躺在身边。大眼睛满是笑意,望向天花板。睫毛上翘,长得快要盖住眉毛。他把妹妹的脸转过来朝向自己。妹妹脸上的微笑是他每天早上醒来的动力。他退休已经十年了。
“早上好,妹妹,我昨天睡得不太好,你呢?有没有做梦?”妹妹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眸清亮又深邃。
冷医生一般会犹豫一阵儿,考虑要不要立刻起床。早晨的阳光投影在墙面的影子,泄露出窗帘上那几处没有缝补的漏洞的形状。他希望妹妹不要去注意到那几个洞——让阳光这样进来吧,也没什么不好,是吗?他这样想。可妹妹不是这样的人——除非她已经把所有破损都缝合到难以察觉的天衣无缝的地步,她是不会安心睡个好觉的。从来如此。那些年他们受了些苦。在最艰难的时候,她用一件毛衣的毛线和两根毛线针,就变化出足以保证他们两人过冬的两条毛裤。这样想来,她其实也是魔术师。他侧身,看见妹妹并没有把两手手掌紧握在胸前,又觉得放松了一些。他平躺着,握住妹妹靠近自己的那只手。冰凉却光滑的手指,就这样顺从地躺在他千沟万壑的掌纹里。于是,他纵容自己又睡了一会儿。
一般而言,冷医生醒来后,如果没有立刻起床,他的视线有时会不由自主去捕捉那些漏进室内的光斑。光斑在墙面上,似乎正在下坠。这意味着新一天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墙面上曾经挂锦旗的地方,如今贴着妹妹的书法作品。是隶书,讲究蚕头燕尾——关于书法,冷医生只知道这么多。因为妹妹只来得及告诉他这么多。妹妹虽然一直喜欢写字,但真正拿起毛笔,还是她退休以后。他们同一年出生,同一年退休。他曾相信他们会在同一年死去。
他的早餐如今总是一碗简单的泡饭。妹妹什么也不吃。她甚至很早以前就不再吃药了。写字桌属于妹妹的那个抽屉,一度塞满大大小小的药盒。妹妹是脑血管堵塞、轻度中风——这和冷医生多年来医治的病人完全不一样。他拿到妹妹的诊断书时,开始怀疑自己其实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那些药品和治疗方案,在他看来都太陌生。是因为医学发展太快吗?妹妹的医生对冷医生几度欲言又止——那位医生多年前刚进入医院工作的时候,冷医生已经在医院同事间赢得了口碑和尊敬。终于,冷医生被告知,妹妹以后再也不能离开轮椅。“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也许还会更糟,如果中风再来一次的话,那就……谁也说不好。”
“他们其实什么也不懂,就像我一样。那些大学生,他们什么都不懂。”冷医生此后总是这样质疑自己一生引以为傲的职业。医生是世界上最无能为力的职业。他一生为无数病人开过抗生素或抗病毒的药品。那些药品总是隔些年就更新换代,然后价格翻倍。他貌似也帮助他们暂时消除了发烧、咳嗽、流鼻涕、咽喉肿痛的种种不适,但那又如何,他们最后都得面对死亡。
“为什么谁也说不好!”冷医生在心脑血管科的接诊室勃然大怒。那年他六十五岁,退休五年。医院新来的护士并不知道他在这座大楼里长久工作过。她们保持着职业性的沉默,口罩上方的眼睛却一律说出含义相似的话——发怒有什么用?在医院,发怒从来不是英明的治疗手段。
“冷前辈,您也是医生,道理不用我讲了,请您理解,我们都很难过。”妹妹的主治医生说。
冷医生一边做针灸,一边跟妹妹说话。这是他每天最享受的时刻。“你看,留着窗帘那几个洞,太阳就能每天照照你的字,是不是也很好?”冷医生说,暗自希望这样的想法不会被妹妹认为是他为自己的懒惰找到的借口。他的懒惰,世界上恐怕只有妹妹知道。“懒得饭到嘴边都不想张口。”妹妹总这么打趣他。在工作几十年的医院,冷医生一直都是勤勉的、受人爱戴的优秀员工。此刻,面对妹妹,冷医生似乎感到一丝惭愧。
冷医生有时觉得日子会永远这样下去,这日子里有妹妹亲切的沉默,也有他对自己的微小纵容。有时阴天,早晨便没有光线能透过窗帘上的破洞涂在妹妹的字上;但大多数晴好的日子里,那些蚕头燕尾的字迹,都在晨曦中闪闪发光。那些字并不能组合成某种特定含义,那只是妹妹临帖来的单独的汉字:一、二、水、土、木、永;再一张,仍然是重复的,一、二、水、土、木、永。闲暇时,他试图将这些简单的汉字组合成有趣味的句子,但并不容易:一生一世,二、二人是夫妻,水、土、木都是五行,永,永远在一起;那么,再回到一,还是一生一世。他的拼字游戏总是止步于此。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妹妹的字,准确说是那些练习用的毛边纸,正在卷曲、发黄。他意识到某种变化正在他眼前以几乎隐形的形式发生。很多事都是如此。
“我真是傻瓜,对吧?妹妹,你不要怪我,我应该早早把它们装裱起来的。你的蚕头燕尾,真好看,差点被我毁了。妹妹,你不会怪我,你当然不会,我保证,我保证今天就拿它们去装裱。”
这天的针灸进展顺利,所以他想干脆就今天出门。如今他不常外出,因为妹妹无法外出,而现在他又几乎片刻都不能离开妹妹,妹妹也片刻不能没有他的照顾。她从五年前坐上轮椅开始就拒绝外出了。他曾想推轮椅带她出去散步,但她拒绝。她认为那太残忍——让别人看见她窝在轮椅里的样子。她从来都很在乎她在别人眼中的样子。冷医生从不强迫她,哪怕现在她对他始终温顺和微笑,再不摇头说出半个“不”字。
于是外出变成这个上午的意外,这意味着他必须尽快完成针灸程序。却不料新的意外随即发生,银针在灵台穴的地方遇到了阻碍,再也无法刺入更深——这意味着它无法刺激穴位,将会成为失败的一针。这是此前没发生过的状况。冷医生有点惊慌,但也很快平静下来。
“妹妹,对不起,我肯定弄疼你了,你再忍耐一下,很快就好了,啊?”
冷医生轻轻拔出那根针,凑近一些,他看见穴位附近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像簸箕上密集的孔洞。他为妹妹光滑明亮的皮肤惊讶,还有她背部的曲线,那就像流沙堆积自然形成般。他抚摸那些针眼,仿佛那都是自己身上的千疮百孔。
妹妹总是承受着更多的东西、更大的苦难。那些疯狂的年代,她庞大的家族被打倒、拆解,像连根拔起的大树,树叶四散而去,谁也无法再依靠谁。妹妹那时怀孕六个月,在扫厕所的时候滑倒了,因为身体太弱,她无法自己爬起来。她在冬天厕所的水泥地上躺了整整一天,没有人知道。妹妹工作的小学已经停课,所有人都去了另一所学校的操场,那里一场激烈的批斗会正在进行。这一切,妹妹都承受下来了。她始终是他的开心果。所以,她后来依然能回到讲台——她说那是她一生无法离开的地方。那些年她在黑板上写下“四个现代化”或者“少年闰土”,粉笔字非常漂亮。她曾经独自完成了小学校操场上的五块黑板报,花了一个周末时间。冷医生那时并不知道,妹妹在黑板报上写下的,是什么字体,会不会有蚕头燕尾?她很早开始就想写毛笔字,但“没时间,现在我还是用这个比较快”,她用大拇指让手中的红色圆珠笔转来转去。桌面作业本上,是她刚刚写下的大段批语。红色圆珠笔写下的自己,每一个都站得笔直,彼此相隔同样的距离,像列队的小小士兵。
“我知道你还是很难过的,那年我们没了孩子,你流产了,你口头上安慰我,说没事,但我知道,你有多伤心。我也伤心,我没办法,我没能好好安慰你。”
“其实,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埋怨了,我们再不能生孩子了。我一点儿也不埋怨。那些年我不明白,总是拿这件事说话,总是戳你的痛处,现在,我都明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虽然我们经历了那些不好的事,但是后来,我们再也没有不顺过,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是老天在回报我们呢!我想,那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妹妹,我们还得进行下去……”冷医生将手中的银针轻轻转动,侧耳贴向那根针,就像要听出妹妹体内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然而,他仍没能成功将那根针刺入。他俯身侧耳,正好能看卧室五斗柜上的香炉,那三炷香已经燃烧殆尽,烟雾在更高一些的地方聚集。这景象让他懊恼,他觉得自己拼命维系的某种宁静,正被这根捣蛋的针击破。
他用了更大的力气,这让他几乎无法捏住银针,灵台穴的地方于是深陷下去,像妹妹的身体被谁咬过一口。妹妹完美的身体曲线被破坏,有了残缺。满背的银针让她看起来很像一只骄傲的刺猬。
“你满意了吗?你故意跟我作对是吗?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吗?”冷医生无法克制自己,朝眼前的“刺猬”嚷起来。
几乎同时,那针银针,歪斜着,从一个不很准确的角度,刺入了妹妹的身体——太深了,甚至都看不见针尾了。
冷医生气呼呼地穿上外出的衣服,他决定让妹妹自己呆一会儿,也许她会反思一下这个早上发生的状况。她总是会有些小脾气的,女人都是有些小脾气的。他知道她有多么执拗,多么能坚持。当初,她的家庭并不接受他,因为他只是一个怯懦的小男人,在医院工作,几乎一无所有。为了让她不再见他,她的父母甚至替她在学校请了病假,将她反锁在房间里。于是她绝食,“拿古诗十九首当食粮”,后来她把这作为小秘密告诉他,“哦,但是读到有一句就不行了,因为那句是‘努力加餐饭’”。最终,她还是成功了,父母为了让她开始吃东西,不得不由着她,替她把冷医生找来。
这一切都让冷医生对她无法真的生气。他生气只是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换衣服的时候,他看着镜中的脸,慢慢平息,为此他不得不多做了几次深呼吸。这是妹妹教他的办法,“你性子太急,多做深呼吸,来,呼……吸……”妹妹每次这样说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又回到童年时代,他就成为了她的孩子。但这时,频繁的呼气吸气,似乎也放松了他的泪腺,他意识到自己流了几滴泪。
这样不好,只会让妹妹更难过,他想。
于是他拿上公文包,匆匆出了门。
医院的老楼很多年以前就被拆除了。新建的医院大楼,外墙上再也没有爬山虎。雪白的大瓷砖像太平间的冷冻库一般,冰冷得让人难过。冷医生走出医院家属楼,走进医院十层大楼被上午的阳光投射出的阴影里。这让他很难感受到这个“秋老虎”的日子事实上的炎热程度。大楼前再也没有小池塘,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像两张巨大的嘴同时向对方咆哮。
他手里的公文包里,正装着妹妹的字——他很不容易才把一共五张纸整齐叠好,顺利放入公文包。他只是一名用听诊器看病的内科医生,缺少外科手术大夫对手部动作和力度的精准掌控。写字也需要这种掌控,掌控动作和力度。他刚刚还为自己这番重大领悟惊喜过,几乎立刻就想去告诉妹妹。
“冷医生,今天怎么有兴致,出来走走?”他在医院的花园里,遇上了从前的同事,陆医生。他们也是邻居,分别住在同一栋家属楼的五楼和六楼。但他们确实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陆医生啊,我今天出来办事。”冷医生并不愿意说太多。
“哦,好。今天真热。我打算回家了。好长时间没见你,还好吧?”陆医生说。
冷医生并不想见陆医生。他们都已经退休。陆医生有大把时间需要打发。于是在妹妹重病的那些日子里,陆医生召集了全医院的退休人员来看望妹妹。可是,他明明知道妹妹不愿意见人。妹妹那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口水和大小便。妹妹仍然是优雅的,她似乎想对每个人都报以微笑。可在冷医生看来,妹妹那种无法控制面部肌肉的笑容,非常可怜,而且,残忍。那次之后,冷医生就拒绝同事们到家里来了,连工会的人送粮油蔬菜来,他也不要了。他必须让妹妹舒适,妹妹一生都在照顾他的感受,现在,是他为妹妹独挡一面的时候了。
冷医生说:“我挺好的,挺好的。我们都挺好的,妹妹,妹妹也挺好的。”
陆医生愣了片刻,才从衬衣胸前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又凑近冷医生莫名其妙地看。这让冷医生很不舒服,于是他决定尽快离开陆医生,“我得先走了,我有急事。”
陆医生欲言又止,冷医生并不理会他,只径直朝医院大门的方向走去。陆医生在他身后大喊:“老冷,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老兄弟啊,别都自己扛着。”
冷医生头也不回地说:“知道,放心吧,老陆。”
陆医生又喊了一些什么,冷医生没听清。听力现在也不太好使了,他想。
冷医生要去人民路转角处的那家文具店。因为他并不知道小城里什么地方可以装裱字画,但他认为文具店的人一定知道。
那时妹妹准备练习毛笔字的时候,他陪她在那家文具店买了文房四宝,不对,是三宝,妹妹没有买砚台,因为妹妹觉得那不必要。“等我字写得好了,再买砚台吧。”她说。他们那次一共买了三支毛笔,分别是大中小号,羊毫或者狼毫,他不是太懂。他替妹妹拿回家的一卷学生练习用的毛边纸,还有一瓶一得阁的墨汁。此后妹妹每天吃完早饭,就在餐桌上铺上几层旧报纸,开始写字。她有一本很破的字帖,她说那是她家里如今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物件之一,很宝贵。他想去新华书店给妹妹买几本新字帖,不想她竟然笑他,说他不知道这本老字帖才是真正的好东西。“看,这种蚕头燕尾,起笔像蚕的头,厚厚的、圆的,收笔像燕子的尾巴,飘起来、轻轻的,太漂亮了。”妹妹说。冷医生那时并不觉得字帖上的字好看,那上面很多字都是残缺的,认不出是什么。“碑帖多数都是残缺的,但并不影响它的宝贵。”妹妹说。这都是她小时候从她的父母叔伯那里得来的学问。而他,并没有那样高贵的父母叔伯,他无法在碑帖的问题上与她深入谈论。
冷医生有时回想妹妹的话,会觉得她在向他暗示什么。但他太愚钝,以至于花了太长时间——几乎一生——才明白她的暗示。
去文具店的路比冷医生以为的要远,也许只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人走在路上。事实上他认为自己走得并不慢。出医院大门后,沿途再也没有荫凉地带,太阳正是炙热,他泛着浅蓝的短袖衬衣纽扣系得太严实,天气真的很热。但再坚持一下,应该不会太远了,他告诉自己。他只需要经过那家售卖殡葬用品的“黑店”——妹妹管那叫“黑店”,因为那家店不仅招牌和木门都是漆黑的,店铺甚至比街道矮下去一米多深,位于半地下室。店堂里也总是昏暗着,没有灯光。妹妹从前经过“黑店”,总是加快脚步,年轻时她还会小跑几步。离“黑店”不远,还有一家粉红招牌的商店,招牌上写满玫红色的英文字。冷医生不知道是什么含义。与“黑店”完全相反,那里总是有柔和的灯光。复杂蕾丝的帘子装饰着橱窗,夜晚还会亮起缤纷的小彩灯。一串串彩灯,密集着挤在小小的橱窗里,全都像警报器一般闪烁。冷医生从前很少注意那家粉红的商店,直到一年多前,他在那些繁复的浅色蕾丝布帘中,发现一个真人大小的娃娃。他才留意到,这其实是一家成人用品店。
在文具店的玻璃柜台上,冷医生铺平妹妹的字,一共五张,每一张都不大。“你知道哪里可以装裱这些字吗?”他问。
文具店老板是个黑皮肤的本地男人,他认识冷医生,因为小时候在医院,冷医生让他屁股上挨过几针。后来他在自家住房的一楼经营起这家文具店,因为路对面就是一家小学校。
“哦,冷医生,好久不见,我看看,你是要装裱,这些字?”男人热情地招呼。小学校刚刚响过这天的第一次铃声。冷医生是男人这天接待的第一位客人。
冷医生点头,又问:“我就是打听一下,城里什么地方可以做这个,就是,装裱。”
因为总是和小学生打交道,男人说话时,总像是对着一个孩子说话。男人轻抚妹妹的字,一边说:“哦,我可以拿去装裱,我们店有这项服务,这是什么字?一、二、三、水、木……”他站在柜台后面,扭着脑袋念出声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没什么意思?冷医生,这是你写的?”
冷医生说不是,“是我老伴儿的字,我写不出这种字,这都是蚕头燕尾的字,你知道什么是蚕头燕尾么?看这里……”冷医生正要讲解那些笔画的玄机。但男人打断了他,“您真逗,人家装裱字画,都是一大幅,写有志者事竞成,还有什么淡泊明志,还有一个很大的龙字,繁体的,没人像您,裱这个。”
“你,你不裱算了。”冷医生做出要把那些纸折叠起来的动作。他觉得男人并不能理解,他相信妹妹的字足够漂亮,漂亮到任何装裱都不显得过分。妹妹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他有能力给她。
男人连忙道歉,“哎,您老别生气,我就是瞎胡说,不过,这字真挺好看的,您刚说是什么,蚕头,什么尾?”
“蚕的头,燕子的尾巴。”
“哦,您看,我就不懂。您夫人学问大,我小时候她还教过我语文呢。人不在了,留下这字,应该裱起来,用最好的框裱起来,是个念想,对吧?”
“你说什么?”冷医生问。
“我说,应该裱起来,裱起来留个念想。”男人重复了一遍。他已经开始仔细收拾柜台上的五张书法作品了。每张纸之间,都有薄薄的泡沫隔开,之后一起装进纸箱,准备送到装裱书画的地方去。
“前面那句?”冷医生又问。
“前面?前面我说什么了?”男人手里正忙着,只好停下手上的动作,想了想,“哦,我说人虽然不在了,她的字还在。”
冷医生不再讲话,他如此确信眼前的男人终究无法理解自己。这男人居然还认为妹妹已经不在了。如果他告诉男人,妹妹还在,现在她就趴在他们卧室的床上,进行着针灸按摩的康复治疗,那男人也根本不会理解,因为他太年轻了。况且,妹妹如今是个秘密。冷医生知道他们会如何伤害妹妹,用他们那种同情的、貌似慈悲的关切眼光伤害她。冷医生这些日子经历的,他们无法体验,不如就让他们继续相信妹妹“不在了”吧。
“您看,我保证好好弄这个,我认识的那个装裱师傅,是全城最好的一个,我保证您会满意的,到时候弄好了,我给您送家里去,您给我留个门牌号?”男人说。
“不用了,几天能好?到时候我自己来取。”冷医生说,他可不希望莽撞的男人再去叨扰妹妹。
“哦,哦,那也行,就是您辛苦些,大概三五天就可以了,通常。哦,对了,您要什么框?”
“就要最好的。”冷医生简短答复。
事情比冷医生预想的进行得更顺利,他曾以为文具店会告诉他一个装裱字画的地方,那样的话,他还需要自己拎公文包去一趟。文具店的男人应当是可靠的,这种代客装裱的生意,他总不会是第一次做。冷医生在回去的路上,想着这些。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仍然心神不宁?也许因为炎热的天气、灼热的阳光,也许因为他惦记着家中等候他的妹妹?但又好像都不是。
他有些恍惚地贴着街边走,这样就无需频繁避让街道中间穿行的汽车和自行车。
或许是因为,他将有几天无法看见那些字了——他让自己相信这就是此刻自己焦灼不安的原因。那些蚕头燕尾,他每天醒来都会看见的蚕头燕尾。饱满的开头,与逐渐纤细下去的结尾。他想这是多么悲伤的写字方法——几乎和所有的人生、所有的感情一样:浓墨重彩有力开始的时候,谁会知道,那种饱满,终究无法持续,而是渐渐地,在你意识不到的时候,它就只剩下一个轻巧的尾巴。
粉红商店的橱窗,现在换上新的帘子,不再是重峦叠嶂的蕾丝,而是薄纱。浅蓝和浅粉的颜色,交汇融合出许多颗心的图案,衬托着橱窗里那个娃娃,愈加唇红肤白。娃娃站在真人高的纸盒内,黑色纸盒上艳粉色的字,都是日文。
冷医生走得离橱窗太近了,以至于几乎能看清娃娃的长睫毛,像两把小扇子高高翘起来。他还能看清,粉红商店内的青年,耳垂上明晃晃的两个圆环。
青年是粉红商店的老板,他似乎已经注意到冷医生。冷医生急忙离开艳丽的橱窗,暗自希望那青年不要想起一年多前在他们之间发生的对话。
“老爷子,您用不上这个。”“为什么用不上?”“这个,是单身小青年们喜欢的。”“哦,你别说了,我知道了。”“而且很贵,日本原装进口,无公害硅胶,手感跟真人一样……那个,我是不是说多了?”“多少钱?”“标价两万八千八,熟人可以打八折。”“多少?”“老爷子,您不是物价局的吧?我都说过了,我的价格是全城最低的。”“哦,哦,不贵,一点儿也不贵。”“是,我知道您是医生,我在附近见过您,医生都是有钱人,您不嫌贵,都是熟人,我给你七折,怎么样?”“不,我不要,我这么大把岁数,要这个做什么,我就是问问,随便问问。”
冷医生当然不会在粉红商店买一个仿真娃娃。他和妹妹,医生和教师,在小城里从来受人尊敬。妹妹的学生如今几乎遍布小城的各行各业,冷医生可不希望那些人胡乱的传言破坏掉妹妹一生的名誉。
再往前,冷医生看见那家“黑店”门前挤满人,一个个花圈被抬出来,沿着街边摆着。这意味着小城里,又有一个人,去世了。两年以前,他在这家“黑店”给妹妹买了骨灰盒,是他能找到的最小、最精致的骨灰盒。漆制的盒盖上镶有象牙雕刻的图案,那象牙应该是真的,因为妹妹的骨灰盒眼下就安放在五斗柜上,两年来,象牙雕刻的松鹤图案并没有变色、变形,反而愈发剔透明亮。是的,他没有安葬妹妹,他希望让妹妹一直在家中。他上网买了硅胶娃娃,在网上购物这种事上,他比妹妹更擅长。网上价格是一万九千九,他认为这是合理的价位。对方保证会密封包装,“亲,谁也不会知道你买了什么。”冷医生经历了心惊胆颤的一周,才收到那个巨大的纸箱。果然是密封包装,快递单上物品一栏内,写着“日用品”。妹妹确实是生活必需品。他暗自赞叹网店老板的智慧,在收货评价时,毫不吝惜给予了相当过分的赞美。但在对方表示“用得好再光临本店”的时候,他删除了这条购物记录。
陆医生一直认为冷医生如今不正常,自从他老伴儿两年前因二次中风去世后,冷医生深居简出,与曾经的老兄弟们再无交道。有一天,陆医生还在楼下的垃圾筒发现被冷医生剪碎后扔掉的锦旗。陆医生有几次去六楼敲冷医生的门,都毫无回应。可是陆医生知道,冷医生确实在家。陆医生住五楼,就在冷医生楼下,陆医生在客厅发呆的时候,都能听见楼上洗衣机轰隆隆运转的声音。冷医生不容易,一生无儿无女,老伴儿的去世对他是个巨大的灾难。每次这样想的时候,陆医生都这样告诉自己的老伴儿——“不管年轻时我们吵过多少架,现在我们都得忘掉,因为我们都得活下去,这是最重要的,要不你看楼上老冷……”
所以这天晚上,陆医生听见门铃响,他开门看见是冷医生在按门铃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
冷医生穿着格子睡衣,身上有种老年人才会散发出的腐败味道,这味道让冷医生的样子看起来也更加糟糕了。
陆医生让冷医生进屋说话,他甚至急忙去拉这个多年伙伴的手,“老冷啊,来来来,来喝我新泡的红枣茶。”
但冷医生直挺挺站着,一点儿都没有准备进门说话的意思。他只是站在门口,五官扭曲着,带着哭声说:“我要去告他们,他们卖给我的什么东西,妹妹,妹妹身上……假冒伪劣!”
陆医生听得不明不白,他只好认为冷医生只是在想念老伴儿。
冷医生却拉着陆医生的手,说:“你上午告诉我,有什么事不能自己全扛着,我要你帮忙,老兄弟,我要告他们。”
“告谁?”
“你跟我去看,我要去告无良商贩!”
陆医生被冷医生拽着胳臂,上到六楼。在冷医生卧室,陆医生看见一个没穿衣服的硅胶娃娃。娃娃的胸脯,高高挺起来,粉红的两只乳头绽开了,雪白的硅胶便露了出来。
陆医生觉得这场面太不堪,他想自己可能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冷医生蹲在地上,小声呜咽,“他们向我保证,说是日本进口,我那么爱惜,现在,现在这样子……”
硅胶娃娃身上,插着数不清的银针,有些地方绽开,陆医生可以清晰看见那些黑色的金属线圈暴露出来。陆医生退休前是眼耳喉鼻科大夫,对身体的症状并不熟悉。所以他只是看着娃娃的五官,那五官十分精致,尤其是小小的嘴唇,就那么不露牙齿地微笑着,仿佛在笑世上每个人。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