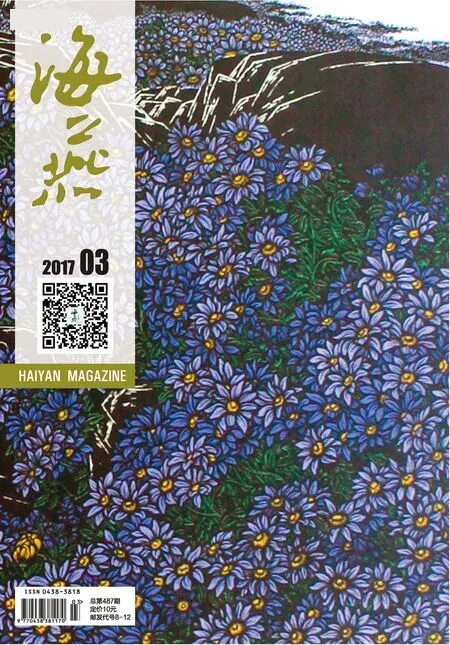食材三记
□隋英军
食材三记
□隋英军
鱼羊为鲜,羊大则美
鱼羊为鲜。汉字“鲜”是个会意字,鱼和羊均是美味,放在一起必鲜美至极。宋人徐铉为《说文》作注曰:羊大则美。古人把“羊”字引申为“美”字,羊大为美。《说文》中这样解释“美”字:“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看来,羊肉自古就是美味,古人亦对其垂涎不已。徐铉又说:“羊主给膳,以瘦为病。”又引申为“羡”,上为羊,下从“㳄”,“㳄”的意思是“慕欲口液”,看看把古人给馋的,望着羊直流口水。
羊,祥也。是吉祥的象征。《左传》中有则故事说的是宣公十二年时,楚国派兵攻打郑国,后来郑国被打败了,郑伯在投降的时候,“肉袒牵羊以迎”。“肉袒”是说郑伯脱衣露体,诚惶诚恐地表示请降。但郑伯在投降时为什么要牵着一只羊呢?就是因为羊象征着吉祥,在亡国的危险时刻,献上羊以祈求得到楚国的饶恕,使己免遭于难。不过,羊无论是否象征着吉祥,因其“主给膳”,所以又大又肥美的羊终究还是逃脱不掉人类的餐桌。人类大概在史前时代后期就把羊驯化完成了,驯化成功后当然需要宰食的,我们的祖先大概在那个时代就可以品尝大肥羊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因此,羊在最早的时候,除了配给贵族食用外,还被用来作祭祀用。古时由羊人来掌管祭祀和食用的羊。祭祀要用羊羔,把羊头割下挂起来叫做“升首,报阳也”,是指提助阳气。羊有多种吃法,涮烤焖炸炒炙均可。周代著名的“八珍”中要有三样用羊肉来完成,最著名的当属“炮羊”。“炮羊”是将整羊宰杀清理干净后在羊腹中塞上食物和瓜果,然后用芦苇等把羊裹好,外面再涂上厚厚一层草拌泥,然后放在大火中烧烤。和江南名菜“叫花鸡”的做法有些相似。待泥壳被烤干后敲碎,取出整羊,再用稻米粉糊涂羊周身,热油煎煮。煎煮后的羊再被切成小块加调料盛放于小鼎中,再将小鼎放在大汤锅中连续烧煮三天三夜,如此耗时耗力做出的羊肉,其美味堪称世界之最。
中医认为羊肉味甘而大热,性属火,食用后可以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开胃健力。北方人也把羊肉称作大补之物,所以冬天多有食之,最有名的当属涮羊肉火锅了。但,在我所居住的辽东小城却有在炎炎盛夏喝羊汤的习惯。烈日似火,一碗热羊汤,几口下肚便大汗淋漓了,野性一些的索性脱下衬衫以“膀爷”的形象出现,一任汗流浃背,亦可排毒养颜。大汗之后可稍作休息,再冲个凉水澡,或在溪谷池塘中野浴一下,如此最美,也最享受。也有人认为夏季喝羊汤不好,酷暑之中再摄取过量大热的食物,人容易上火,损伤身体。我亦对羊汤情有独钟,百喝不厌。我的一个朋友则从不喝羊汤,也不接近羊汤馆,他说那个膻味受不了。我总是不理解,羊肉、羊汤只有鲜和肥美,何来膻?另一位画家朋友老郭整个夏季一口羊汤也不喝,还经常告诫我,夏天不要再喝羊汤了,喝多了会得病的,比如高血脂、脂肪肝什么的。但羊汤对我的诱惑犹如光棍汉见到美女,实在是控制不住。辽东山区,山高林密水寒凉,所生产之羊即非绵羊也非山羊,更不是什么新品种小尾寒羊,而叫绒山羊。此羊肥硕、健美,整日在山林中食野草,啃树皮,喝山泉,肉质肥美,绝无腥膻。绒山羊在冬季来临前周身遍生绒毛用来御寒,待第二年春季,周身绒毛又将褪下,只留老毛。此时的绒毛要用特制的铁梳子梳下,即为名贵的羊绒,是制作高级羊绒衫和名贵织物的上佳材料。绒山羊以骟过的一年生公羊味道最鲜美,被称作“羯羊”。没有骟过的羊和母羊切不可烹煮羊汤,其腥膻之味让人受不了。
近日,城郊新开一家小馆子,名叫马家大院。专营农家饭菜,口味不错。老板姓马,做羊汤却是一绝。几次光临品喝之后,果然货真价实,遂由熟悉而变为朋友。嘱其每有杀羊,必短信告我。于是经常会接到马老板手机短信:杀羊了。见此三字,馋虫立马被勾出,定会去喝上一碗,大快朵颐。马老板对我说,其实,夏天不能喝羊汤是误传,绒山羊和草原上的羊、戈壁滩上的羊、黄土塬上的羊不一样,并非大热之物,恰恰有温凉之性,夏天喝羊汤,对身体有益。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佐证,我也不知道。不过马家大院的羊汤好喝却是公认的。每次老马都要到山区亲选“羯羊”,宰杀后先滤干血水,再用山泉水烹煮羊肉,将羊肉、羊骨头、杂碎、下货等一并在大锅中沸煮,且一定要用柴火铁锅,否则味道就会不纯了。而且用水是纯净的凤凰山泉水,一次加满山泉水后,连续烹煮五个小时以上,中途绝对禁止兑加生水,一羊一锅汤,售完为止。
其实,伏天吃羊并非辽东山区独创,《史记•秦本记》中记载,秦德公于公元前676年初置伏日,并初设伏祠,这是伏日的开始。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记载徐州人开始吃伏羊,徐州是彭祖的故乡,“彭祖伏羊节”就是徐州人每年一次的巨大盛会。徐州人认为,“三伏天吃羊肉,可强身体”,在一周的活动中,将会出现万人共吃伏羊的盛大场面。伏日到了,又因为新麦登场,新酒酿成,此时羊肥味美,便于操办宴席吃肥羊,所以每年入伏第一天为徐州人吃伏羊的开始。因地处丘陵地带,青山绿水,草木葱茏,从青草发芽到入伏前,山羊肥壮,肥瘦相间,鲜嫩可口,加上徐州特有的精制辣椒油,佐以青蒜、香菜和各种香料烹制,其味香汁醇,厚而不肥腻,汤色美白令人胃口大开。我个人认为,在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排汗排毒,将冬春之毒、湿气驱除,是以食为疗的伟大创举。由于羊最早是中国人驯化成功的,因此不论南北均出产著名的羊种,也出产闻名天下的羊肉美食,著名的有江苏苏州的藏书羊肉,其特点是肉质鲜美;山东单县羊肉汤,其特点是营养滋补;四川简阳羊肉汤,其特点是驱热排毒;内蒙古海拉尔羊肉,其特点是肉肥美无膻腥。这几种羊,无论放养于太湖之滨,还是青山绿水间,抑或莽莽草原深处,独特的山水环境造就了它们非凡的品质。“冬天羊肉赛人参,春夏秋食亦强身”,吃吧,老饕们,没有禁忌,四季皆宜,岂不美哉。
小时候家居山村,爷爷就是辛劳的放羊人。无论冬夏,无论风雨,羊每天都需要赶出来放养的。爷爷在后腰间捆绑上半张羊皮,在头羊叮当叮当的响铃声中隐入大山密林中。累了就席地而坐,后腰间的羊皮垫子是用来隔凉和防潮的。一群羊,羊生羊,为了生计,爷爷在二十余年间只从事这一项劳作,其枯燥和劳苦,又有谁知?如今,爷爷已经老迈了,别说去放羊,恐怕连羊肉也咀嚼不动了。每每饮酒吃羊时,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爷爷家赶羊入圈的场景,就会想起将“羊屎蛋”作粪肥在田间劳作的场景,就会想起母羊生羔,爷爷、四叔守在羊圈里彻夜不眠的场景,更会想起羊丢了漫山遍野去找羊的场景……
现在,正是青草发芽,羊肥味美的季节,我是不是该做一盘香喷喷的红焖羊肉去孝敬爷爷他老人家呢?
西红柿和蛋
西红柿和蛋,绝妙的组合。我不知晓中国人从哪里来的灵感,鲜红欲滴的西红柿,像少女的红唇,黄黄的鸡蛋黄,像夜晚的油月亮,白若羊脂的蛋清,如无瑕的美玉,热油爆炒,红黄白瞬间化做鲜红的红,油黄的黄,令人垂涎。甜酸香,令人难忘。
西红柿是乡下园子里的,蛋是家养土鸡下的,这在乡下是寻常的物件儿。倘若时光倒退三十年,这又是不寻常的物件儿,鸡屁眼里抠出的蛋可能是孩子的书费,祖母的药片儿,也可以换来针头线脑儿和盐巴。西红柿则更不一样了,它最有可能客串水果的角色,堪比现在的芒果、榴莲、大樱桃等。甜甜的、酸酸的,或酸中有甜,更像生活的滋味,童年的味道。
西红柿炒鸡蛋是一道好菜,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有营养,色香味俱全,就是好菜的标准,当然这是我这个非专业的吃货所定的标准,并没有得到权威的认证,仅供参考。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玉米馇子饭,或半个粗粮饼,两根大葱蘸酱,吃完了走人,赶紧上学去,哪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多事,吃得精细,呵护得精心,个个却都像根豆芽菜似的。
民间常说,萝卜白菜最养人。这说出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人乃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山川草木、水果瓜菜也是万物的一部分,互生和依存,相互生发,就这么简单。违背自然法则会带来折损、也会生病的。同样,做人做事违背准则和伦理道德,又怎么谈得上有修为呢?一个没有修为的人又犹如草芥和粪土。
西红柿炒鸡蛋,好吃。吃了几十年了,仍有偏爱,是我家餐桌上的常客。其实西红柿和鸡蛋也并非土得掉渣的货色。一种说法是说西红柿是舶来品,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地带,在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地,直到现在还有野生的种群分布。西红柿在16世纪由墨西哥传入欧洲时,在英法、西班牙作庭院观赏所用。斯时,其身价还是很高的。由此看来欧洲人的园林造景水平和中国人是没法比的。中国人讲究风水、五行,讲究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再布一长廊,弄几块太湖石,植几株修篁,配点儿牡丹,整点常青的藤子什么的,营造出一种氛围和意境。还可以再上演些“隔着乱红人去远,画楼今夜珠卷帘”的无奈离别和“冰绡斜映薄如烟,鬓云撩乱堕香肩”的私密幽会。就连最寻常的百姓家也要营造出“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唯美意境来。从资料记载来看,西方人可没有那个情趣,不知道是审美不发达,还是进化出了问题,种了满园子西红柿作观赏用,那和中国人城郊的菜园子有什么两样?其实欧洲人不明白,西红柿熟时的鲜红娇艳,红果配绿叶,如比做佳人,也是美丽诱人的。一场雨后也同样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说来,西红柿也是有洋基因和贵族血统的。
至于鸡蛋及由鸡蛋当食材做出的美味更是不胜枚举,本人将另作小文赘述。中国人曾有过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其实都是些无谓的争论,无论是鸡生蛋还是蛋孵鸡,蛋与鸡都可一饱口腹之欲。钱钟书老先生还有关于鸡和蛋的精辟论述,一位妇人看了钱老的文章后,立刻成了铁杆粉丝,非要一睹大师的风采,钱老传话:如果觉得鸡蛋好吃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见那个下蛋的母鸡呢?中国人还用“以卵击石”来形容自不量力,用“累卵”来比做情况危急。我小时候吃过的蛋不仅仅局限于鸡蛋,还有鹅蛋、鸭蛋、野鸟蛋、家麻雀蛋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在丛林中发现了斑鸠蛋,青褐色,像一个个圆溜溜的雕琢好的青玉,上面点缀着粒粒黑斑,只是比鸡蛋小了些许,大概有乒乓球般大小,有时连鸟巢一块取走,有时用青苔包裹着把玩,碎了就随手扔掉了,斑鸠大鸟在树林上方不停地叫唤,恨不得俯冲下来啄你的眼睛呢。这是童年的恶作剧,如果蛋孵鸟,鸟生蛋,该有多少只斑鸠飞翔在丛林山谷中啊。
再说西红柿。在它的原产地只是生长在森林里的野生浆果,当地人把它当作有毒的果子,称“狼桃”,无人敢食。在16世纪,有位英国公爵把西红柿当作礼物送给情人表达爱意,于是情人果、爱情果之名就远扬了。又过了100年仍无人敢食西红柿,直到有一位法国画家面对这美丽可爱而“有毒”的浆果,实在抵不住诱惑,就冒险吃了一个,居然没有死。于是西红柿无毒、好吃的消息传遍西方,又迅速传遍了世界。由此,西红柿从公园进入了菜园,由观赏变为食用。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和A以及叶酸、钾等营养素,特别是它所含的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有益。西红柿先传到中国南方沿海城市,被称为番茄,由南方再传到北方后被称作西红柿。
中国人向来有食补的传统,如果用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来解读西红柿,它又具有中药属性了。中医说,西红柿味甘、酸,性凉、微寒。能清热止渴,养阴、凉血,归肝、胃、肺经。具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清热解毒,凉血平肝,补血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
一个西红柿,如果你喜欢叫它爱情果,那卿卿我我中的男男女女们就别吃什么巧克力、开心果了,七夕那天,拎上几斤西红柿送给心仪的美人吧。如果你把它称作红宝石,那请在一个花影乱、月如水的静谧午夜,几个西红柿,一杯红酒,数声私语,醉个深沉。而我,还是让老婆来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吧,它朴实、纯粹、养人,清热除烦,安我身心!
黄豆芽,绿豆芽
芽菜类的菜蔬总给人生机勃发,葱郁向上的感觉。如果把素菜归类,我把芽菜比做素颜布衣,温婉可人的邻家女孩。她纤弱、娇嫩,惹人心生怜爱。
闲来读书方知,自古以来芽菜即为素菜之王。芽菜是指黄豆、绿豆、豌豆、蚕豆等种子萌发出数厘米长的幼芽,可做蔬菜食用。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种子萌动、生发了才产生了芽菜,因此芽菜是有生命的东西,多食有益。以黄豆为例,马王堆汉墓竹简上曾有“黄卷一石”的记载,黄卷即为晒干的黄豆芽。这一考古发现可以证明,中国人是豆芽的发明者。古书中还有记载,宋代福建泉州人在中元节前,“用清水浸泡黑豆,曝之以芽……色浅黄。”这就是著名的“鹅黄豆生”的记载。“鹅黄豆生”,多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让我想起了美丽的春天和春天里泛青的秧苗,踏青的裙裾……
一次,在一本明清笔记体小说中读到,有“芼”为羹者,总觉不妥,芼也可食?芼有“拔取、采摘”之意,是一个动词或者是一个动作。难道是要把一个“左右芼之”的清纯小女子给“秀色可餐”了?我猜想,大概是《诗经》中有采薇、采荇的场景引发了明清作者关于芽菜的遐想吧。《诗经》“关雎”篇中有“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的句子,《诗经》中还有关于“采薇”的篇什。其实,荇是一种野生水草,嫩叶可食。薇则是豆科植物,今俗名为大巢菜,另一说法是指野生的豌豆苗。这些都最接近于芽菜的特质,被古人谬误为“芼”也可食吧。就在我为自己这一推断沾沾自喜之际,又一次偶读闲书让我大惊不已,脸红汗颜。原来,“芼”本意是指可供食用的野菜或水草。这些野菜或水草祭祀时被用来覆盖牲体,故而有“覆盖”之意。《礼记·昏义》:“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清人吴伟业在《江南好》诗中有“鸡臛下豉浇苦酒,鱼羹如芼捣丹椒”,这里的“芼”也是指可以食用的水草。但最新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芼”的解释只有一条:〈书〉拔取(菜、草)。真是害我不浅啊。但,做学问还是要端正态度,严谨为好,浅尝辄止,同样也会害人的。
我们北方人所食以黄豆芽、绿豆芽为主。小时候家住荒僻小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哪有今日南北菜蔬遍地,时令青菜遍布城乡之况。黄豆和绿豆虽是自家地里耕种出来的,但相比于苞米、土豆、大白菜已属上品。黄豆要等到年节时用来做豆腐的,吃豆腐、喝豆浆,甚至豆腐渣也被掺入青菜叶子炒或炖食了。黄豆最主要的用途是榨豆油,油滤尽后,油渣压成饼,即为豆饼,又是牛马驴骡的好口粮。小时候,我们甚至把豆饼切成小块放在煤炉子上烤吃过,也是满口溢香。所以,黄豆、绿豆生成芽菜也属奢侈品了。黄豆芽配以肉丝爆炒,下饭、扛饿、有营养,如再有个好牙口,更是愈嚼愈香。我老娘是生绿豆芽的高手,她生的绿豆芽比菜市场里卖的要好吃百倍。因为没有添加任何生长剂、除根剂等乱七八糟害人的东西,实属绿色食品。小时候,见到我的太奶生绿豆芽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太奶将绿豆放在木盆里,用井水浸泡后,小脚的她老人家端坐在火炕上,用一木勺在盆中不停地搅拌,嘴里喃喃说:“绿豆、绿豆快生芽,瞎子、瘸子都出芽。瞎子、瘸子都出芽……”那个时候,物质短缺,每一粒绿豆都生出了芽芽该有多好啊。
其实豆芽在古时,远比今日要高贵、神秘许多。今人只是在大鱼大肉吃腻了,吃出了病患,才想起食素来着。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称豆芽为“大豆黄卷”,并被列为“中品”。古人造“大豆黄卷”要选择在壬癸日,也就是冬末春初之时,用井水浸黑大豆,候芽长五寸,干之即为黄卷。豆芽生长的过程,古人甚至用卦相来描述:“从艮而震,震而巽矣,自癸而甲,甲而乙矣。”豆芽初生芽时曰黄,黄而卷,则具备木性了。木为肝藏,藏真通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大筋聚于膝,膝属溪谷之府也。故主湿痹筋挛,膝痛不可屈伸。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最早的豆芽菜首先是用于食疗,大概是治疗膝痛不伸,湿痹筋挛等症状吧。除了食疗,我还读到古时道家用豆芽来养生的记载,可见古人对豆芽类菜蔬的认识程度要比现在高许多。
到宋朝时,中国人食豆芽已相当普遍了。豆芽还与笋、菌一起被称为素食“三霸”。纤秀爽口的豆芽成为“一霸”,可见古人对其推崇的高度。宋元时期吃豆芽,主要用于凉拌,和今日吃法雷同。《易牙遗意》中记录了一个生豆芽和吃豆芽的方子:“将绿豆冷水浸两宿,候涨换水,淘两次,烘干。预扫地洁净,以水洒湿,铺纸一层,置豆于纸上,以盆盖之。一日洒两次水,候芽长,淘去壳。沸汤略焯,姜醋和之,肉燥尤宜。”“沸汤略焯,姜醋和之”就是凉拌的吃法了。“肉燥尤宜”,我的理解是把豆芽配以肉丝和葱姜蒜末,用热油爆炒的吃法。
但无论什么样的菜蔬,若是落到文人手里,便会变得繁杂、拖沓,讲究个时令、心境,甚至变得之乎者也,非得翻出个文化的花样来。明清时的文人们食用豆芽开始讲究个入汤融味。《随园食单》就有记载:“豆芽柔脆,余颇爱之(必定是个文人的口气)。炒须熟烂,作料之味才能融洽。可配燕窝,以柔配柔,以白配白故也。”嫩嫩的豆芽配上名贵的燕窝,还美其名曰“以柔配柔,以白配白”,真是讲究,但也酸腐。不过,老祖宗还真有创意,今人不及也。
黄豆芽也好,绿豆芽也罢,因其物美价廉,既可进华堂入国宴,亦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餐桌。西方人把豆芽看做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把豆芽、豆腐、大酱和面筋称为中国食品的“四大发明”。其实,中国饮食文化之渊源,又岂是几个西方人所能知晓,又岂止四种。据说,豆芽是李鸿章出使欧洲时传入西方的,因此豆芽还有“李鸿章杂碎”之说,现在西方有些国家和地区还把豆芽称为“杂碎”。听了也不甚舒服,龟孙子们不懂中国文化,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给糟蹋了。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