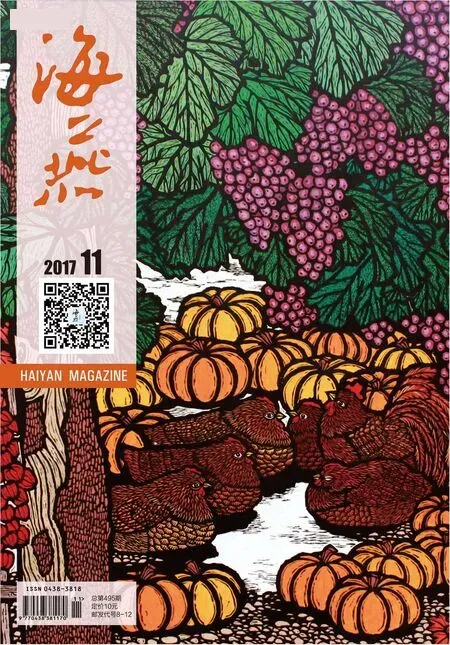“我只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
——王宏军诗歌论
□姜超
“我只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
——王宏军诗歌论
□姜超
当下诗歌貌似一派繁荣,实则假风甚炽,乱象纷呈。假慈悲者在大嚼烤乳鸽后,对受伤的麻雀和挨饿的穷人视而不见,却在诗歌里大发慈心。连儒释道基本常识都没搞明白,一些诗人偏偏接连借用词汇,眉头紧锁故作高深。很多诗作俗不可耐,归于无聊;大多数诗歌不疼喊痛,陷于浮夸。与其东躲西藏而拼命伪饰,莫不如像王宏军这样胸怀磊落,尊崇本心,自然成诗。王宏军年届中年,世事浮沉不知多少,却坚持直言快语,他入世但不遁世,深情但不滥情。他的诗歌看起来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小问题,但它们将顽韧与柔软合二为一。他的很多诗歌喷洒着血性披挂上阵,戳破虚假,扬起猎猎阳光大旗;另一些嘘寒问暖的诗作百钢化作绕指柔,如玉温润心灵,如《致动荡国度的那个黑孩》《晾玉米的老人》等诗作读来让人心思久久不能平静,洋溢的是一种大关爱。
王宏军对实在人或有才华的人一派赤诚,敢于掏出肝胆,但不屑与宵小或者伪善之辈为伍,真正实践了“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的古语。我对其诗的关注,源自对他为人、为事的高度认同。王宏军写诗不爱叠床架屋,也讨厌花拳绣腿,他看中的是直述内心的切近方式。 “在搜求诗的内容时,必须追究自己的生活,看其中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感觉,一吐为快的。”王宏军的诗歌就是这样的热烈倾吐,这样的诗朴素且真挚动人,这样的诗篇也许不是冲天烈火,但如恒久的炭火,始终炙烤着全世界。是的,王宏军不太会显幽烛隐之术,他那些老老实实的诗句充满诚挚,笨拙的音调里藏有诚意。正所谓修辞立其诚,王宏军的诗歌努力值得肯定。不管何时,你对世界真,世界才会予你馈赠。只有坏人才拼命装好人,才用伪装来显真实。王宏军近年重拾诗笔,将前半生的思索归为虔诚地叩问,仿佛“储备整生的热量/只为了写一首让人寂寞的诗(洛夫语)”。他飞蛾扑火一般的自在精神,照亮的正是真实的人性和生命的大美。“火盆里的烙铁/先于太阳的/温暖”,王宏军的这句诗夫子自道,他的诗歌就是不停歇地洗心,就是在为自己的灵魂洗澡。王宏军用滚烫灵魂发声的诗歌,召唤已渐渐走远的本真。他的诗歌是深入现实,而非代入,亦不是植入。那个随时在街道俯身拾起垃圾的人,那个看见弱者或者可怜人就难受半天的人,那个半夜用手机写诗且不断回看的人,合并为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王宏军。
帕斯捷尔纳克说:“诗歌无须到天上去寻找,而要善于弯腰,诗歌在草地上。”王宏军的诗歌草地确实是弯腰获得的,它们是匍匐于地生长的茂盛植物。王宏军是永远接地气的人,他笔下的村庄不是某些诗歌观念的“客观对应物”,而是血肉丰满的生命体验。看苍茫大地,演绎生死哀荣,王宏军表达的是原初的意义,视野从来没有飘移过。他没有将乡土与城市对立起来,甚至连缠斗都懒得去展现。王宏军受过高等教育,对哲学也颇有心得,在诗中却不愿意摆弄这些。他的诗歌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念与技法统统抛在一边,径直展开的就是鲜活的乡村经验。此种做法颇似“我手写我口”,但在当代诗歌中也别树一帜——当下书写乡村的诗人多远离乡土,即便是地道的农民诗人也在琢磨如何让诗歌看起来国际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乡土诗歌更像是隔靴搔痒式的自我抚摸。乡土诗歌不缺技术,唯独缺少良心。王宏军不是回望家园,而是真情“探望”,传达的是物我同哀的在场体验。唯此,他的诗歌更像是对乡土的血亲指认。作品《布谷鸟》的第一节情感如是,亦可以看做是王宏军内心之幔:
夏日来临
你站在枝头
或振翅
奔袭于绿野
一声声鸣叫:
进屋、进屋、快进屋
把故乡喊得
如此热情
王宏军笔下千呼万唤的村庄,并不是眼下的村庄,应该是原始思维下的前现代村庄,它满是土地的百般艰辛和贫穷记忆。他是苦难亲历者、亲近者和言说者,用诗歌写出了一部真实的心灵简史。王宏军把对生命和世界的领悟,寄托在乡村的微风、流水、大树、燕子等上面,诸如“恬静的清晨里/母亲的炊烟早于/太阳升起”等诗句,完全是深味乡村经验者才可发出的心灵之语。美国作家奥康纳说:“一个作家所能拥有的巨大祝福,也许是最大的福分,就是在家乡发现其他人必须去别处发现的东西。”这话仿佛专为王宏军所说。他诗歌经验的策源地就是他的出生地,这是王宏军针尖上的蜜,驱策着他献出全部的情感能量。黑龙江省海伦市福民乡众福村,就是王宏军的第一思维,是其诗意的起点和终点。王宏军熟稔乡村物事,对草木、庄稼、牲畜的一腔热爱。牛庆国说:“回望故乡时,心里涌起的那种东西就应该叫做‘诗’。”王宏军的诗歌经验“不隔”,这源自他始终使用第一手经验。他的这类诗歌物我一体,主客体殊难分开。
哲学家以塞亚·伯林说:“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王宏军的诗是非神性写作,但离不开现实的苦涩,也离不开揭示,并提出了自己的疗救方案。王宏军不愿意看到乡村日益凋敝,他已经为故乡的繁荣积极奔走,全力助其发展。但乡土外的现实又用决绝的姿态切断了现代人返乡的途径,它留给我们的,只是昔日故乡一个模糊而落寞的背影。众福村作为“被抛”的存在,既是云端里的华彩,更是泥污里的莲根,是神性大地的肉身。英语中的“乡愁”,可直译为“家乡的病”。换言之,文学中的乡愁若无疼痛,几乎贱如废铁。乡愁,并非变动不居,于近三十年来说,不知发生了多少变迁。就吾国目下风行的乡土诗歌来说,几乎朝着偏离回乡之途的方向用力呢。如果诗歌里的故乡不能引领人回到最原始的经验,那真是形迹可疑了!乡愁有大美搜求,但造就“乡悲”的诗人无异于万箭穿心,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呀。好在,王宏军笔下的乡愁没有成为乡悲。王宏军艰苦行吟,无非是想让苦难融入骨血,这颇似蚌病成珠的经历。
仁心妙术出佳篇,好诗讲求技术,但永远要求诗句靠近灵魂。好诗,始于感动,精于才艺,成于老辣。王宏军的诗歌不假修饰,语词结实硬朗,节奏昂扬有力。王宏军信仰大道至简,追求文字的洗练。洗练,来自思维的淘洗,然后去锻造、淬炼,将那些围绕在诗句周围的无用之物统统烧掉,而最终实现语词的光亮闪闪。诗意的生成离不开语言的打磨,但过度的打磨反而丧失了最本质的东西。好的乡土诗歌,恰恰应当葆有土腔土调,那样才会有荡气回肠的奇效。王宏军的诗歌有了这样的态势。乡音,让故乡在场。他作品中的声音,源自泥土,始终是在本乡本土中觉醒的语言。如海德格尔说:“在方言中根植着语言的在场。如果说土话是母语的话,在方言中也根植着栖居的乡土乡情,栖居着家乡。土话不只是母语,而且同时并首先是语言之母。”乡音是天地之间的珍贵回响,王宏军贴近大地,像扎入泥土的根不舍大地。王宏军的诗明显有广袤苍凉的大东北气质,但在建构诗歌时自觉远离方言,他高举的是带有土味的语言。
王宏军希望诗歌能直抵事物的核心。他的诗中时常出现父亲、母亲的形象,并借助梦境频频展现。王宏军很多诗作中有母亲劳动的场景,母亲的形象温暖而清晰,温暖的细节频现于小叙事当中,很像美好记忆的复现;诗作《棉鞋》仿佛要挽留住时光,试图让美好的事物缓步徐行,充满温暖明亮的气息。为表达此类意思,王宏军似乎拨慢了时钟,为居留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做着美学努力。在塑造父亲形象时,王宏军采取皴染之术,父亲变得模糊而遥远,即便有父子交流的场景,也像是隔空的倾诉,颇似一次次严肃的精神对话。这与汉民族的含蓄传统密不可分,也与王宏军个人成长经历相关。诗作《父亲的猎杀》直述凶残与无奈,读来让人心悸;“他只是用最简单的办法/从大黄狗的胃里/讨回属于自己的玉米”,我觉得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最好的乡土诗句,它是那样的直接有力,仿佛寒光一闪就达到了一剑穿心。他对乡情血肉亲情的表述,述写出了不奇不异的众人共有之意、共有之情,往往能催人泪下。他还经常选取日常化的场景入诗,通过拟真的语言表达,有时收到“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的效果。
诗歌不负责“绝对正确”,那样反而戕害了艺术,好诗歌永远不排斥用“僭越”来纳“投名状”。王宏军的诗歌苦涩但不排斥幽默,诗作《卖冰棍儿》生活现场感十足,且充满诙谐,其精神非常接近李老乡,最后一节堪为绝句:
时隔这么多年
我才知道
孵不出小鸡的鸡蛋
叫实蛋
烤着吃要比新鲜鸡蛋
还有营养
原来那时
乡下人的欺骗
也是善良的
一切的忧伤,通过王宏军对苦难的独特人生颖悟,都变得举重若轻,趣味横生,苦难反而成了生活的调剂。王宏军将苦难的感受放置在喜剧情景里,营造了一种“笑谑”的语言,它谑而不虐,书写着丰富的人性。如若想追求更高的诗艺,王宏军还要多写诗,在情感与形式上投放更多的精力来。如此,诗才可穿越俗世为心灵沐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