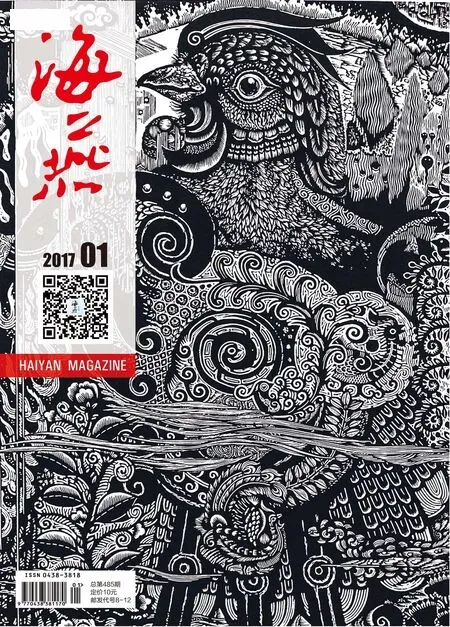送礼的小孩
□曹明霞
送礼的小孩
□曹明霞
应该是三十多年前了,在我们的县城老家,平房所在的那条街上,那个叫小波的女孩,她又一次让我好奇:大冬天里,呵气成霜,她左手扶着自行车把,右手,去提车把外侧挂着的松花江牌革制大兜——地上滑,冰冻的霜雪像石头,自行车滑倒了,她的手指也一定冻僵了——大兜掉在地上,发出哐当的一声脆响,是玻璃碎裂的声音。小波顾不得扶她的自行车,猛地蹲到地上抢救——她的提兜里是水果罐头及烟和白酒,槽子糕,那个年代典型的四盒礼。遇到这么硬的冰地,玻璃如同鸡蛋碰上了石头,全碎了。槽子糕包装纸上浸着油,两条烟也有薄薄的一层塑料,使甜水和酒精都没有浸润进去。小波心疼两瓶罐头和白酒,看着无法收拾的液体和碎碴,她横起一只胳膊到眼睛上,呜呜哭了,嘴里含混说着让他们别锁大门,别锁,就是不听。这下好了,还送礼,送个屁吧呜呜呜……
我跑上去帮忙。她家的大门,是用一块块竖着的板子连起来的,中间斜拉一道铁丝,算固定,上下的板端是参差不齐的,如果小孩或大狗从下面钻,一点困难没有。门框是两根圆木,权作立柱,一条铁链子,从板子的缝隙穿过,再连到门柱上,加一把锁,算是防盗了。这样的大门,确实无锁必要。刚才小波,就是一手想扶车子,又怕兜子滑掉,又得兼顾着掏钥匙开大门——我安慰她说小波姐,别哭了,来,我帮你开——小波哭掉的眼泪流到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冰洞,她侧过身让我去她兜里掏钥匙,她的手指已经冻僵,她嘟囔着说这么冷的天,我爸他也不着个家,什么爸啊。
小波的爸爸在我们那条街非常有名,一是他喝大酒,二是打老婆。小波的妈妈在她十三岁那年,就喝毒药决绝地死了,留下三个孩子。她爸爸从此愈加的以酒度日,那时候,一元钱能买一斤散装酒,有一个相声讽刺过这样的男人,说他们是“一元糠夫”。小波的爸爸因此也有了“一元”的绰号,像个日本人。小波是家中长女,十五岁那年,她就不读书了,找了一个县委的对象。小波家族有异族的混血,她长得非常漂亮。据说县委的那个小伙子对她的容貌非常着迷,最近,正思谋着带她去送礼,把小波的工作也安排到县上去。
县上,在我们的概念里是政府,是最有权的一个庙,能在那里上班的人,都是大人物。后来,有半年多的时间吧,小波果然到县里去上班了。先是打字员,后是办公室机要,再后,转战到粮食局,当了一个风不吹雨不淋的开票员。那还是一个吃粮食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开票员,很肥很肥。
“四盒礼”的鲜明记忆,就来自小波。后来,我上班了,同事的爸爸是厂长,我们去她家玩,在她家的酒柜里,经常看到森林一样的各式白酒,水果罐头。想必“四盒礼”中的槽子糕,已经被她们吃掉了,烟和酒,供她爸爸细水长流。这些白酒和水果罐头,一批批更迭着品牌,商标的普通或豪华随她爸爸的沉浮而载沉载浮……
民谚说:大小是个头,强其戳岗楼。这是这个国度的特色。
只要持衡拥璇,就拥有一个关口,关隘。想过者,皆低头,且手不能空也。
送礼的滋味,是若干年后,我才品尝的。带着孩子来到异乡,十几年里,孤苦,不单表现在家庭人口上,时而,那经济上的窘困,一人抚养孩子的艰难,让年纪小小的女儿,比同龄孩子更懂事。那时,每当她拿回那名目繁多的学杂费单,我都无声发愁:工资才有二百多,而这一开学,就要去掉两百,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呢?这时候,女儿总会再抽回去,在上面,试着划掉两项,问:这样行吗?——似乎她就有这样处置的权力。
这一动作让我心生疚痛,疚痛又转化成怒火——那个人,真的就可以这样逍遥?吃饭时,桌上报纸的一则消息,又加剧了这一愤怒。报纸上说,关于抚养费,法律上又有了什么新规定,追索机制,拒不付的,怎么怎么样……是孩子先看到的,她轻轻移开碗,怯声说,妈,你看这个。
那顿饭,吃得我好噎,孩子还这么小,心里却要装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事。深深对不起的同时,胸中怒火更加万丈,下决心,改名,换姓,我们就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那样一个人!孩子,是我自己养出来的,上帝给的,天生。
就开始了漫长的跑派出所,送礼,求人。
先去了户口所归片的派出所,那是一个面相还善、且有福气的女人的脸,额上一颗饱满的圆痣。我对她满脸堆笑,讨好的笑,乞求的笑,陈述了那么多那么多,请求她根据实际情况,实现我们的愿望。
但她公事公办,一二三,四五六,一条都不行,这是规定。
下一次,再去。我像当年的小波一样,也带去了几样礼,带去了我的恭顺孝敬——但时代不同了,不是四盒礼的行情了,土特产,早已过时。也许,这些东西让她们更烦,不但不起作用,还激起了女户籍员的火儿:她只扫了一眼,声音当时就提高了,并清白地站起来,离柜台远些,再远些。她大着嗓门像在给全世界讲道理,批评教育我,不该这样,拿公职人员开玩笑吗?甚至接下来嘲笑了我的异想天开,派出所又不是给你家开的,拿一点东西就能违法办事吗?公安部已经明文规定,谁都不许再随便改名,现在犯罪分子老是改名换姓,查都不好查,给侦破工作带来多大障碍啊!尤其是那些杀人犯,在逃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女户籍员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斥得我既无地自容,又怒火万丈。泪水在我脸上汹涌成河,但转化为我发飙的马达:是你们无能,你们内部的一群废物,抓不住逃犯,就给良民设障碍。一人有病,你让所有人吃药,你们,你们,你们……我的痛斥也许有一点道理,女户籍员的脸色和声音都渐渐低了下来,开始给我解释,说理解我的情况,很多人都这样,但她也没办法,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得公安局长批。她一个多年要好的姐妹,想给孩子改名,她都不敢,没办法啊,这是上级规定。最后,她给我出了两个主意,一是,找硬关系,托人,托到局长那,也许能办。第二,就是耐心等,等到孩子长到十八岁,她自己来申请,可以。
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中,也求过人,送过礼,都很难。
女儿就长到了十八岁。
长大了的她,已经独自办过很多事情了。比如开学,带着行囊自己去报到;去交什么表,包括家里的水电费。派出所更名这件事,先期要交很多资料,她已经看出了我的怵头。她说,妈妈你不用管了,我自己去。
一趟一趟,年轻的她,腿脚和眼神一样天真,无邪,不累。
我问她:你要不要,带一点东西?
她说不用。
我是准备了一份女士礼品的,这回,应该拿得出手。给孩子看时,我内心复杂,既想到了当年的小波,大冬天里,她打碎了四盒礼时眼泪掉到雪地上砸出的小冰洞,那个让人心疼的场景,又侥幸想:现在,我们手续都齐全了,也许,那个户籍员,能看在一个孩子的份上,动一动恻隐?
来来回回,女儿效率很高。终于有一天,她告诉我,妈妈,成啦。
那一天,我们无比欢喜,像完成了一件盛大的工程。从此,女儿就成了我一个人的孩子,从精神到心理,我们都得以解脱。完成了这个,像去掉我一块心病,自此,生活上再出现别的沟坎,我基本听之任之,不去送礼,不去求人,更不会,让女儿像小波一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的生活,走到了有光的地方。
现在回想,无论我们这个国度的送礼特色多么根深蒂固,都不该,让一个小小的孩子去送礼,这样,是太戗害,太难为她们了。时光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小波冬天的那一幕,还时常浮现。前几年回老家,听说她已经到人大去工作了,丈夫,也升任为组织部门的一个领导。她的“一元糠夫”爸爸,因有她的供养,照顾,还长命地活着。小波胖了,一个生活优渥的妇人。邻居说,现在,她家已经是别人总给她们送礼了,风水轮流转啊,小波好命。
邻居的啧啧让我五味,冰天雪地,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面对一兜碎裂的玻璃瓶,那条横到眼睛上的胳膊,电影画面一样,永远不能抹去……
责任编辑 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