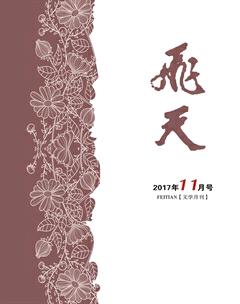干旱之花
赵兰振
这里应该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年降水量不足200mm,蒸发量却高达2000mm。70年前这儿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战役——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山城堡战役。历经四分之三世纪,这场战役的战壕竟然还在,某年偶至的雨水甚至没有淋坍它,它横在一个俯瞰开阔地带的小山头上,跳进去,仍然可以隐蔽起来不被发现。近百年的风风雨雨竟然没有湮灭它,也没有蕩平它,可想而知此地缺雨到何种程度!听当地人介绍,旁边站着的稀不愣腾的几株白杨树,树龄至少也有50年了。那树不多的叶片确实也碧绿着,但树身柴不拉叽,刚有一条生过小儿麻痹症的病腿粗细,表面黑暗,疤痕累累,疙疙瘩瘩的。看着这株柴瘠的老树,你不能不生出感慨。在雨水丰沛的华北平原,一株三年龄的白杨树树身肯定要比这株岁逾50者更粗硕。即使作为一株树,生对了地方也很重要。但华北平原上的白杨树鲜有活过50岁者,连30岁者都不多见,从这一点上看,守望在没有雨水的旱山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儿作为战场不只是70年前,700年前,或许7000年前,这儿应该都是战场,兵燹频仍。当你走在那一座座黄土山包上时,你不时能望见一柱柱陡直的堆土矗立,像是没事儿干的人故意垒起来做游戏玩的——那正是古时的烽火台,是连绵战事的遗留物。这儿长期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族裔争夺较量之地,因而也就成了战场。周朝崛起的最重要开国皇帝不窋,曾经居住在戎狄之中,应该即在此地,因为自此朝南走上不足100华里就是周祖陵,不窋帝的墓葬之处。但当时雨水肯定比今天要丰沛,不是鱼米之乡,起码也应该碧草无边,否则不会吸引游牧部落居住于此。但也许此后很快气候发生了变化,一下子干旱起来,于是这儿仅仅成为了一处通往关中平原的孔道,而居民却愈来愈稀少,从而那些战争的纪念物——烽火台也少有雨水侵袭得以保全下来。
是的,这儿是环县,位于甘肃省的东北部,与宁夏的固原地区接壤。这儿有一条著名的江水,叫环江。环江名是一条江,但江水并不深,也不宽阔,要是一个人横躺江上,脚搁在这岸,头枕着对岸,可以保证两头都能干燥,被水沾湿的仅是肚脐之下的身体。但这条瘦水在这儿就有了江的名字,而且这块偌大的山山峁峁因这条江命名,叫环县。据说环江并不总是这个瘦弱模样,到了某年暴雨骤至,它也滔滔不绝,浩浩汤汤。一个轻易不发脾气的人,一旦耍起了性子,确实也够看的。你看看环江的岸坡,就能知道它的脾性何等暴烈——那哪里是河坡,分明是陡峭的山崖,刀削斧劈一般,呈90度角笔直而下,像高墙一般护卫着深不可测的谷底的一线水流。当然,洪水激荡的时候,高崖之间的深邃谷涧,肯定是日夜波浪轰鸣,雷霆万钧,和平时的和煦气象判然有别。
写水的文章,当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范仲淹写作此文是受好友滕子京之托,当时并没见过岳阳楼,倒是刚刚从环庆地带返回京都,说不定他写的那水,充满了环江潮湿的气息,有着环江的影子呢。范仲淹是宋代庆历元年镇守环庆一带的,主政三年,时值西夏王李元昊入侵,边事告急。胸怀坦荡而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友爱民众,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并且采取迂回策略御敌,让西夏兵不战而退。当时传诵着一句民谣:“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心胆寒”,足见范仲淹镇守边关的卓越成就。当然,也正是因为其治下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仲淹才进一步得到朝廷的重用,而他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中国文化人的人生格言,代代相传。
环县的一切都因旱而生。因为干旱少雨,这儿地广人稀,将近一万平方公里的偌大地面上只居住有30多万人口,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在华北平原,一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县的面积,至少居住1000万人以上,是环县的几十甚至上百倍。历史上的干旱与兵燹是环县人口稀少的最主要原因。环县的黄土层甚厚,应该是地球上黄土堆积最厚的地区之一,那些富含养分的土壤只是因为缺水,平素难有用武之机,而一旦有了少许的水,厚土们会踊跃欢呼,使出全部力量来生长植物,显露它们厚积薄发的能量——你可以尝尝环县的杂粮:小米、绿豆、豌豆、燕麦,甚至油麻,那才是美味,和天下所有其他地方的粮谷均有异。那是土地的精华偶露,有着最内在的质地与味道。庄稼生长得如此不寻常,做法上又独树一帜,环县的杂粮食品在花样繁多的食品中当然就偶露峥嵘。那些利用最短暂的雨水季节奋力生长的油麻,出产的油汁味道也格外香,清香,这是美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当然,不仅仅是杂粮,在这样干旱的地区,昼夜温差如此显著,膨大的糙皮蜜瓤的瓜果愈加香甜自不必说。那些瓜果不一定模样耐看,但一律内慧,一律香气四溢,让你吃一回记忆一辈子。可惜因为干旱,这些杂粮与瓜果的产量不高,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让环县名满天下的不只是这些美味的地方特产,其独有的道情皮影,被西方人称为“东方魔术般的艺术”,是我们国家第一批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遍布中国各地,但只有到了环县一带才有了变化,坐在前台耍线子的艺人不但灵活地支配着线子也支配着人物的生死恩怨;更重要的是,他开始配合着人物起伏无定的命运歌唱,而且唱腔是这一带独有的道情。道情本来是道士们为了弘扬道教在闹市街头向人众拉长腔调的宣讲,但不知怎么一回事儿,七变八变,似乎宣讲道教被弃之一旁,竟然变成了一种类近质问与呼唤的唱腔,宣泄人们胸中积压日久的各种情感。“夫天者,人之父母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是体会人生滋味至深的司马迁悟出的真理。在环县,在极度的干旱和战事频仍中,动荡奔波中的人们一次次濒于绝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呼天号地成为一种本能的情感反应。而道情,正适应了困苦中人们的需求,于是生发繁衍,长成了一种独立的戏剧。而皮影戏也接踵而来,因为其简便,“一驴驮”就可以囊括其所需的一切道具;戏班子也不需要人多,少则三两人,多则四五人;在偏僻的窑洞里,只需要一盏油灯,就可以让三皇五帝到如今发生的所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一重现,同时更可以重现人们的爱恨情仇,凄惶苦难日月。道情与皮影在黄土高原不期而遇,一拍即合,开始唇齿相依,一种全新的艺术随即诞生,接着渐渐成熟。道情皮影最繁盛的时期,环县竟然有几十家戏班,活跃在这里的沟沟峁峁。即使近些年普及了电视,电影也在多年前被打入冷宫,但
道情皮影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让环县人享受着沿袭着祖先的习俗,享受着这独特的民间艺术。
在繁星密布的冬夜,在无尽的黑暗与荒凉中,一盏灯亮了,一群人物突然鲜活地映现,接着一个悠扬的高亢唱腔猛地平地而起,击碎深深的黄土窑洞里的沉寂空气,也击碎每个洗耳倾听的人的心事……这就是道情皮影。
在环县的高峁深壑间,在冬夜里的黄土窑洞里,淋漓尽致地看一场道情皮影戏,该是何等美妙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