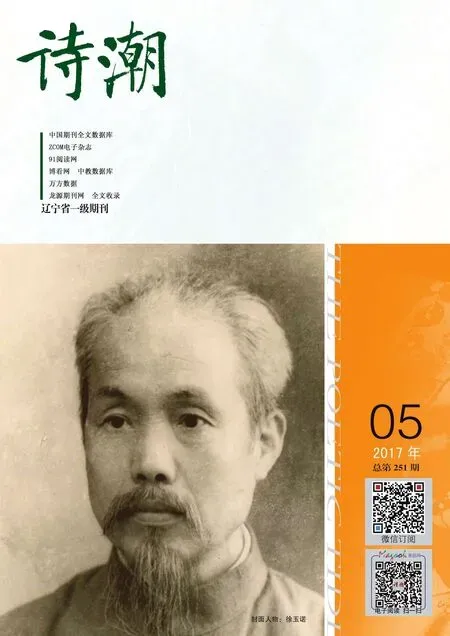鲜艳的果实会嘲笑种子吗
——关于“新诗百年”的几个问题
荣光启
鲜艳的果实会嘲笑种子吗
——关于“新诗百年”的几个问题
荣光启
约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不断的有学术会议在总结、讨论“新诗九十年”“新诗百年”之类的话题。这些年不管是诗歌界还是学术界都有这样的题目,开过好多次会议。诗人们之间,也喜欢做高端的访谈,总结彼此的成就。2016年更是热闹,新诗似乎是真正的一百岁了,一个大整数,多么招人喜欢。为什么我们这么热衷于谈论“新诗百年”,这里面除了真正的学术问题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一、新诗“百年”了,真的吗
若从时间上抠,一般认为新文学是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胡适(1891-1962)《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为开端;而第一首新诗,一般认为是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的“白话诗”——《蝴蝶》,它写于1916年8月23日,发表于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上,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但严格说来,新诗更早的“第一首”可能是胡适1916年7月22日写的《答梅瑾庄——白话诗》。此诗可能比《蝴蝶》更接近“白话诗”。好,这个我们不提。我们问:在这些诗之前或之外,有白话诗吗?有的话,算不算新诗的起点?
比如有人就认为第一首白话新诗应是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的《民呼日报》,诗题《元宝歌》,署名“大风”。据查“大风”即是于右任(见《于右任辛亥文集》)。全诗如下:“一个锭,/几个命,/民为轻,/官为重。/要好同寅,/压死百姓,/气的绅士,/打电胡弄。/问是何人作俑,/樊方伯发了旧病。/请看这场官司,/到底官胜民胜?”于右任是否大人物、大学问家?这个是不是更像白话诗?
如果你了解《圣经》的中文翻译,你就能读到许多现代诗,举例:“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旧约·诗篇》32:3-4)这样的诗歌在《圣经》中很多,不“现代”?我想告诉你,英国传教士杨格非(JohnGriffith,1831-1912)有《诗篇》译本,时间是1886年。近代传教士带来的白话文,可以追溯更早。1830年代的报刊上的白话文,就已经和今天差不多了。如果我们回到19世纪的历史场域中,好好考察那个时代的语言和文学,也许我们有更多的发现。新诗至今只有“百年”,真的吗?凭什么?
二、你真的读懂了“两个黄蝴蝶”了吗
即使是关于《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无心再上天,天上太孤单。”我们读懂了吗?比如《于坚、多多、王小妮、李亚伟、雷平阳、徐敬亚、谢有顺谈“中国新诗90周年”》:“从《尝试集》来看,中国当时的诗歌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徐敬亚)“其实新诗最初的阶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都是大白话,比如胡适著名的‘两只蝴蝶天上飞’,确实是口语,但也过于直白简单了。”(谢有顺)如果你参照胡适留学日记,你看一下胡适当时跟他的朋友们(胡先、梅光迪、任叔永等)的关系,就知道这首诗的历史的语境,它不是梁山伯、祝英台的“蝴蝶”,不是庞龙那样轻浮的流行歌曲中的“蝴蝶”,它是文学先驱者的那种孤独感,兄弟们分道扬镳的那种疼痛。他写的可能是这个。那么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你就知道它不是简单,它很有意味,它很沉重,或者有其他的意思。
诗该如何去读?一个基本的道理:文学作品的意蕴不光来自审美的层面,也蕴含在具体历史语境当中。这好比博物馆的一个破陶罐,从美学的层面,它可能很简单,没什么可看的。但是,考古学家却在认真思忖,细细考察其在历史中的意味: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物品呈现这种形态?围绕这个物品的历史语境有哪些?应该说,那个陶罐的美学效果,由这些信息系统构成。单凭表面上的形态,它确实不够“美”,但是围绕它的在历史当中的丰富意味,不也是属于它的吗?这样看待一首诗,是否要有趣得多,专业得多?
三、鲜艳的果实是否会嘲笑种子
2016年除了有关于“新诗百年”的学术会议,还有很高端的访谈。一个朋友这样写道:“总结新诗百年以来的诗人和作品,学院派的主要精力继续在解读新诗开始阶段的那一拨诗人,和几个当红的朦胧诗人。我的观点大相径庭:新诗一直在往成熟的方向进化,新诗百年里表现出成熟品质的诗人,要从第三代诗人里开始往后找。若一定要说之前的诗人,我宁愿选名气没那么响亮的弦、昌耀、多多等人,其他大牌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艾青、食指、北岛、顾城、杨炼等诗人,作品的价值需要在历史的维度上才能确认,单凭文本的说服力,已难服众。而在辨认作品时,附带的历史维度,部分原因是我们基于善意给出的尊重。”又有一位我尊敬的诗人这样说:“1980年底后期至今三十年的当代中国诗歌,其所取得的成就,其在诗歌多个方面拓展、发现的意义,在未来诗歌史的评述中的地位将远超此前七十年的中国诗歌。……他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当下,和一个更加复杂但也更加开阔的未来,背靠一个分类精细、随取随用的传统资源库——他们几乎不可能写出逊色于前辈的诗歌。”(清平:《创作谈》,《草堂》2016年第07月)
我突然想到,新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新文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新诗百年”是一个想象还是事实?对于很多诗人,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他们要做的只是关于“新诗的成就”的想象;而在这个想象中,他们在乎的只是其中的“我们”的成就。
我们很有“成就”,我们根本不知道新诗何时发生……也就罢了,但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可以不知道吗:初期白话诗、新诗和当代汉语诗歌不是从种子到果实、花朵的吗?实质上不是“一”吗?鲜艳的果实会嘲笑种子吗?爱因斯坦会嘲笑牛顿吗?
四、可以不这么急着自我表彰吗
历史中的新诗真的那么简单吗?在美学上可以轻视吗?当代诗真的那么牛到超绝吗?可以无视这个“一”吗?许多当代诗人那种奇怪的未来主义倾向与其说是锐气,不如说是因骄傲而无知。是T.S.艾略特说的那种上了年纪还缺乏“历史意识”的幼稚病。
事实上比谈论“新诗百年”更有意义的事有很多。“百年”,对于一种文学类型的成长与成熟,时间长吗?应该是很短很短吧。想想“近体诗”的成型。那么在百年之中,这种文类的问题与不足当然多于成就,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吧。新诗——现代汉语诗歌的这一种体式,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其诞生、成长至“成熟”,可能还需要时间。
我想我们更应该干点别的,比如:不要满足于“新诗百年成就”的想象。今天就谈论“成就”,未免太自恋。我们要关注百年新诗在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生成之中的诸多问题;别提“成熟”了,这不应该是自我评价,而是历史评价。对于写作而言,对一种文类的历史与文类特征有深刻的了解,何尝不是一件有益之事?
作为研究者,就更应该关注问题,比如“新诗的发生”;比如“新诗的发生”与社会、文化等相关场域之关系;比如“新诗”给当代诗歌写作的遗产;比如近现代历史中的诸多(未被人关注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