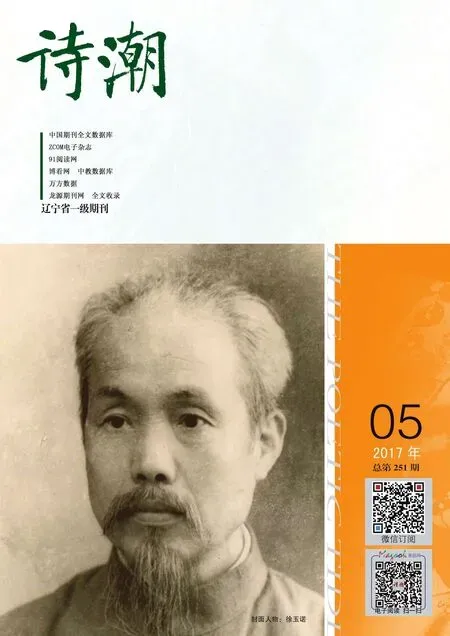雪线[组诗]
荫张翔武
雪线[组诗]
荫张翔武
何处得秋霜
我说,秋夜高空中,会有候鸟飞行,
不知从哪年开始,再也没有听到它们的鸣叫,
或许要怪飞机霸占了它们的航线,
那么我该说,我怀念候鸟迁徙时候的呼唤。
我说,秋夜当有明月转过天空,
抬头却见到耸入云层的高楼,
千万个灯泡哄闹着闯进视线,
我想起天上没有杂质,明月一家独大。
明天早晨,地上肯定敷着一层白霜,
开门以后,草尖只有些许灰尘,
车辆的尾气抢夺了地盘,霜露不敢降落,
我再次改口:我记得霜花碎在鞋底的声音。
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干脆回去乡下?人问。
你不知道,我的乡下也变作你们的城里。我答。
雪线
我这个人,天生有点牛的脾气,
偏爱玩具般的名词、动词,
沙子和雨水不可以混淆,
土地和国家绝不能等同。
我并非一个唯技术主义者,
所以不大使用任何术语;
对于表扬和教训,生来具有抵触的心,
自然,我一直排斥虚词和形容词——
宁可追求夜幕清晰的轮廓,
也不要性格过于柔软,以免头脑稀成糨糊。
这个国度,有思想的人剩下不多,
我尊重他们,但不主动亲近概念。
在暂时居住的城市,
我跟人保持十步的距离。
生活,这个身穿制服的老杂种
常常不请自来,厚起脸皮暗示
我对他应当表示最起码的尊重。
太阳和月亮同时照耀山头,
在山顶,雪线不停延伸,
暖阳随时变成烈日,那又怎样,
清辉也会化作寒气,那又怎样,
一个人专注于赶路,才会发现
只属于他的风景。
愤怒
你得先安顿自己的生活,
他们说了一句,看看我,欲言又止,
神情仿佛在搬运易燃易爆物品,
很明显,话多成仇,避免带来新的刺激。
我清楚他们的好意,从不怀疑
有些建议确实诚恳。当然,
我也从不怀疑自己那么多愤怒
喷发的理由。如今,我偏爱安静,
避开大路,而拣条小路来走。
在台历换掉几本之后,
愤怒,我又想起,这个词
从灰白波浪里飞离大脑,
落地打挺,持续不停,
直到耗光力气,翕动鳃部,
还是不能摆脱困于河滩的处境。
躲雪
女人说,连续三年,昆明
都是这天下雪。她讲下雪——
多数人习惯于这种说法。
安乡人却讲落雪。“下”字
偏于抽象,“落”字暗示还有声响。
我坐在书桌前,打量窗外
两只麻雀站在阳台上,注视
降雪慢慢掩埋地面、道路,
连同它们过冬的食物。
它们站在那儿,
在这个季节的进攻里
像两个平民观望远处的炮火。
电话里说到的地方
挂掉电话,我看看远处,
还会下雨,又没带伞。
城市上空,云群滚来涌去
像缺牙的人在吃软糖。
其他乘客和我一样
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车。
打电话的人说,如果需要
再打电话,我届时赶去那个地方。
雨会再下,电话会再响,
人们在城市深处加快脚步,
雨的逼近糟过天黑的来临,
我等着电话再次响起,
即使冒雨,我也得赶去那个地方。
很多人没有带伞,
很多人会遭到大雨的追击。
站牌上许多地名,其中一个是我要去的地方。
那人说好会来电话。
雨滴在脸上,闪电的灰原来有些冰凉。
灯火纷纷亮起,像河水喷进船舱,
电话始终没响,我想着
那个还没到达的地方。
暴力之盐
抽笔的动作没有发出声响,
每天握笔,写下残篇断句,
仿佛刀手练习挥刀的招式——
找准一个角度,把握一些力度,
调遣词语,去贴住世界的外壳
像膏药温热风湿病人的膝盖;矫正细事,
要有夹板的效果,防止弯曲骨头——
这些说法或许闪现瓷片的缺陷之美,
他只是一名沉迷缝补的工匠,
缝他天生的眉头,补他心里的墙壁。
他老想复原一幅地图,
唯一需要只是母语,
风投周期会是终生。
又或者,他是人形蝙蝠,
一字一句,如同水珠
稀释体内的暴力之盐。
西部小镇
我们坐在车里,等候一辆卡车拐弯,
车上堆着钢筋,它吃力地转动车头,
轮胎陷入浮土,它的关节喀喀直响。
远处,两座白色高炉拔出成片房顶,
倒过来看,像两只胶桶正向海湾
倾倒过剩的牛奶。浓烟虚胖、笨拙,
如外星的沙虫,爬满天空,又跌落。
我有个意大利同行,迪诺·布扎蒂
一次去地铁车站采访,猛然发现,
所谓地狱,恰是人们正过的日子。
尤其夜晚,工业区的烟囱喷出火焰,
大气中太多硫磺味,来往车辆排放的蛊毒
钻入人们的耳朵,开始啃噬疲软的脑髓。
灰尘封住窗台,玻璃具有磨砂效果,
路边房子看似废弃仓库,里面传来一阵笑声。
地平线
屋外大雨,我还要出门。
地平线上走动一些人,
他们扭转头来看我。
雨水闪烁灰白的光,
雨水在闪光以后钻进下水道,
又从堵塞的下水道退回地面,
地面张手抱起一片池塘。
在天上和地面的灰白之间,
地平线的颜色变浅,线条变粗,
一些人走来走去,回头看我,
似乎等待有人加入。
一些人的脸在远处晃动,
好像儿时猫头鹰的瞳孔。
地名
一个电话打来,说
他的出生地已经划归一个小镇。
原来地名从此作废,仅限流通
在老辈人的记忆和话语,等到
他们过世,老地名又后缩,退进
档案、方志和旧地图发黄的纸张。
土地还是那块土地,
之前是乡,再之前是公社,
更早的年头,各省迁来的人们叫它大垸。
经过几个人的商议,
新地名张扬一股塑料气味。
如果每年制作一帧土地的胶片,
慢镜头放映几百年,
增加的是路,跳变的是地名,
地里埋一批人,又生一批人,
地图上没有平民墓地的名称。
楼盘层层推进,仿佛分裂生殖的移动城堡
——土地还是那块土地,
在抵达故乡的傍晚,
游子绝无可能找到祖坟,还有许多人。
昭通西七十九公里
“我的朋友”的朋友丁文江
抚养学生的遗孤,那位地质系高才生
死于土匪出没的昭通境内。
9月初,我下车,站在雾雨中
想起1928年的事,也想起去年
诗人芒原在他家果园里摘下苹果
放进纸箱,然后发货到昆明——
由词语搭建起的友谊
通过一箱苹果物质化于我的手里。
在雾雨中,我跟身边的朋友突然说
很想回家,回到那间满屋是书的房子。
来不及吃完的苹果失去水分,开始皱缩,
冰箱空了,嗡鸣声更大,似乎表达它的饥饿。
大巴再次颤动起来,继续我们的行程,
路边树上挂满的苹果仿佛遗孤的脸
红里透白,具有早熟的沉静。
“人不亲,艺亲;艺不亲,刀把儿亲”,
带我来这里的是词语,也是写诗这门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