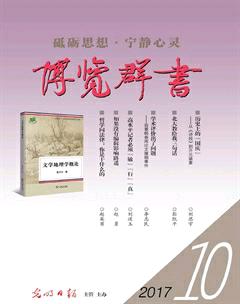如果没有编辑影响路遥
赵勇
我曾写过一篇《遥想当年读路遥》(《博览群书》2015年第5期)的文章,文中说:“我在90年代没读过《平凡的世界》,却读过他那篇绝笔文字——《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但这篇随笔究竟是在哪里读到的,又是何时读到的,现在已忘得精光。”如今,我已找到了答案。让我恢复记忆的是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他在梳理路遥1992年5月的活动情况时指出:“《早晨从中午开始》开始在《女友》第5期连载,至第10期结束。”(P273)读到这里时我眼睛一亮:哈哈,水落石出!当年我在一所地方院校教书,那里的图书馆或中文系资料室就订有《女友》杂志,学生们也喜欢读《女友》,我肯定是在那上面读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记得一边读一边还暗自嘀咕:这篇很严肃的文章怎么发表在这种通俗类的读物上?路遥是要提升这本杂志的文化品位吗?
记忆就这样神奇地复活了。
我从这个细节谈起,是想说明王刚的活儿做得很细。作家年谱我读得不多,但董大中先生的《趙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却是认真读过的。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觉得作家年谱要想写得好,作者的工作不外乎涉及这么几个方面:一、作家的作品读得熟;二、作家的生平创作资料搜集得全;三、善于鉴别和取舍材料;四、要视野开阔,能从大处着眼;五、还要善于微小叙事,让细节说话。这几方面的功课做好了,写出的年谱就既可信,又能有血有肉。
《路遥年谱》就是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的。从1949年(路遥出生)至1992年(路遥去世),作者逐年记录的是两大块内容:其一是文坛大事记,其二自然是路遥的生活、创作情况。而这两者又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呼应关系。例如,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飞船完成有史以来的首次太空飞行,那一年路遥只有12岁。但这一事件将会影响到20年之后的路遥小说创作,因为《人生》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便是来自于加加林。又如,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到延川县插队落户。对于路遥来说,这更是一个重大事件。于是作者特意在此条目下加一长注释,指出知青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路遥生活的文化环境”,“路遥听说他们谁读书多,有见识,就去请教,彻夜长谈。后来证明,与北京知青的交往,对路遥的影响很大”(P67)像这种呼应就很耐人寻味。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而通过作者的梳理,《路遥年谱》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与环境交往互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还有两处地方,我不知道能否构成呼应关系,却也引起了我的兴趣。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而一年多之后,路遥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这两者之间有无一种隐秘的关联?而所谓关联,首先意味着路遥当时是否关注过这场讨论;如果关注过,这场讨论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写作《人生》的触机之一?而恰恰在这里,我们大概不容易找到史料的支撑。其次,《人生》出版并改编成电影后,它所引发的巨大社会效应和相关讨论显然比潘晓来信的讨论更热烈,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生》大讨论是对前者讨论的延续和深化?如果说前者的讨论还显得空洞、抽象和浮泛,后者是不是因为可以聚焦于高加林而更容易使讨论向纵深拓展?
我之所以能关注到这里,是因为我在《路遥年谱》中有关《人生》的记录面前盘桓良久,也对作者引用的相关通信产生了更浓的兴趣。此前我虽已读过厚夫的《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那里对路遥写作《人生》的细节也是浓墨重彩,但我当时并未在意。这一次读《路遥年谱》,一个问题却挥之不去:作家与编辑应该形成何种关系?好的编辑究竟会对作家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本书恰恰在这些方面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机会。
可以先从《人生》谈起。据《路遥年谱》记载,1981年5月,路遥赴京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而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既当过评委,也对路遥的获奖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印象深刻。于是有了王维玲与路遥的长谈,也有了他与路遥的约定。其时,路遥正准备写一部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中篇小说,王维玲便希望他写成后能在中青社出版。
于是有了他们二人的通信。路遥写完初稿后便致信王维玲:“这个中篇是您在北京给我谈后,促我写的,初稿已完,约13万多字,主题、人物都很复杂,我搞得很苦,很吃力,大概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脱稿,我想写完后,直接寄给您给我看看,这并不是要您给我发表,只是想让您给我启示和判断。”(P147)而当王维玲终于读到路遥的稿子并与编辑室的另两位编辑交换过意见后,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其“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又给路遥提出了五点修改建议,涉及小说结尾、巧珍、马栓、加林和德顺爷爷。于是又有了路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客房部修改小说的过程。改稿既成,王维玲很是满意,但为扩大影响,他又主动联系《收获》杂志,让其首发,同时又与路遥商量小说的题目。《人生》原名《生活的乐章》,王维玲觉得不理想,后路遥模仿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改作《你得到了什么?》,王依然觉得不妥。这时候,王维玲“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路遥则答复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P155-P156)正是在王维玲对路遥的催促、鼓励和建议之中,一部时代杰作才横空出世了。
由此看来,编辑在80年代文学生产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以上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王维玲既当着伯乐,也是小说的助产婆和把关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参与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而路遥作为一个出道不久的年轻作家,对于这位资深编辑也是毕恭毕敬,虚心接受其意见和建议。他们因其合作,也共同书写了一段文坛佳话。现在想想,假如没有王维玲,《人生》是不是会在那个时间点上完成,完成之后是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种样子,似乎还很难说。endprint
但众所周知,《平凡的世界》的發表却颇不顺畅。《当代》编辑周昌义第一时间读到了这部长篇的第一部,可是他读不下去:“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P204)结果,这部长篇被他退稿。而王维玲事后好几年才听路遥说过:“假如王维玲来信、来电要稿子,他便要无条件地把《平凡的世界》抽出来给中青社出版。”(P207)这让王维玲感到震撼。现在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这部长篇能被《当代》相中首发于此刊,又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率先推出,那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由此让我意识到的是,失去了熟悉的编辑的呵护,《平凡的世界》的发表与出版就遇到了许多波折。虽然这种波折最终并未对这部小说构成多大影响,但对于路遥本人的心境应该是影响较大的。他能挺住并完成后面两部,显然是凭借其执着的信念支撑下来的。
相比之下,《白鹿原》的面世要顺畅许多,而编辑在其中应该说也厥功至伟。当《白鹿原》历时六年终于写成之后,陈忠实第一个想到的是给他的老朋友、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兼任《当代》杂志副主编)的何启治写信,想请他鉴定成色。何启治则派两位编辑高贤均与洪清波前往陕西取稿。虽然此前《白鹿原》已得到本省评论家李星的高度评价,但陈忠实心里依然不踏实。随后他接到高贤均来信:“这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起来,‘噢唷大叫一声,又跌趴在沙发上。妻子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我缓了半晌才告知这件喜讯。又忍不住细读这封信。……自然,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240-P241)邢小利写《陈忠实传》时想看看此信,但陈忠实却不知放至何处,他便只好借用周昌义的文章,转述高贤均对《白鹿原》的评语——“开天辟地!”(《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180)这是一个高到无法再高的评价,难怪陈忠实会高兴得又吼又叫。
这一例子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作家与编辑之间的关系。陈忠实每写完一个作品,就会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所以,他需要编辑的确认和首肯。但除此之外,路遥发表《平凡的世界》时屡屡遇挫,是不是也让陈忠实产生了某种压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名刊大社的编辑说出来的话就往往一言九鼎、字字千钧了。我不知道今天的编辑是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但读《路遥年谱》,却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编辑之于路遥的重要性。
在“《路遥年谱》研讨会”上,我见到了作者王刚。这是一位出生于1981年、朴实且敦实的陕北汉子。据他讲,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以自己特别的方式向这位同乡前辈致敬”。他在后记中也说:“在写作之初,我就给自己定下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以编著其生平事迹的方式,尝试理解那个文学语境中的路遥、陕北文化中的路遥,以及人世间最平凡的路遥……我期待《路遥年谱》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加丰满、真实、多层面、全角度的路遥。”(P326)要我说,这一目标已经达到了。我在会上还说过:一个作家的传记作品往往会有许多本,但可靠的年谱往往只有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刚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我相信,以后研究路遥的人,手头肯定是要备一本《路遥年谱》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