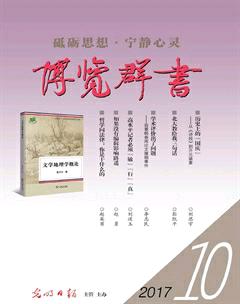终于找到了《小英雄阮友充》
梁东方

收藏之用,有人说在钱,有人说在趣,诚然自有其理;其实,只一个资料之用就已经十分可堪造就了。记得多年以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单位里的美术编辑李老师询问有没有《小英雄阮友充》;她解释说现在上面组织编写一种美术编辑创作汇编,让每个美术编辑都将自己的主要创作扫描一下交上去。而这本《小英雄阮友充》是她去世的前夫——同样是美术编辑的尹庆芳先生——的作品,她家里早就没有了,现在想为亡人寻这点在人间的痕迹,求之无处,找我帮忙。她记得封面上是一个戴着斗笠的越南孩子,旁边有芭蕉叶子。斗笠(或者说应该叫锥形帽)和芭蕉,这是那个时期关于抗美援越的连环画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恍惚中是觉着似曾相识的,就答应下来一定好好找一找。回家在电脑上的目录里搜寻了几遍,没有。隔日带着载有目录的U盘到了单位里,很遗憾地告诉她没有找到。她又提供信息说是河北版,1971年画的,当时画完了以后还因为“不专心革命、走白专道路”、自己“画小人”的罪名而遭到过批评——其实那个时候画连环画连稿费都没有,而作者绘画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坐在小马扎上在膝盖上的小画板上作画……马上打开U盘,进入我的藏品里河北版的目录,一行一行地找下去,竟然真的找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26幅画面,定价5分;我是在这本书出版23年以后的1995年12月10日买的,花了原价的十倍价钱:5毛。
李老师将这本书扫描,以怀念人生中那一段岁月里的甘苦,自是悲喜交加,视若珍宝;藏品不独写就了时代的印记,更有感情的熔铸,像很多艺术品一样,很多连环画藏品后面或许都有可能有一段特殊的故事,那故事联系着创作和时代,联系着生命与呼吸。
连环画画家尹庆芳(1943—1984),1966年毕业于天津美術学院,先后在河北美术出版社印刷厂、河北梆子剧团、河北群艺馆、花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工作过。主要连环画作品除了这第一本《小英雄阮友充》以外,还有《画中人》《武帝雄图》《赶猪记》《心血与鲜花》《称呼问题》等。以他的创作势头,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连环画作品问世的。据李老师讲,她家中还有好几部尹庆芳先生绘画的没有出版的连环画作品。
翻看他的众多作品,可以感受得到,尹庆芳先生的连环画作品笔法精细,细节一丝不苟,不论是芭蕉叶还是爆炸的气浪,都严格遵循着写实的线描原则,不遗余力,精益求精,工笔雕琢。每一幅画面都是非常认真的艺术品,都是他艺术上自我表达的心血之作。这样的创作态度与这样的艺术功力,在经过了时间大潮之后依然熠熠生辉,甚至已经成为今天绘画创作中非常罕见的绝唱。也许只有在那样不计名利,只为表达的人生巅峰状态里,才有可能有那样的贴近艺术之为艺术的原始出发点的创作态度,才能创作出这样不论内容如何,画面却都绝对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艺术品!
《小英雄阮友充》是那个年代里一本很典型的抗美援越连环画,讲述一个父亲被敌人处决的越南孩子如何在敌人的探雷队过去以后抓紧时间再埋地雷、如何偷出敌人的手榴弹扔到敌人头上、如何面对敌人的审问宁死不屈,虽然结果是敌人迫于乡亲们的愤怒而把他放了,但是也一点没有损害他作为一个英雄的存在。仇恨导致的报复心理在一个孩子身上表现得如此剧烈。战争毁灭了死去的人也毁灭了活着的人,毁灭了活着的人应该享有的阳光雨露,让活着的人不得不扭曲着自己进行与侵略者一样不讲人性的抵抗。这本连环画里没有讲到中国人,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不论是编绘者还是阅读者,都是用自己的阶级感情来说话的:我们鲜明地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我们对一方的同情和支持达到了甚至超过对我们自己的国民的情感倾向,至少可以说一切就都跟发生在中国一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接受着战争教育的年轻人,突然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对应物,一再惋惜自己没有置身于火热的战争岁月、没有能参与战斗的年轻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让理想立刻转化为现实的途径!打仗是实现理想的最佳途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参加战斗、就是为了崇高的信念而牺牲!“文革”鼓动起来的狂热气氛中,很多红卫兵以连环画里的人物形象为楷模,以去帮助最具体的“阮友充”“阿福”这样的越南英雄为目标,偷偷越过国境去尽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义务,自发地直接去越南参战;一心去做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去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比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更身处苦难,连吃饭这样最最基本的事情都已经是整个国家的大问题。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则在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强大宣传机器的鼓动下热血沸腾,游行、示威、喊口号、写血书……而所有国内的问题,所有自己祖国的贫困与饥饿也就很自然地被排除在了人们的所思所想之外了。
当然,在时过境迁之后,历史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当年我们竭诚以献的被支持者与当年的侵略者联盟,反而一起将枪口转向了一切都天然地以意识形态和淳朴人性为马首是瞻的我们。这种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翻转,在翻阅着这些连环画的时候实在让人感叹与深思。国家民族之间的援助与个人化的朴素同情之间是不是应该掌握一个合适的分寸,那种纯粹阶级论的全球革命观点下的无私是不是有盲目之嫌?这类问题其实相关的战略研究早已经都有成熟的结论,只是今天在翻看连环画的时候,在再次触及这些代表着情同手足的呐喊的直接文本的时候,我们偶然瞥见了那并不遥远的历史或者说是历史教训而已。
抗美援越的连环画热潮之后曾经出现过对越自卫反击的连环画潮,如果不是连环画这种大众美术媒介的死亡,估计现在又应该有声讨有关国家图谋中国南海岛屿题材的连环画出版潮了。历史上,连环画始终是作为一种文字文本的附属品存在的;所谓原著和绘画,很少甚至是绝对没有是同一个人的现象。充其量是画家有了文字原著以后,带着任务去生活中体验,获得自己的观感以后与原著中的思想进行结合,就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创作了。不能不说,这种创作时候普遍被动性其实也是连环画不能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品种而长存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正是历史上连环画这种一再随波逐流的整体现象,为我们日后通过连环画回看社会留下了一个比较方便的窗口。
连环画作为普及的图文读本,其简单直接的形式后面,正是彼时的社会情势与人民心态最明显的披露。连环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同时还作为一种鼓舞与宣传的工具,作为体现政治意图与民族心理的直接表现物的特征,在这类作品里都是非常明确的。类似的连环画还有很多,如河北版的《阿福》、人美版的《女英雄谢氏娇》《琼虎》等。这些连环画不仅出版品种多而且发行数量大,可谓风行一时、蔚为大观,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是一个气象热闹而气氛严肃的文化现象。“文革”中其他出版物普遍凋零,影视剧也出奇地单调乏味,抗美援越的连环画兴盛一时,既有国际政治话语的强烈影响,也体现出自身文化一旦有了出口和需要,就会生长的自然现象。其留给今天的回忆与反思只是再次应验罢了。
(作者单位:花山文艺出版社) endprint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