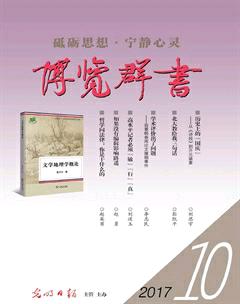新诗的“逆袭”
莫真宝
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后来被称为“新诗”的《白话诗八首》,胡适等以“革命”的姿态登上诗歌舞台,鼓吹“白话诗运动”,试图与旧体诗彻底划清界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极端不一样的形态。新诗这棵“寄生树”,它虽然通过翻译学习西方诗歌形式,但毕竟寄生在汉语这个母体之上,先天性地带有传统诗歌的基因。正因新诗同时具备西方诗歌和传统诗歌基因,也不自觉地影响了与之共时性存在并有所发展的各种旧体诗歌体式。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越来越清晰,正在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着当代旧体诗词的面貌。
首先,新诗语言的白话化对旧体诗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诗,或称自由诗、现代诗、汉诗,而其最初的名称却是“白话诗”,它是伴随着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而出现的。旧体诗虽不乏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骤风疏)等明白如话的作品,但它根植于文言传统,即使明白如话,也依然秉承了文言词法、句法等语法底色。如韦庄《菩萨蛮》有“绿窗人似花”之句,“在场”的“绿窗”与“人”,与“不在场”的喻体“花”并置,“绿窗”作为“人”的状语,但它不借助任何介词、副词或关联词,与现代句法迥异其趣,而且“绿窗”不仅仅是表示处所的状语,同时还暗示了季节和“人”的身份。《平水韵》《词林正韵》等文言时代语音系统的承载物,提供了旧体诗词平仄、押韵的标准。新诗以不讲究行数、字数、押韵、平仄等为显著特色,旧体诗领域内的“词的解放运动”、新古体实验,以及声韵改革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少作者公开呼吁旧体诗词要口语化与白话化,其中固然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而新诗讲求言文一致、自由灵活不受格律拘束的文体特征,无疑成为其最重要的参照对象。
其次,新诗的知性写作,对旧体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旧体诗以 “言志”“缘情”为两大诗学系统,“缘政”则是其共同指向的现实关怀,至于“趣味”“格调”“神韵”“性灵”“肌理”诸说,亦各争一时之胜。整体上看来,旧体诗长于再现,缺乏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思辨性是新诗的重要特征,当代旧体诗也不乏走思辨一路的尝试。如李子把他的“部分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词”称为“人类词”。他有一首《临江仙·童话或者其他》写道:“你在桃花怀孕后,请来燕子伤怀。河流为你不穿鞋。因为你存在,老虎渡河来。//你把皇宫拿去了,改成柏木棺材。你留明月让人猜。因为你存在,我是笨婴孩。”解释词中的“你”,他说:
这里的“你”就是造物主,或者说自然意志。“你”决定了大自然的形态,决定了春去夏来,决定了时间的流驶(桃花、河流句),决定了生物的特性(老虎句)。“你”还决定了人类的历史,设计了人类进化的路线,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你”的设计中,人类需要朝代兴替,需要流血厮杀(皇宫、棺材句)。而面对无所不包、无比强大的自然意志,人类的力量和智慧,有如儿童一样幼稚。
旧体诗词中的这类写法,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当代诗词中,哲思已不只是诗词暗含的、需要发现与研究的部分,而是成为诗词抒写的直接对象。具有深度的理论命题,尤其受到诗人关注。他们在诗词中直接叩问宇宙与生命,叩问神灵与生存,将思考的过程呈现在诗词之中。”
最后,当代旧体诗在艺术手法上向新诗靠拢的迹象也日益鲜明。今天的旧体诗写作,不仅受到传统诗歌的深刻影响,也受到新诗影响,甚至像新诗一样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如李子提出“以物证心”和“整体虚构”的创作观,独孤食肉兽曾在诗集的前言中,称自己所写为“后现代格律诗词”。他力倡“现代城市诗词”,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手法和电影语言,熟练地运用意识流、蒙太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超现实的时空异度的迷宫,如古风《诸客》《后七十二家房客》及《莺啼序·武汉会战》等大量词作,均呈现出相当前卫与先锋的艺术特征。
在写作层面,旧体诗人往往通过隐括新诗或使用新诗典故,或进行新旧体互涉的创作实践。如李子有《虞美人·读海子诗演其义》等篇,直观地表达了取法新诗的尝试。他在解释《风入松》的“河流为你不穿鞋”一句时,就自承取自海子《亚洲铜》诗意。他还引用青蛇出洞在榕树下发表的新诗《在高处的静》中的诗句,解释《忆秦娥》结句“花儿疼痛,日子围观”的涵义。再如独孤食肉兽,曾将自己的新诗《今夕何夕》改为《踏莎行·仲夏夜的湖畔喜剧》。他取法西方诗歌,在《水调歌头·自2015年4月送别1979年3月的特朗斯特罗姆》一词小序中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其“最敬慕的诗人(不分古今中外,没有‘之一)”,独孤食肉兽的词不仅学习其手法,甚至直接化用其比喻之处甚多。他还注重从后现代小说和影视艺术中汲取营养,自称“博粉”(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其词在摒弃议论、回归个体叙事的同时,打上了十分鲜明的后现代色彩。一批披着格律外衣下旧体诗词,有的酷似新诗,如李子《采桑子》:“亡魂撞响回车键,枪眼如坑,字眼如坑,智者从来拒出生。//街头走失新鞋子,灯火之城,人类之城,夜色收容黑眼睛。”有的略为圆融,如独孤食肉兽《河满子·梦后》:“谁在无星之夜,独留未阖之睛。荒墅间呈雷雨里,古帘带落青瓶。一片键光明灭,钢琴自响空厅。//昨日长廊幽邃,重门随过随扃。 若有素衣人秉烛,肃然导我前行。最是百年伤感,觉来无物关情。”这批词作散发出的是与传统词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不唯词如此,气质上更接近于新诗的古体诗,也是如此。如响马的《高丘》《不周山》《康康舞》等。兹将《不周山》分行分节如下:
洪水、地震、瘟疫,
流民褴褛出埃及。
茫茫九州岛坏禹迹。
渺渺三山呼帝力。
星陨,海立,
冰盖溶缩陷北极。
白令辽阔飞鸟溺。
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
深匿于胡底。
不周山静如处女。
纵目,盘膝,白光如荆棘,
挖掘机已去山半壁。
这类“实验体”之作,原皆连排,倘如此分行,其艺术气质,包括语言、节奏,实去“旧体”远而离“新体”近。
新诗走过了漫长的百年历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并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旧体诗的气质与面貌。聂绀弩、蔡世平、刘庆霖、杨逸明、李子、独孤食肉兽、嘘堂、响马、无以为名、杨弃疾、伍锡学等的创作,都呈现出新诗化的倾向,有人称之为“旧体新诗”。然有论者以为,与新诗对接的旧体诗,由于受严格的格律束缚,在思辨深度与艺术高度上均难以超越新诗,而质疑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其实大可不必。新诗“逆袭”旧诗,或者说是舊诗“纡尊降贵”,放下身段,虚心向新诗学习,在造成旧体诗褪变的同时,也为确立新时代旧体诗审美标准与审美风格,使之跻身具有现代品格的“现代诗”之列,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