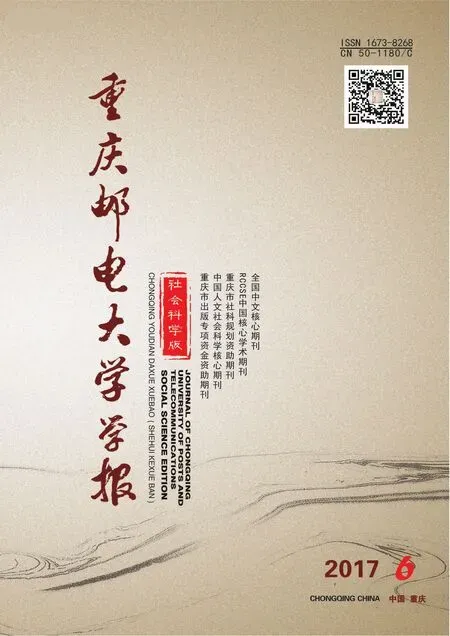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
唐定坤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
唐定坤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卞和献宝”是考察中国文学母题的意蕴生发损益的典型案例,这可以从文史虚实考辨、寓言立意、文学创作的接受阐释、思想史的影响等角度来进行探究。参以史学的考证和文史虚实的分殊,可以见出卞和献宝确有其事,但经过了韩非的“虚饰”加工。正是韩非对卞和事件“以立意为宗”的先秦诸子式的寓言改写,才使之具有了表珍宝良才、怀才不遇、楚音“深情”的悲剧感等文学意蕴,此后文学创作“事类”援用所昭示的接受性阐释大致以此为起点。这一寓言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值得重视,卞和客观而纯粹的“求真”取向颇近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诸子多元时代不乏同类,但随着“儒道互补”思想史格局的形成,则被转入了儒家取向中逐步失落其“求真”品格,这在一定程度表徵了文学母题的价值观念受制于思想史的走向,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主体性和丰富性。
文学发生学;卞和献宝;虚化;“求真”取向;儒化
关于“卞和献宝”,完整的记载首见于《韩非子·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1]34
同书《解老》另有“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1]48的记载,但此处则引为寓言故事,有“文学”加工意味,旨在以之比喻法术之士遇明主而得以施其术的困难。这一事件自韩非起被大量加以运用,而体现为文学功能的不断生发,无论是“和氏玉”的意象化,还是用为故实,都具有丰富的文学意蕴。这是一个中国文学母题递增意蕴的“发生学”典型案例,它作为寓言所包孕的比德品质、人才托寓、悲剧美,乃至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及此取向的转变消失,无不典型展示了中国文学母题内蕴的生发损益。兹加以考论,以求教于方人君子。
一
按韩非敷衍此事,实有迹有循。当本于《荀子·大略》: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2]334
此段王先谦释为:“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而此篇所记又有所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晏子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3]
这两处史料中关于和氏璧的故事并无多大差异。晏子虽早于荀子两百年左右,《晏子春秋》一书作者不可考,不过从书中反映晏子的言行思想尚无战国诸子固定某一家学说的痕迹来看,此书当成于《荀子》同时或之前是不用怀疑的[4]。上引这段话可能是《荀子·大略》的出处,因为除此之外,《荀子·劝学》中尚有:“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2]1也取于此段,可为佐证。另外,尽管《荀子·大略》是荀子的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2]321,但此书整体风格一致,所谓荀子之作,“最为平实”[5],这里并没有对《晏子春秋》中的卞和事件加以敷衍,这无疑增加了此事的真实性;又以荀子曾三次任“稷下学宫”“祭酒”的情况来看,其学问时属“显学”,弟子辑录,尤其是韩非两引此事,也说明了卞和琢玉一事在当时应广为人知。同时代秦国的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孟科季》有:“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6]吕氏编此书颇费心血,悬“一字千金”的美谈,是为求得世人知晓,而取和氏璧与“百金”“道德之至言”分别作比较,这更见出和氏璧的事已广传其时,所以下至汉初便有《淮南子》一书两次引用此事[7]198,655,嗣后更屡见不鲜。
正史的记载和比较,可以为观察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和文学意蕴的生发提供另一视角。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数次提及和氏璧,《鲁仲连邹阳列传》说:“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8]2471此条史实是现存正史中透露卞和献宝事消息的唯一一次,唐人司马贞索隐说:“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见《国语》及《吕氏春秋》。”今本《国语》无卞和事,显然已佚,唐人见到那时的《国语》中记有此事,史家司马迁亦必知道,故《国语》才应是卞和事的最早出处。又《廉颇蔺相如列传》谓“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8]2439,“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8]2440。叙述的重心则转移到和氏璧上。《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九年嫪毐“矫王御玺”,关于此处的“玺”,三家注刘宋裴骃引卫宏之说:“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唐张守节《正义》值得关注,他引崔浩的话说:“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指明此玺乃李斯取和氏璧而磨篆,后代帝王命为“传国玺”则强化了它的政治意义。尔后又引班固《汉书》的记载,并历考“传国玺”入汉以后屡被当权政治人物争夺的命运,至于晋、南朝、隋、唐[8]227-228。这些史实足证此事必为实有。但我们注意到,在正史家这里,焦点集中于和氏璧作为宝物和“传国玺”这一面向,对于卞和献宝一事,只有司马迁语焉不详的提及,嗣后不再受到关注。和氏璧变成“传国玺”,其功能发生巨大转变,被依附上了政治学的意义,具有了等同于“九鼎”般的王朝象征意味。一般而言,新王朝的建立势必要找寻到与前朝的某些承续物事或精神,以确立其政治合法性,从而承续史统而绵延不绝;而史学叙事的一大重要任务便是追求“通古今之变”,在叙述帝王临祚和王朝更迭中努力凸显历史的通识,这使得传统史学家和政治家具有某种共通性,他们关注“传国玺”的深沉意义即在于此。换言之,卞和献宝这一事件,在史学家这里并没有生发多少文学意义,毋宁说史学家因为史学叙事的追求而消解了它本身的文学意蕴。
司马迁引“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符合韩非的记载,却又极简化模糊,或许经过了他取材《国语》和《韩非子》的互校。从文学、史学的分化来看,文学在汉末以下便不断被从经史文章中分离出来,历史学自班固始倡谨严的笔法,渐次规范了史学本身,同时也在抽离掉叙事的想象成分及情感倾向这一过程中判然形成了文史“虚”“实”的分际,所以刘知几《史通》立《言语》《浮词》《叙事》三篇以判文史之别,特警惕于史学家的“枉饰虚言,都捐实事”[9]165和“妄饰”[9]188;但从文学的视阈来看,史实的考述旨归所剥离掉的情感叙事和虚饰夸写,恰恰是文学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参以文学、史学互校而旨归文学的角度,韩非的“文学加工”尤其值得关注。按本文开篇所引韩非《和氏》,很明显较《荀子》和《晏子春秋》作了增写,这主要体现为敷写了事件情节,而变成了论证当下的寓言材料。具体而言,他增添了故事的发生年代、卞和的“楚人”籍贯以及三次献宝的过程;这一叙事坐实于“时”“地”,从表面看是对事实的叙述,但仔细校读,则不难发现此中有“虚饰”成分。首先此为孤证,上引较早或同时期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最多见于“玉人琢和氏璧为国宝”,即便后起的司马迁“卞和献宝,楚王刖之”这一记载出自《国语》佚文,佚文也必然没有韩非所叙那样丰富的情节,不然《晏子春秋》和《荀子》应该多少会露有消息。其次,和氏被刖双足后,“泪尽而继之以血”,不必说手法的夸张和浓郁的情感色彩,看他下边引此故事后以之比较人主用法术之士的议论:“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则有道者之不戮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1]34正是要惊耸帝王起而关注“法术”,很明显有煽情意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卞和先后三次献宝给厉王、武王、文王,历时共百余年,便引来后世非议,《楚世家》记楚称王从武王始,并无厉王其人,王先慎在《韩非子集解》中便认为献宝的先后当为武王、文王、成王[10],尽管可能此处是误写,但至少证明韩非引此事不在考实而在作引论的材料,结合上述内容已可见出;亦或谓“今本之误”,然而此后如《新序》[11]《淮南子》[7]198《琴操》[12]等书所引三位王的说法又各不相同,诚如太田方所言:“《韩子》各有异同矣,《和氏篇》殊甚,每引载辄异。不可枚举。”[13]如果韩非所说属实,那时《国语》佚文尚在,足供诸家参考,何以诸本所说不一?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韩非之前的卞和事件,连并《国语》佚文,记载属实的仅及“井里”、“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最终“良工琢之”而为“和氏璧”,此外的情节都应是韩非通过想象、夸张而“虚饰”的“文学加工”。
Qu ECh ERS法是一种新型果蔬农药多残留前处理方法。该方法是由美国化学家川等人研制,它以一种快速、简便、成本低、高效、安全的分析方法实现高质量分析。
这种“虚饰”加工,就韩非而言本不属 “文学”创作, 其目的不在描述和阐发事件本身,而是以“本近上书”的“奏议”类“书说之体”[14]18来惊起人主,因此是“以立意为宗,不以叙事为主”[15],据“立意”而选取史料进行任意剪裁加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其实也是战国诸子作论说文的普遍策略。如此也造成了此类叙事“引古不必皆虚,设喻自难尽实”,引真实之典实立论,又不囿于事件的细节而任意“虚饰”,在虚实烟雾中乱迷人眼,总归于叙事的渐次虚化。史料演变为寓言故事,“虚化”甚而成为战国诸子引用故实普遍的特点[16]。以卞和事件为例,这是一个由事实渐次虚化的过程,虚化而别生审美意蕴,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夸张和浓郁的情感色彩;这也正是中国文学母题产生审美意蕴的发生学过程,所以冯梦龙说韩非是“小说之祖”[17],而后世蔡邕在《琴操》中又增饰了“乃封和为陵阳侯,卞和辞不就而去”[12]的情节,亦如此类。
二
从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母题的产生足供后人“事类”为用,这是类推思维的“文学推衍”[18]。尤其学术文化的渊薮即诸子原典之言,是后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19]的好材料,所以无论韩非作了怎样的文学想象加工,详尽的情节都会成为后世诗文故实的重要内容,即此种诸子时代的虚饰反而转化为后人笔下真实的故实,这是“卞和献宝”的意蕴生成后被反复运用,复以生成新的文学蕴涵的重要前提。在明辨卞和献宝的虚实叙事之后,从文学创作的语用本位研究来讲,则不再执著于此事的虚化,而是阐发它作为诸子时代定型了的故实所包蕴的丰富内涵,以此才可见出它为后人“事类”所用的文学品格。
“和璧”作为玉本身就具有意象化的文学功能,这与玉文化传统有关。现代考古学已经发现,远在新时器时期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时代,佩玉、葬玉、礼玉等形式便大量存在,尤其是礼仪祭祀沟通天人,玉为必备之物。这点存世资料多可互证,《说文解字》:“灵,巫也,以玉事神。”[20]13巫觋沟通天人必以玉,玉则在使用中渐渐被赋予了通灵的神秘品格。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21]183《周礼》记载“礼玉”有“六瑞”[22]558-559“六器”[22]561-563之说,可见玉文化内容的丰富。而随着“轴心文明”的突破,理性文化兴起,巫觋文化神秘性渐次让位,玉的通灵品质逐渐在使用中被转化为蕴涵高雅的礼仪文化品格,甚而成为人物身份等级的表徵。比如尚存巫风的《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23]29玉在隐含了祭祀的通灵性的同时又有了高贵的礼仪内涵。而《楚辞·九歌·涉江》则有“登昆仑兮食玉央”“被明月兮配宝璐”[23]79的自我抒情,这不难见到作者要力求通过食玉配玉来获得某种高雅而通灵的品质。至于《山海经·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24]《诗·大雅·域朴》颂文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25]则可以看作是以玉来追述圣王大人高雅高贵的品质。另一方面,上述玉使用中的礼仪、仪式以及文化品格,又最终被纳入了先儒周公、孔子礼乐秩序建构之中,这也正是玉文化能够经由儒家产生比德品质的重要原因。《荀子·法行》载孔子之言:“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遐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缀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2]351-352《礼记·聘义》中有孔子“比德”玉与《荀子》记载略同,其后又更进一步将玉的品格提升到“忠”“信”“天”“地”“德”“道”的德行境地,许慎《说文解字》释玉石之美有五德“仁、义、智、勇、絜”[20]10正是依此而出。在这里,儒家祛除了玉在巫觋文化中的神秘通灵性,而通过其形象特征诸如颜色质地、温度触觉、声音形状等,对之作概念性的理智认识而激起了同构的伦理情感,成为了审美的感受或表现对象,使自然感受与伦理情感相交融。更进一步,玉的品格就逐步抽象化,甚而提升到与“忠、信、天、地、德、道”同德的境界。
以上可见,玉作为意象不仅本身具有高贵、高雅的品格内涵,且又比德为抽象化的君子德行。“和氏璧”是玉中极品,相较而言更具有独特性和超拔性,一是喻为兼具品行的良才,如曹植《与杨德祖书》:“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26]卢谌《答刘琨诗》:“不待卞和显,自为命世珍。”[27]中册:883王融《杂体报范通直诗》:“和璧荆山下,隋珠汉水滨,无双自昔代,有美今为邻。”[27]中册:1396二是此璧通过卞和三献的苦心孤诣,最终成为王者之器,甚而演变为“传国玺”的王权象征之宝,附上了具有正当性和纯粹性的至宝财富的内涵,早期“和璧”“隋珠”并举,最见此义,《韩非子》即有:“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之美,物不足以饰之。”[1]48《墨子》亦有:“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28]李斯《谏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8]2543等等。
更进一步,“和氏璧”以姓命名,则在使用中必然指向良玉来历,据韩非所改写,三献宝的过程指向怀珠玉而不为人主识,且最终引发“刖足”悲剧,这就生发了怀才难遇明主、且人之行世每多悲怆情怀的悲剧意蕴。这一丰富的文学蕴涵,足以引发千载共鸣,是后人“事类”以引的绝好素材。首先是卞和终其一身,三献宝遭刖,且宝玉“题之以石”,世人诬贞士为“诳人”,有怀宝不遇明主的辛酸和愤慨,亦隐有对统治者颠倒黑白的尖锐批判,这正是怀才不遇的典型案例。按人类最大的悲剧总在于自我的价值实现与现实世界的彼此悖离和分裂,这是形上的主体自觉性与形下的社会自足性之间的永恒二难命题,使得怀才不遇成为士人永不绝息的主题。对于这一层面而生发的和氏璧“事类”引用,多带有对现实生活的痛感,和怀才不遇的追问乃至批判,不防随举后世诗作中的援“类”证今,以见代有同慨:汉东方朔《七谏》:“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29]晋司马彪《赠山涛诗》:“卞和潜幽冥,谁能证奇璞。”[27]上册:728晋傅玄《拟四愁诗》:“卞和既没玉不察,存若流光忽电灭,何为多念独蕴结?”[27]上册:574唐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践奇璞。”[30]第5册:1821唐李峤《玉》:“徒为卞和识,不遇楚王珍。”[30]第3册:711唐皎然《咏史》:“卞子去不归,何人辨荆玉。”[30]第23册:9241
再次是韩非所改写的悲剧感,这是最能震撼读者之所在。按卞和先后献宝二位君王而遭刖双足,本为悲剧,但韩非的焦点尚不在此,而在彰显“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这一过程,这是人物执著于当下的价值追求,而最终被撕裂、毁灭的性格悲剧,属第一层。更进一步,是要引出“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不是悲自身命运,而是悲宝玉不为人识,悲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念被误解为形而下的庸俗行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中“不可能实现”[31]的必然冲突,由此“毁灭”而凸显出来的执著求真、贞刚品质等“价值”[32]内涵超越了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其“情感形式在显露和参与人生深度上,获得了空间的悲剧性的沉积意义和冲击力量”[33]338。它呈现出来的悲剧美,是在主体实践基于伦理道德品质与对象作强烈的斗争中形成的,其内在冲突的张力表现为不断激荡运动和反形式,具有粗犷、刚健、雄伟的特征,极易震撼读者并引发崇高感,这同时也增加了上述怀才不遇主题的情感内涵,多为后世作者从不同角度“引类”为用。如北周庾信《哀江南赋》“荆山鹊飞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34],以悲愤的故实作点逗。唐薛据《古兴》“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30]第8册:2854,徒伤怀才无奈之痛。徐夤《泪》“已闻抱玉沾衣湿,见说迷途满目流”[30]第21册:8183,最悲涕泪恸痛。李商隐《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30]第16册:6204,则引为反讽。而以下三篇作品则专就卞和献宝的悲剧内涵作阐发,角度不一,可窥一斑:
抱璞岩前桂叶稠,碧溪寒水至今流。空山落日猿声啼,疑是荆人哭未休。
——唐胡曾《荆山》[30]第19册:7419
和楚人,兹楚地;泣玉山,无所记。但见楚人夸产玉,古庙幽幽无鬼哭;倘有鬼,定无足。
——宋梅尧臣《荆山》[35]
——元薛昂夫《中吕·朝天子》[36]
“荆人”“楚地”“荆山”无不指向故事的楚地标识,暗含了作为“楚音”之悲剧感人的地域文化内涵。按《史记·货殖列传》谓楚人“清刻,矜己诺”[8]3267, 《隋书·地理志》说楚地“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37]897,“风气果决”,“视死如归”,“此则其旧风也”[37]886。可见楚人刚悍果决、重情义、重然诺、不计生死的性格特征,其情感则执著深情,“激烈而粗犷”“热烈而粗豪”[33]76。因此作为“楚音”的悲剧,往往体现为以个体血肉之躯来对抗当下和叩寻真理,这真理“不是某种实用性的生活道路,而是‘此在’本身。所以,它充满了极为浓烈的情感哀伤”[33]335,此即楚音“深情”[33]338的悲美内涵,屈原堪为代表,卞和类属之。去先秦不远的史学家班固曾敏锐地指出这一点,《后汉书·班固传》载其上东平王苍的奏记里说:
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听,少屈神威,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38]
班固将之和屈原的悲剧并提,认为它们同是“尘埃之恨”。按卞和三献其宝遭刖双足而不改其志,只为让宝玉的价值得以确认,他“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置生死于外的执著追求,正近似于屈原对国家民族“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深沉情感,二者皆能以血肉之躯叩寻“此在”真理,而具有“浓烈的情感哀伤”。这种类比讨论,使作为楚音“深情”的卞和事件的悲剧意蕴更加深沉动人。
三
楚音的独特动人之处,还在于悲剧美背后的形上意味,即其所呈现出来的主体价值取向与中原文化又有不同。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个体的精神意志对社会实践参与的选择方式。这种选择是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与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互作用和影响,决定了主体对生命本质、形式的终极叩问;落实到社会行为实践中,则更倾向于实现人生的审美理想和体现自我的形上品质。文学实存的母题,它深处的价值取向作为观念形态乃是其文学意蕴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文学审美中它隶属于人文教化功能的核心部分,它的接受阐释更能体现思想史的向度和走向。屈、卞二人都能不计生死,超越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去追求理想纯粹的此在之“真”,在实现自我的实践过程中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要摆脱生命的物质形式,从而获得绝对又崇高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名之曰“求真”取向。这种取向以形下的血肉之躯叩问“此在”之真,可能与楚地大量保存的巫风习俗有关,所谓“楚隔中原,未亲风雅”[14]29,导致了其人情感建构的天真、质朴,当上通先秦巫史文化的独立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屈、卞二人毕竟有着细微差别,屈原的求“真”取向只因其家族的关系而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卞和的终级追求却是使世人识得宝玉的真面目,与现实政治无关,从而更具有客观的“求真”性和纯粹的自由意志,这大致类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考虑到科技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以及众所认同的中国科学主义精神的匮乏,这是最应值得珍视的地方,因此很有必要对它的存在和走向进行分析和梳理。
卞和这种“求真”取向,在先秦时代虽稍不同于屈原甚至其他各诸子,但还不能彰显出其特别价值,只能构成同时代丰富原典思想的一部分。屈原的 “求真”取向主要体现为“美政”的诉求和高蹈人格的自我抒写,连并他神秘的楚地巫祀文化再现,也总指向在对“灵修”肃穆神秘的描写中透露出人格的高蹈卓绝,无论如何,这种“上下而求索”的历程总与“民生多艰”的现实政治干预关联在一起。其实韩非的取向亦大致相同,他虽阐发了卞和献宝的悲剧,但引用此事来讨论君王用法术之士之难,最终也落到了现实政治层面。最为动人的是,他叙卞和之悲,恰似引以为一生之“谶”, 既“知说之难”,又为《说难》而“不能自脱”[8]2148终死于秦,这真是“怀抱一腔热血”[39]的“孤愤”,是执著介入现实不计生死以实现自我理想的价值取向。其实这并非个案,而是“道术为天下裂”[40]的战国时代,诸子学说归趣的普遍特点。张舜徽先生便据《淮南子》鲜明地指出,诸子学说“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41];余英时先生亦指出诸子之争的新局面,都是围绕“礼崩乐坏”后的乱世而重建人间秩序为其目的的,所以称这种“哲学的突破”具有“人间性”的特点。不过,只因源于“以道自任”,诸子普遍都有着“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人格尊严,并强烈地体现在儒家“士志于道”而“求善”的追求中[42]。这导致先秦诸子尽管有着极强的现实干预性,却并不屈服于现实君王政治,而在“从道”的执著上,呈现出了一种主体精神的自由意志,一种主体人格的高蹈卓绝,故亦可谓之“求真”。只是这种“求真”取向在与形下血肉之躯的现实对抗中,尚不如楚地人激烈极端,不如卞和客观纯粹而已。所以我们看韩非引卞和之事并加以改写,并未深入阐发他纯粹而客观的“求真”性这一颇有价值意义的一面,这正彰示了战国时期二者并无太大差别。同时,在焦聚人间现实干预、以重建文明秩序为首要任务的诸子时代,卞和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客观纯粹的“求真”取向,使他不能进入中心话语场,在各种思想甚至极端学说纷呈的大背景下,自然也就不能彰显出其独特性,因此最多只能算是构成多元思想时代中的一元。
卞和献宝“求真”取向的独特价值,要在日后同化进儒学的进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先秦诸子纷争,迟至秦汉,儒家便取得了“正统”待遇,而下至魏晋之际的思想格局重新发生转变,道家因士人转向山林和谈玄而发展成为文人退守和超然于现实的精神家园,此后儒道互补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后来也有诸家学说参与了思想建构,但在价值取向上大致不出儒道两家“进”“退”和“用”“隐”互补的二元格局。卞和事件自然也因与儒家取向的大致类同而最终化入其间,这一转化过程颇能见出其“求真”核质的失落。从理论上讲,原典儒学“士志于道”所强调的“死守善道”[21]81“匹夫不可夺志”[21]93,作为“道统”意志确实能超越生死,但此理论昭示出来的主体自由意志,却必须如神学自由意志一般有赖于“无限的创造力量来实现无限多种多样的美和善并获得纯粹的真”[43]。尤其是孟子强调人格自我的完善乃后天培养,来源于“集义所生”[44]232,当有了“仁”“义”作为行为指导原则,主体便可在“求善”过程中获得一种处世不屈的意志力量和人格气节,甚至是精神上的情感愉悦,从而使得个体在面对或选择死亡时可消减掉其必然产生的恐惧、焦虑等情感压力。在卞和这里,这种力量来源于对既定真理的执著,它无须后天培养便可直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因此我们才说卞和更具有纯粹的“自由意志”,他更原始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人格自我,这也是“求真”价值取向具有彻底的科学主义精神的主要原因。这样,在儒家的卞和接受叙事中,“求真”的向度便无所对应,自然也就转化到了“求善”的各种表徵中,甚至最终失落。考察此后关于卞和献宝逐步儒化的接受叙事,可谓照然若揭。在汉代,儒学有一个逐步取得话语权和发生普遍影响的过程,卞和事件尚且保持了楚风的特征。汉承楚音,“未亲风雅”而浓烈哀伤的楚风北渐,让士人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本末体用之斟酌,因去古未远所以未必明显。如《淮南子》的两次征引卞和事,便没有带上感情评价;又上引史学家同时也是经学家的班固,论屈、卞之事并列为“荆山、汩罗之恨”,叙卞和事件尽管保存了楚风原味,但却与屈原的“忠”相并提,并在言外隐藏了一丝对卞、屈二人执著追求的赞许;到了汉末蔡邕改写这个故事的结尾:“乃封和为陵阳侯。卞和辞不就而去。”可以明显地发现,作为经学家、文学家的蔡邕增写这个辞官不就的结尾,重点是要突显卞和的人格气节。这个过程展示了“求真”取向的逐步转向,此时楚风的悲剧之美并未消失,且儒化的痕迹也不是太重。
三国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典型例子,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言语》引《文士传》云刘桢因甄氏事获罪曹操,罚以磨石,武帝问石如何,对曰:“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45]这里刘桢引石自喻,强调“内含卞氏之珍”, 原文“悲乎宝玉题之以石”的求真“意味”已不甚明显,反倒是禀气坚贞、节操高蹈的“贞士”儒化比德的观念非常明确。尽管旨归于人格气节仍然体现了主体的自由意志,略可上通于原典的“求真取向”,但儒化的痕迹较汉代则很明显。此后对卞和献宝的引用,如本文第二节所引大量例子,大致可以分为两途:一是藉其悲剧美以“事类”为用,这是取“楚音深情”的文学化用,当然也淡化了其价值取向;二是大量用于怀才不遇,正是在这一点上典型体现了卞和事件价值取向的完全儒化。怀才不遇究其质指向贤才合遇君王,按原典儒学论君臣,在于以实现自己的“道”为终极追求,而寄之于一种理想的君臣相遇的关系诉求。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4]136“君使臣以礼,臣视君以忠”[44]66。《孟子》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4]290这其实是以“礼”来衡量一种君臣关系的契约冀求,只是此中尚且保持着“道尊于势”的“道统”原则,再加上春秋战国时代君王尊士的大背景,终能在行为主体上呈现出一种高蹈的人格。但随后在国家大一统的大背景变动下,儒家便为人主所用,这种君臣关系的冀求反而异化成一种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恰如章太炎先生所说,儒家之弊正是在此“干禄致用”中滋生了“富贵利禄”[46]之心,以此逐步消解了“道统”的严肃精神,“求真”的向度便渐次解散,而终无归依。以此观察,对卞和献宝怀才不遇的叙事,在价值导向上正沿续了儒家君臣相遇的情结,而最终演变成了对现实政治人生的执著渴望。这样,行为主体的先天自由意志也就消失了,正是在此过程中较然失落了客观而纯粹的“求真”取向。如果说在怀才不遇的主题抒写中,尚不能见出卞和“求真”取向明显儒化而失其自由意志的向度,那么,我们观察上文引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践奇璞。”这是用于怀才不遇,可是请看他的另一篇《鞠歌行》: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30]第5册:1691
李白竟然明确称呼卞和为“忠臣”,很明显,他是把卞和的所有品质都转化到了儒学君臣关系中去进行阐释的,以自由意志为表征的“求真”品质被描述成为冤鬼“忠臣”的悲剧。到了宋代,每有见解的经学家刘敞在《责璧文》中竟说:
世独谓和为不幸,谬矣。夫谓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谓贞,又非其名。所谓贞者,必审于轻重之分际,荣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此轻,是竖刁之自宫……[47]
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早已判然形成了“儒”“道”对立互补的二元格局,儒学作为思想资源而具有的阐释和限制功能是惊人的,刘敞指责卞和的竟然是不识真正的“轻重”和“荣辱”,不谙保生全身之术,连历来被认可的人格气节也被抽离了。此非孤例,清代尤侗《卞和论》也说:
卞和,古之愚也。夫兰生幽谷,不以无人不芳;玉产深山,不以无工不良,雕之琢之,执之佩之,人之利,非玉之幸也。何以献为?以怀王之昏,虽忠如屈原,尚且被放,况玉人乎!一之为甚,再取辱焉。……和之刖,宜哉![48]
立论的逻辑起点依然是站在政治的维度,而所倡保生全身恰恰又是儒道两家世俗化后的生活智慧。卞和献宝的“求真”取向所呈现出来的主体自由意志、人格高蹈之美,不仅在这二人的叙述中荡然无存,反而被讥为愚笨活该。如果不是还能读到清代沈岐铨反对刘敞《责璧文》而作的《广卞和责璧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赞叹卞和“志之不可夺也”“诚自不可揜也”[49],故能“名不朽”,我们简直要为“求真”取向的儒化和完全失落感到窒息。在这一儒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仅有的最具客观性和纯粹性的科学主义“求真”价值取向火种,被怎样地一步步转化,并最终被纳入儒学的政治视角解读,以及世俗化的生活智慧解读之中。显然,卞和献宝作为文学母题在价值取向这一维度的接受阐释上完全受制于思想史的走向,从而渐次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和丰富性,这与它在韩非的虚化叙事中所赋予的怀才不遇主题、作为“楚音”深情的悲剧内涵,以及后人的“事类”为用,典型地展示了中国文学母题内蕴的生发损益实貌。
[1] 韩非.韩非子[M].阙名,注;顾广圻,识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 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第4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6:143.
[4] 张铮.《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6):122-124.
[5]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2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60.
[6] 吕不韦.吕氏春秋:第6册[M].高诱,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102.
[7] 刘安.淮南鸿烈集解[M].刘文典,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 刘知几.史通评注[M].刘占召,评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0]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86:66.
[11] 刘向.新序全译[M].李华年,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91.
[12] 欧阳询.艺文类聚:下册[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28.
[13] 太田方.韩非子翼毳:上册[M].上海:中西书局,2014:159.
[14] 姚华.弗堂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5]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96.
[16] 徐君辉.先秦诸子著作叙述渐趋虚化的阐释学意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5):123-127.
[17] 冯梦龙.古今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
[18] 易闻晓.诗赋研究的语用本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7- 65.
[19]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14- 615.
[20] 许慎.说文解字: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2] 郑玄.周礼注疏[M].贾公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3]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4] 袁轲.山海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38.
[25] 金启华.诗经全译[M].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84:635.
[26] 曹植.曹植集校注[M].王巍,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390.
[27]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8] 孙诒让.墨子间诂:第4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6:259.
[29] 王逸.楚辞章句[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卷.
[30]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6.
[3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3.
[33] 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4] 庾信.庾子山集注[M].倪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65.
[3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5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946.
[36] 张中月,王钢.全元曲:下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666.
[37]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8]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32.
[39]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87.
[40] 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489.
[41]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204.
[4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34.
[43] 洛斯基.意志自由[M].董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32.
[4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5] 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63.
[46]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话文[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157,125.
[47] 吕祖谦.宋文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2:1761.
[48] 尤侗.西堂全集:第5卷[M].康熙丙寅本:61.
[49] 《湖北文征》出版工作委员会.湖北文征:第7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427.
(编辑:李春英)
BianHePresentsUniqueJadetotheEmperor:ATypicalExampleofLiteraryGenealogy
TANG Dingkun
(CollegeofLiberalArts,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The allusion of “Bian He Presents Unique Jade to the Emperor” is widely used at the present tim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t was an actual occurrence but the story was rewritten and given some literary fantastic phenomena by Han F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nealogy, the critical factor of creating the implication in this allusion is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literary fantastic phenomena which were given by Han Fei.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usic in Chu, the story of underappreciated is to show the feeling of affectionateness. The tragic inherence in the allusion contains the objective and pure orientation to “seek truth”; however,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allusion had finally turned to Confucianism since the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history. This allusion typically show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implication in the motif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genealogy; Bian He Presents Unique Jade to the Emperor; fantastic phenomena; orientation to “seek truth”; confucianization
10.3969/j.issn.1673- 8268.2017.06.017
2016-12- 01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姚华曲学研究(2015JD041)
唐定坤(1978-),男,贵州遵义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6
A
1673- 8268(2017)06- 0120-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