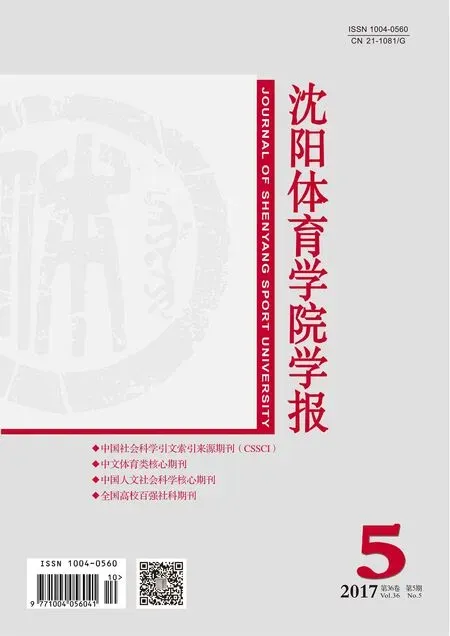武侠电影中武术形象生成的传播符号学阐释
王柏利
(河南理工大学太极拳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武侠电影中武术形象生成的传播符号学阐释
王柏利
(河南理工大学太极拳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武侠电影对武术的世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武侠电影作品中武术文化内涵的匮乏不利于武术形象的塑造。从传播符号学视角,对武侠电影作品中武术文本符号及其传播的意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武侠电影中武术动作的图像表达建构了武术形象符号;武侠电影作品中报仇雪恨、江湖争霸、民族精神弘扬的叙事主题,以及效忠旧主、家族本位的文化表达,为武术形象的生成营造了一个低俗的文化语境,诱发了武术负面形象的产生。而武侠电影作品对民族主义的狭隘恪守,对武术文化的片面解读,导致武侠电影作品文化意义的整体缺失,不利于武术文化的世界传播。赋予武侠电影文本正确的文化意义,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民族文化的正途。
武术;武侠电影;传播符号学;负面形象
在大众传媒掌控社会话语的当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今天的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利用电影传达的图像画面,穿透时间、空间的限制,感悟世界的五彩缤纷,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样式。可以说人们通过电影所虚拟的画面感知了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或者说我们生活在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所建构的文化世界里。在大众媒介的推动下,武侠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纪录,创造了巨额的商业利益,使武术成为世界熟知的文化符号。武术所彰显的浓郁文化特色、形态各异的门派拳种、潇洒飘逸的技术动作、令人眼花缭乱的格斗技术,通过电影屏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人们正是通过武侠电影所建构的武术图像,知晓了武术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建构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武术形象。但无法回避的是,武侠电影在建构武术形象的过程中,“对中国武术‘现实’的误读、曲解,甚至是伤害,更是不容小视的。正是影视武术、武侠小说的这种误读、曲解,才使得大众对武术形象产生认识上的偏差”[1],对当代武术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正确认识武侠电影传播中武术形象存在的问题,分析武侠电影中武术形象的文本意义,揭示其产生负面形象的深层原因,对武术传播发展以及形象重塑有着积极作用。
“形象是一种符号体系,形象的感知必然由符号而获得”[2]。武侠电影中武术形象的生成,与武侠电影中武术动作图像的符号表征及电影文本信息的表达有密切关系。因此,关注武侠电影中武术符号及文本意义,是探究武术形象生成的重要路径。而传播符号学立足于符号传播模式,以媒介符号为研究对象,以意义的指涉和表征为逻辑起点,“强调文本和传播意义的建构”[3],重点关注“意义如何产生与意义如何传达的问题”[4]。从传播符号学理论出发,研究武侠电影的文本内涵及意义表征方式,探讨武侠电影对武术形象的建构路径,对武术传播有重要理论借鉴意义。
1 武侠电影传播中武术技击动作的符号表征
1.1 武侠电影中武术技击动作的图像再现
在中国电影作品中,武术与电影的结合给中国影视界带来了巨大活力。由此形成的武侠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座耀眼的丰碑。以武术为题材的武侠电影作品自问世以来,技击格斗动作就成为武侠电影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是李小龙“真实的打”、成龙“喜剧的打”、李连杰“审美的打”[5],还是电影《狼犬丹尼》中“近乎凶残”的打斗动作、《英雄》中飘逸唯美的动作风格,以及《卧虎藏龙》中芭蕾舞般的武打动作,几乎“每部武侠影片的故事,都是一场以武术对打形式出现的暴力冲突。它既是影片影像特技的呈现高潮,也是影片剧情的叙事高潮,更是一场刀剑技法的演示高潮。这种已经延续了数十年的‘经典本文’,展示了中国武侠电影诱人的动作奇观,构成了武侠影片主要的观赏卖点”[6]39。武侠电影作品甚至突破了国界的限制,成为好莱坞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2000年中国港台资本和创作班子生产的武侠片《卧虎藏龙》,在欧美地区就获得了极大成功。此后,张艺谋拍摄的《英雄》获得了1.7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为第一部在北美市场中战胜好莱坞大片的中国电影。此部电影中精美绝伦的武术格斗动作,使中国华语武侠电影畅销海内外。
不可否认,从军事舞台中走来的武术,基于安身立命的谋生需要,具有了很强的技击格斗特征。关于武术“能打”的传说,几乎伴随其发展的整个过程。武侠电影在迎合大众消费心理的过程中,塑造了无数个武术“能打”的神奇故事,满足着大众对武术暴力的心理需求。尽管武侠电影作品中的武打动作并非现实中的真打实斗,但“能‘打’的中国武术,已经成为人们对中国武术形象构成的第一认知”[1]。由此来看,无论是武侠电影,抑或是备受好莱坞青睐的中国动作片,武打动作始终是武侠电影作品的主要表现形式。武打动作的好坏,甚至成为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核心要素。
然而“中国武侠动作片在好莱坞屡屡得胜,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突发奇想,对东方文化有了兴趣,也不是好莱坞如今对武术独有偏爱。归根到底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源于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市场。中国的武术动作在进入好莱坞主流电影后,能够为它带来可观的市场回报,这才是决定性因素。尽管中国的武侠动作作为当代电影的‘新卖点’在好莱坞已经得到验证,但是,这种所谓的‘国际化’从本土文化的长远利益来讲,也许并不完全意味着中国电影的胜利”[6]96。或者说武术借助电影媒介的传播,扩大了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提高了世界人民对武术的认知度,但并非意味着武术传播取得了胜利。在国内,人们对武术的偏见依然存在,各种与武术相关的负面新闻屡见不鲜;在国外,武术遭遇了人们认知度较高而认同度较低的尴尬境遇。跆拳道、柔道、空手道等项目仍然占据着格斗类消费市场的主要份额,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武术传播的不足之处。其主要原因并非是武术与其他世界格斗类项目的技术差距,而在于武术在传播过程中,一味地张扬武术能打的图像,进而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武术形象的负面认知,影响了人们对武术产品的消费心理。由此可见,单纯依靠武打动作取悦于好莱坞,或者是迎合国内受众娱乐需求的武侠电影作品,不仅会制约武术电影作品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导致武术负面形象的生成。
1.2 武术与“打”传播符码的生成逻辑
事实上,武侠电影作品中单纯的暴力武打动作图像,并非一定会导致武术负面形象的生成。因为电影作品中的世界其他格斗类项目,泰拳以“凶狠”闻名,但似乎依然备受泰国人喜爱;相扑尽管不符合人体健康的需要,但仍得到了日本人的推崇;跆拳道也极力宣传其技击格斗功能,但世界各地遍布跆拳道道馆。这就说明“暴力的技击动作”图像表达并非是负面形象生产的直接原因。由此也引发了对武侠电影传播中武术负面形象生成原因的深层思考。
传播符号学理论指出:“传播离不开符号,符号的意义在传播中生成,其生成和流变的规律,构成了人类意义生产和文化建构的基本法则”[4];“传播必须有意义为前提,没有意义传播行为就不会发生”[3]。美国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曾说:“世界是有意义的”[7]139。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物品、现象,都是自然存在的。当我们在房间中看到一把椅子,会联想到是可以坐的;当在马路上看到红绿灯时,就知道了是汽车停还是走。总之,“意义组织了世界,人类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中。意义是一张地图,存留于人们的头脑中,指导他们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如何处理不同的事情,如何寻找到他们需要的和渴望的东西。这张地图给人们提供意义,也使得这个世界变得容易理解”[7]141。然而,世界中的意义都是被人类文化所赋予并建构的,“意义既是人们在世界中遭遇并发现的东西,同时也是人们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东西,一种对于世界的精神投射”[7]141。所以说武侠电影作品中武打动作的图像表达,其实质是建立了一种武术与“能打”“格斗”之间的意义关系,而这种意义关系的获得,对泰拳、跆拳道,或者是其他格斗类项目来说,效果都是一样的。
换言之,武侠电影作品中武打动作意义的构建,并非一定会产生负面的形象。它仅仅是表达了一系列武术与“能打”之间关系的符码,即索绪尔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能指即为可以被感知道的标记,可以是一段声音或影像,“能指之所以是能指,是因为它必须是某个可识别代码的一部分,这个代码是唯一的,能与其他任何可能的能指相区别”[7]157。但从符号学角度来说,“能指自身并非意义,它唯有和另外一套系统结合方能产生意义。这套系统就是代码或符号的第二个层次——所指”[7]159。武侠电影作品中的武术动作在表现形式上有“劲爆的”“唯美的”“飘逸的”,甚至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美感;在表现特征上则有少林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以及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兵器、暗器等。这些代表武术博大精深的图像符号,体现了符码的唯一性,进而把武侠电影作品中的武打动作与其他格斗类项目进行了区分。至此,武术与“能打”的符码生成了,即“能指”产生了。而武术“所指”符码的生成,则是武术形象意义产生的基础。武侠电影对武术“所指”意义的阐释,决定了人们对武术形象的认知效果,即“所指”意义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效果。因此对“意义”的阐释成为评价武侠电影传播中武术形象如何生成的关键所在。
2 武侠电影中叙事主题的文本表达
乔治·J.E.格雷西亚认为:“一个文本就是一组用作符号的实体,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语境中被作者选择、排列并赋予某种意向,以此向读者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8]16。传播符号学理论认为,文本主要由“构成符号的实体、符号本身、文本意欲传达的特定意义、意向、符号的选择和排列以及语境”[8]17等要素组成。武侠电影中的武打动作元素,构成了武术形象的符号实体。而门派众多的拳种,使复杂的武打动作形成了符号本身。但武侠电影中的文本才是“武术与打”意义产生的载体。也就是说,“一个文本被理解,是因为它的意义是其所指称的东西”[8]35,是“以言表意”借以引起的特定的“以言行事”。武侠电影文本中武术“能打”所指向的特定意义,则赋予了武术形象的内涵。因此,关注武侠电影文本表达的特定意义,是分析武侠电影中武术形象生成的关键。
2.1 武侠电影中“报仇雪恨”的主题表达
“报仇雪恨”是武侠电影作品的重要叙事主题。“为父报仇”“为师报仇”“杀妻之仇”等构成了武侠电影作品叙事的主要线索。如1983年由鲁俊谷导演的《武林圣火令》,讲的就是尹青松夫妇由于得到了武林圣火令而被江湖各门派人士所杀。18年后,其子尹天仇学成绝世神功,最终为父母报仇,杀死了武林中的两个魔头。1982年由张鑫炎执导的《少林寺》,其叙事主题讲述的是“隋唐年间,著名武术家神腿张维持正义被王仁则所杀,其子小虎侥幸逃脱并被少林武僧救出。小虎为报父仇,拜昙宗为师,取名觉远,习武少林,最终杀死了杀父仇人的故事”。1981年张彻导演的《碧血剑》,则以“为父报仇、为妻报仇、为师报仇”的叙事主线,演绎出了一部江湖仇杀的曲折故事。另外,如《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六指琴魔》等武侠电影,仇杀几乎都贯穿于故事情节发展的始终。
曾荣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也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卧虎藏龙》,尽管也反映出主人公想逃离江湖恩怨的愿望,但最终也不得不陷入“为师报仇”的窠臼。正如影片中的主演李慕白所说:“剑惹了无数江湖恩怨”“恩师遭碧眼狐狸暗算,这么多年师仇未报,我就萌生了退出江湖的念头”。“报仇雪恨”的叙事主题,使武侠电影中武术打斗图像与“报仇雪恨”的习武价值联系在一起,进而使武侠电影中的武术符号指向了特定的报仇“意义”,使受众形成“习武为了报仇雪恨”的认知心理。
2.2 武侠电影中“江湖争霸”的价值取向
在诗人眼中,江湖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避难所;在小说家眼中,江湖是打家劫舍的群豪聚义场所;在武侠影视作品中,江湖则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以武功高低为生存基础的虚拟场所。武侠电影自诞生以来,江湖就成为其主要的叙事场所。武侠电影中的江湖人为了争当武林霸主,争夺一部绝世神功的武林秘籍、一把能带来至高武功的神奇兵器,展开了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江湖争斗,使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与尔虞我诈,黑与白、正与邪、真与假、善与恶相互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了无数个豪气万丈、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江湖成为武侠电影作品最为重要的隐喻空间。在武侠电影虚拟的江湖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俱在;武林门派、秘密帮会组织、黑白两道都有。人们可以逍遥自在、我行我素。正如《卧虎藏龙》影片中碧眼狐狸所说的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想拦着我们,就杀他个痛快,这就是江湖,恩恩怨怨、你死我活”。
在江湖中,武功高低成为江湖权利的象征,武术往往成为江湖人争名夺利、江湖争霸的工具。如2001年黄健中导演的《笑傲江湖》中,福威镖局总镖头林镇南深谙江湖之道,认为“江湖上的事,名头占了两成,功夫占了两成,余下的六成,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但因为一部《辟邪剑谱》招来了杀身之祸。而《笑傲江湖》中为了争夺《葵花宝典》,武林盟主,兄弟之间反目成仇,武林中各大门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正亦非正、邪亦非邪,体现出江湖的人心险恶;《倚天屠龙记》中,围绕着能够带来巨大威力的倚天剑、屠龙刀,江湖中引发了无数的争斗;《六指琴魔》中,六大门派为争夺“天魔琴”,演绎了一部相互争斗的故事;《少林与武当》《少林小子》则体现出武林中的门派之见、门派之争;《风云雄霸天下》中为了争当武林霸主,掀起江湖中的血雨腥风。另外《东邪西毒》《侠客行》《天涯明月刀》《萧十一郎》《天下第一剑》《名剑》《踢馆》等武侠电影,对江湖中的名利之争、门派之争刻画的更是入木三分。总之,武侠电影中的武术是江湖争斗的工具,江湖人也把追求高超的功夫、获得武林秘籍作为行走江湖的资本,其习练武术的价值取向直指江湖中的名利之争。正如1993由王晶导演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的头陀,在练成武林绝学九阳神功后找张三丰比武,被打败时仰天长笑说:“想不到我练成九阳神功后还不能天下无敌,我练了又有什么用?”,说完就跳崖自杀了。江湖争霸的文本叙事,使武侠电影中武术打斗符号指向了“名利之争”的“意义”,容易使受众产生“门派之争、江湖争斗”的认知心理。
2.3 武侠电影中弘扬“民族精神”的价值诉求
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清朝的衰落及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面临着亡国、亡种的生存危机。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激发了国民的民族精神。一批武术家如霍元甲、孙禄堂、王子平、蔡龙云等,为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西洋武士进行了擂台决斗。武术作为弘扬民族精神的载体得到重视,孙中山先生亲自题词“尚武精神”。于是,承载着弘扬民族精神重任的武术打擂被演绎成了武侠电影故事,成为吸引众人眼球、满足大众民族主义心理诉求的消费品。如《精武门》讲述了霍元甲的弟子陈真为报杀师之仇,与日本道馆高手较量的故事。最终陈真手刃了仇人,为国家与民族争回了尊严。1972年张彻、鲍学礼执导的《马永贞》,主人公马永贞在擂台上打倒了洋人大力士,以雪国人之耻,声名大噪,但最终也逃不过人在江湖、利字当头、惨遭杀害的宿命。张华勋导演的《武林志》中,武林高手东方旭与一个自称周游四十六国未败一场的俄国大力士达德洛夫打擂比武,演绎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决战,最终在中国武术八卦掌与西洋拳术的较量中,把故事推向了高潮。李连杰先后主演的《黄飞鸿》《精武英雄》和《霍元甲》等电影,尽管在叙事中突出了武学“不打”的修为,淡化了民族主义色彩,但打洋人依然是重要的主题之一。甄子丹主演的《叶问》系列电影作品,又把痛打洋人作为影片赢得票房的亮点。总之,武术与西洋拳法的对决,成为武侠电影作品重要的叙事主题之一。在中国拳师痛打西洋人的过程中,中国武术所展现的民族气节,为观众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提供了出口,自然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在此过程中,武术被赋予了强烈的国家意识,成为一种弘扬民族精神的载体。而武侠电影也无形中把习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精神弘扬联系在了一起。
2.4 武侠电影中恪守传统文化的伦理表达
武侠电影尽管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做出了榜样,但在国际市场中却遭遇了文化认同的抵牾。“中国电影创作中缺乏一种对全人类的共享价值观的自觉把握”[9]49,“中国影视作品文化符号的模糊性与内涵的贫乏以及影视作品的商业化追求与艺术品位追求的严重错位与脱节是造成此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10]。武侠电影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所皈依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一种更高的武术道德、武侠道义和社会伦理相联系”[6]5,使“忠、孝、仁、义、信”等传统伦理构成了武侠电影故事情节演绎的伦理脉络。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效忠旧主”的报国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权的“忠”是规范人行为的传统伦理道德准则。武侠电影往往围绕着对皇权的“忠”展开故事情节的文本叙事。如1992年由李晶执导的《鹿鼎记》中,天地会把“反清复明”作为其存在的宗旨。正如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所说:“青木堂堂主惨死在鳌拜手下,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诛杀鳌拜这个奸贼,同时将满清皇帝和所有的走狗赶出关外,复我大明江山”。1988年李歇甫导演的《断喉剑》中方国毅说:“你只要进了这个门,你活着就是为了闯王活,死也是为了闯王死”。最后方昭为了效忠闯王而自杀身亡,体现了对君王的忠。《龙门客栈》说的是明朝“夺门之变”后义士为搭救忠良之子所展开的一场厮杀。《侠女》反映的是明朝东林党重臣杨涟之女为父复仇的历史故事。《迎春阁之风波》写元朝末年志士刺杀元将李察罕的烈举。《少林与武当》《洪文定三破白莲教》《少林三十六房》《投名状》《新少林五祖》《功夫皇帝方世玉》《清宫大刺杀》《血滴子秘史》《风尘女侠吕四娘》等武侠电影,都是以反清复明为题材,反映了江湖侠客对清朝暴行的反抗。这些电影作品把“侠以武犯禁”的抗暴思想作为叙事主题之一,无形中把习武的意义与效忠“皇权”的观念联系在了一起。
二是家族至上的本位思想。武侠电影作品,尤其是“涉及到武林门派之间相互争雄称霸的影片中,家主时常是整个门派的轴心家长,又是家族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门派不可一世的掌门人。这种同时扮演家庭与社会双重首领的特殊身份,使这类人物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矛盾冲突无法调和的时侯,出面裁决的往往是家长、掌门人,而对家长的态度便为影片中的其他人物提供了一个相斥性的选择,要么顺应、服从,要么反抗、背叛。这两种选择使家长在武侠电影中俨然成为一种判断人物道德归属的界碑”[6]62。1980年由张彻导演的香港电影《少林与武当》,故事情节体现出武当与少林两大门派的争斗,由此发生了两大门派弟子之间的比武。1984年由张鑫炎执导的《少林小子》,更是把少林、武当两大门派之争体现得淋漓尽致。《独臂刀》中的侠客方刚已经隐退江湖,但为了尽孝、完成父亲的遗志重出江湖。2015年由徐浩峰导演的《师父》,讲述了民国时期南派宗师陈识北上开武馆的故事。故事中的收徒、踢馆等场景体现了家族本位的门规和门派之间争斗的江湖规则。这一系列武侠电影,传统的伦理道德贯穿于故事情节的始终,使“师父、掌门人、江湖霸主”拥有了绝对的权威,体现出至高无上的家长地位。而处于不同武术门派中的各色人物,则体现出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家族伦理特征。由此使武侠电影中恪守传统伦理的武术文化形象跃然纸上。
3 武侠电影中武术负面形象的生成逻辑
3.1 武侠电影的叙事结构塑造了打打杀杀的武术形象
叙事就是讲故事,是文本意义表达的主要方式。“叙事是大众媒介中最为普遍的代码,在广告和各种娱乐形式中,它无所不在。对于电影、电视、漫画和大多数流行歌曲来说,叙事结构是最关键的因素”[7]181。“叙事结构就是影片中故事情节展开的顺序: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从哪儿来?未来是什么?人们所遵从的社会关系又是什么”。[7]180-181武侠电影中的叙事结构,往往围绕着叙事主题展开。影片中的“他们”是代表武术符号的各门各派武林人士。而这些武林门派人士来自于江湖,“他们”可以凭借武功“潇洒走江湖”。至于未来“他们”去干什么,电影的主题告诉了答案:他们或报仇雪恨,或打打杀杀,或追逐名利,或张扬本门派武功的高超,或以己之身报效国家。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则为他们社会关系的形成以及社会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武侠电影的叙事结构为武术营造了一个打打杀杀的文化语境,进而形成了受众在现实世界中对武术形象的潜在认知。
于是,人们看武术的打斗动作,就产生了报仇雪恨、打打杀杀的武术形象。如网络中关于武术与报仇的新闻《六旬老人被小伙殴打,苦练8年功夫报仇》《四川筠连男子少年时被打外出习武5年后回乡报仇》《学生在初中时被老师责骂练武术7年后提刀复仇》《男子酒后用少林功夫打人逼对方只穿内裤扎马步》等。有的新闻特意强调了肇事者“之前在少林塔沟武校学过武术,2009年在体育学院参加过比赛,到现在还在武术教练馆里教人家武术、格斗技巧”[11],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武术形象的真实反映。
3.2 江湖争霸的叙事主题刻画了门派之争的武术形象
“门派之争、江湖乱斗”一直是阻碍武术健康发展的陋习。在武术传播的过程中,“门派间相互勾心斗角、相互贬低,习武者拉帮结派、自我炫耀正宗的江湖陋习一直无法根除。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武林门派之间的争斗、对武林正宗的追逐依然存在”[12],极大地影响了武术正面形象的塑造。然而在武侠电影中,江湖争霸的意义表达直指武术门派之间的名利之争,这不仅影响着武术正面形象的塑造,同时也容易使门派之争的观念映射在现实生活中。如在当今社会中,“某氏太极拳”“某派武术”“某某拳”成为当今武术传播的一个怪相,这些所谓的“新的武术门派和拳种不断涌现,这种逆流出现的异化现象对武术发展来说实在是有害而无益”[13]。而门派之间的相互争斗极大地损害了武术形象。如2013年佛山精武体育会会长、叶问第二代弟子梁旭辉,在回复给少林寺的石碑中,只将自己师傅张卓庆的名字留在正统咏春传承表上,剔除了叶问的其他弟子,自称正统。此举遭到了世界咏春联会的强烈反对。在10月9日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世界咏春联会主席、叶问之子叶准,以及叶准首徒、世界咏春联会副主席冼国林直斥梁旭辉有商业目的,甚至发生了“叶问之子开发布会遇砸场”[14]的闹剧。在对河南新乡某个民间武术拳种调研的过程中,曾出现同一门派的师兄弟两人,为争正宗,曾扬言“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现象,反映出武术传播中门派之争的弊端。因此,武侠电影中江湖争霸的叙事主体,赋予了武术的负面形象,不利于武术的世界传播。
3.3 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武术形象的国际传播
武侠电影中讲述中国拳师暴打“洋人”的故事,借以宣泄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达到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但就实际情况来说,“对民族性的刻意强调和执意坚守往往会造成人为的壁垒和接受的障碍,使地球变得不平起来。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要真正走向世界,首要做的就是把民族文化转化为世界文化。事实上,只有真正成为世界的,民族文化才能够被弘扬、被传播”[9]47。正如李连杰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但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一定是坏东西”[15]38。“很多情况下,当我们看到一个在中国受人尊敬、喜爱的演员在外国电影里被人暴打,我们一定会说这部影片在‘辱华’。但反过来想,如果有外国演员在我们拍的影片中被打,那其他国家的人会不会说这是‘辱洋’呢?”[15]39。因此,“越是民族的,并非一定是世界的”。尤其在今天社会中,中国武侠电影所彰显的民族主义色彩是非理性的表达。是过去中国社会长期积弱到今天发展起来的一种亢奋状态。正如卢元镇先生评价竞技体育时所说:“当处在弱国地位时,会出现一种‘擂台心态’,希望在一个擂台上过一把强者的瘾,把政治、经济、文化说不清摆不上桌面的事情做一番推理。清末以来,经常看到作品或新闻中有中国拳师将外国大力士、拳击家打得鼻青脸肿或踢飞下台的痛快场面,其实大多是虚拟的、一厢情愿的”。而当中国进入了奥运大家庭后,当中国以大国姿态展示给世界的时候,如果仍然怀着这种“擂台心态”,则不免会陷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因此,中国武侠电影作品中“暴打洋人”的图像表达,只能成为阻碍武术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不利于武术形象的国际传播。
3.4 低俗的文化语境形塑了武术文化的负面形象
“行侠仗义”是武术文化的典型特征,但武侠电影却为行侠仗义塑造了一个低俗的文化语境。武侠电影中的武打动作往往伴随着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正如符号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组织文本往往围绕着一系列二元对立或者二元代码来完成:黑与白、个人与社会、好和坏、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人、美丽和丑陋、强壮和虚弱、工作和玩耍、自然和文化。在不同的二元对立的概念之间建立某种等值的关系,并赋予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特权,这样的代码就形成了意义的结构”[7]195。武侠电影中的武术暴力在“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文化符号掩饰下,给武术暴力行为披上了正义性与合理性的外衣。然而,武侠电影中的侠义行为往往体现出“侠以武犯禁”的抗暴思想。侠客们“反清复明”“效忠旧主”的叙事故事,大多围绕着“清朝对汉族的暴政统治”而展开,这样的叙事主题一方面容易激化民族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当代民族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容易把武术作为反抗社会不公的暴力工具,不利于武术文化正能量传播。并且武侠电影中对已亡王朝留恋的叙事故事,体现的恰是江湖侠士效忠于王朝皇权的愚昧报国思想。
“尊师重道”是武术文化礼仪道德的重要体现。但武侠电影却赋予了尊师重道狭隘的文化内涵。武侠电影把传统社会所形成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的观念,演变成对师父的“孝、忠”和对门派、师门的盲目遵从,体现了典型的家族本位思想。传统武术中的“门、派、户、姓氏”等观念,“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制度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它体现的是对师父个人、家族、某一个群体的强烈认同,张扬的是对族权、王权的‘王朝国家’形态下的认同,不仅容易造成武术内部‘门派之争’‘门户之见’等武术传统陋习,也不利于当前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16]。武侠电影对传统伦理的狭隘恪守,武术文化意义的整体缺失,加剧了武术负面形象的形成,最终给武术传播带来了不利影响。
4 结语
武侠电影的确为武术的世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武侠电影作品文化底蕴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根本问题所在。“电影剧本的故事苍白、情节平淡、精神内涵空洞、文化功底薄弱等致命伤已逐渐显露,它成为只不过是一个过目即忘的视觉盛宴而已”[17]49。武侠电影已经成为受众娱乐消费时“用过即扔”的低俗产品。以武术为主要叙事文本的武侠电影,对武术文本意义表达的曲解,加剧了武术负面形象的形成,这不仅制约着武术的世界传播,同时也影响着大众对武术的消费认知心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武侠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输出载体,应该承担起传承武术文化的重任。在向世界传播武术文化的过程中,自觉规避武术负面形象的影响,塑造良好的武术文化形象。惟其如此,武侠电影才能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完成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
[1]李源,王岗,朱瑞琪.中国武术负面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反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9):33-40.
[2]胡易容.符号学方法与普适形象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9-26.
[3]冯月季.传播符号学及其理论建构[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58-62.
[4]李思屈,刘研.论传播符号学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8):29-37.
[5]戴国斌.不同历史时期武术影视明星发展特征研究——以李小龙、成龙、李连杰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6):37-40.
[6]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39-79.
[7]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M].祁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9-195.
[8]乔治·J.E.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M].汪信砚,李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5.
[9]高力.电影批判的七张面孔[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49.
[10]刁生虎,郭岚宁.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与传播符号学[J].高校社科动态,2016(2):1-5.
[11]腾讯视频.男子酒后用少林功夫打人逼对方只穿内裤扎马步[EB/OL].http://js.qq.com/pho/?pgv_ref=aio2015&ptlang=2052.2016-11-23.
[12]王柏利.中国武术传播中越轨行为的社会学诠释[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38-43.
[13]王晓东,郭春阳.从分化到异化:对武术门派产生和发展的理性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6):503.
[14]彭博.“叶问之子开发布会遇”“砸场“咏春正统之争起风波”[N].南方日报,2013-10-10(2).
[15]张海.电影江湖的真功夫[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38.
[16]王纯,王柏利.国家文化建设中武术文化认同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4):63-67.
[17]明安香.传媒全球化与中国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76.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Wushu Images in Swordsman Movies
WANG Baili
(School of Tai Chi,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Henan,China)
Swordsmanmovies have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pread of Wushu,but the lack of Wushu in Swordsman film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haping of Wushu imag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significance ofWushu text symbols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in Swordsman film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age of Swordsman film expresses the constructed image symbol of Wushu;swordsman film,arena hegemony,paying off old scores of national spirits and the narrative theme,allegiance to the oldmaster and fam ily ethical cultural expression create a vulgar cultural context to generate the image produced by Wushu.However,the narrow attention of Swordsman films to nationalism and the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Wushu culture lead to the overall absence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wordsman films,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pread ofWushu Culture in the world.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wordsmanmovies,is to tell a good story and a sound way to spread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Wushu;swordsman movies;Sem iotics of communication;negative image
G852
A
1004-0560(2017)05-0138-07
2017-04-27;
2017-05-24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016-ZD-090)。
王柏利(1979—),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社会学。
责任编辑:郭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