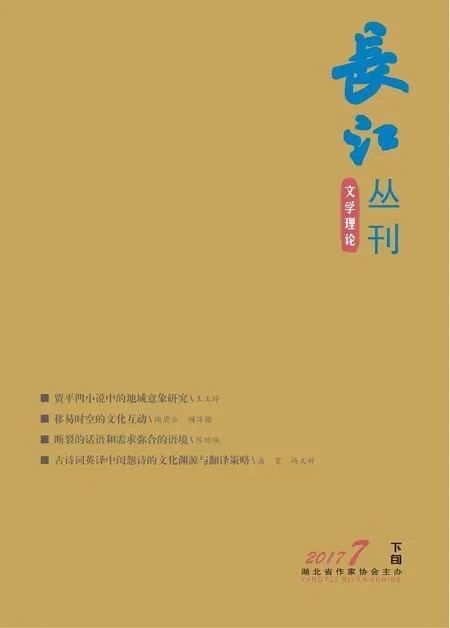农村集体财产分配中的司法救济制度研究
——基于行政法的视角
李雨书 邢 磊
农村集体财产分配中的司法救济制度研究
——基于行政法的视角
李雨书 邢 磊
农村集体财产分配是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极为重视的部分,本该由村民进行民主决策来决定集体财产的分配,但当下更多的是村委会在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擅自处理集体财产,直接了侵害村民合法权益,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初衷。法院一般把此类纠纷归入民事案件处理,然而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民事诉讼救济无法给予村民有效的权益保护,其救济途径混乱。本文在分析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现状的基础上,对保护村民权益的司法救济制度,从行政法的视角进行一个初探。
集体财产 村委会 村民权益 司法救济
一、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中规定村内重大事务应当由村民会议通过决议由村委会执行,尤其是集体财产的分配,涉及每一个村民的利益,村委会无权擅自决定其分配。然而现实中仍有部分村委会通常不通过村民会议而擅自决定村内重大事务,剥夺了村民对集体财产进行分配的民主决策权利,严重损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与建立村民自治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只能由村委会召集的制度背景下,村民通过内部民主决策程序约束村委会集体财产管理权的预期自然落空,外部的司法救济成为村民保护集体财产权益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1]但事实上,司法救济制度的不完善无法给予村民一个有效的权益保护,诉讼费用过高,大多数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等因素,作为正式救济途径的司法救济很少被村民选择,而是更多的选择其他的救济途径,最后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现状及司法救济制度建立的意义,以及当前司法救济制度的困境进行研究分析,最后尝试提出完善司法救济制度的对策,以便有效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现状及司法救济制度建立的意义
当前村民集体财产分配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时有发生,《村组法》中规定村内事务属于村民自治事项,由村委会进行决定管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委会借着此条例而排斥国家和法律的监督。本文就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现状以及司法救济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进行探究,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一)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的现状
《村组法》第八条规定村委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村委会依法可对集体财产进行管理,在处置集体财产方面可分为对内分配集体财产和对外处置集体财产两个方面,《村组法》第24条及第28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以及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要通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处理。然而在现实中,村委会不经过村民会议讨论而擅自决定集体财产的处置此类现象层出不穷,村委会私吞集体财产或擅自决定对内集体财产分配方案,村委会违反内部决策程序擅自对外签订集体财产处置合同等现象日益成为村民自治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此类现象更是频繁出现。从近几年的各类集体财产纠纷案件中可以看出,农村集体财产分配已经成为村民自治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建立农村集体财产分配司法救济制度的意义
鉴于上述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现状的阐述,村民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选择正式救济途径或是非正式救济途径?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的纠纷中,村民之所以会选择非正式渠道而没有选择法律救济的正式渠道,正是由于我国目前在解决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纠纷上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村民从司法救济途径中无法保护自身的权益,所以建立有效的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是保护村民在集体财产分配上的合法权益的首要任务和必要途径,对于促进村民自治的实施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当前农村集体财产分配中司法救济制度的运行困境
村委会擅自处置集体财产损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司法救济作为正规的救济渠道应给予村民有效的权益保护。我国的法律在司法救济方面虽然有出台相关的规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由于存在各方面的漏洞,导致村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司法救济制度相当于一纸空谈,致使村民更多的选择了非正式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无明确法律规定其具体诉讼途径
司法实践中,法院常以“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由,认为村委会不是行政诉讼的合格被告,从而拒绝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2]这就造成了村民起诉村委会时,法院以村民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范围为由驳回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又以村委会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为由不予立案,形成了诉讼的盲区。我国法律在集体财产分配方面的司法救济中具体诉讼途径无明确规定,这导致了村民在民事诉讼途径中无法得到根本上的权益保护,也不能从行政诉讼途径中得到维护。
(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无明确法律依据
由于责任界定以及追责机制的不完善,致使大量集体财产纠纷案中村民合法的财产权益救济举步维艰。村委会擅自处置集体财产造成了损失,而村民的利益诉求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应该追究村委会成员私法责任还是公法责任,法院无法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如若按私法进行审判,由于村民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法院无法强制判决村委会做出决定,按照规定其成员的赔偿责任无论损失大小都要承担经济赔偿,对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造成了严重打击。从公法上来说,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公务人员或者授权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追偿中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责任。村委会并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其成员也不应属于国家公务人员,再者村委会成员的补贴和收入决定了其较低的赔偿能力。当下我国法律并没有一个合适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不包含对内部公务人员的赔偿诉讼,村委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及其大小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依据,致使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时无从下手。
(三)诉讼费用过高,潜在收益低
针对村委会擅自处分村集体财产的行为,村民若是选择通过诉讼救济途经,则需要承担一系列的诉讼成本。首先,从原告一方来看,除了案件受理费之外,还包括案件申请费、聘请律师的开支、交通费等显性诉讼开支,此外还包括因参加诉讼而产生的其他误工、精力等隐性支出,[3]并且民事诉讼途径的案件受理费用过高。根据民事诉讼案件规定,集体财产纠纷案往往被归为财产案件,村民需交纳巨额的诉讼费用。《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然而对于村委会在未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擅自处置集体财产的事实,村民要证明村委会没有进行民主决策程序而擅自处置集体财产这一事实是相当困难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其次,从被告一方村委会来看,村委会参加司法活动的开支,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以及由于应诉而导致村委会对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精力、品质的减弱等隐性成本,这些最终都要由整个村集体成员来承担。在目前的司法救济制度中,欠缺相应的辅助性配置和激励机制,村民如果直接提起诉讼,可能无力承担的诉讼成本,村民的潜在收益低,也就导致了村民诉讼积极性不高,司法救济制度空置。
四、完善农村集体财产分配中司法救济制度的对策
司法救济制度在农村集体财产分配纠纷中是正式救济渠道,应该成为村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首要选择途径。但由于司法救济制度存在着种种问题,导致村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司法救济成了摆设。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不断优化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引导村民自治纠纷的解决渠道走向正式化、制度化、法制化。
(一)明确诉讼途径,将其纳入行政诉讼体系
由于在法律上对村委会在诉讼中的被告资格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才出现了发生集体纠纷案时,法院更多的是将其当成民事案件处理,要明确农村集体纠纷案的具体诉讼途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村委会主体地位的问题。有学者以村委会行使职权缺乏国家要素,而否定村委会行使职权的行政权利属性。村委会虽然是基层自治组织,但是其管理权利是《村组法》赋予的,村委会也是依据此法和基层政府的权利行为设立的,其设立、合并、变更都要征求基层政府的同意或批准。再者从行政权的本质来看,是一种公权力,乃为权利而设,村委会行使对集体财产的管理、处分等行政权力,恰是以护卫村民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为存在基础与目的。[1]所以村委会应该归为行政主体,是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最后行政诉讼对原告资格的要求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标准低于民事诉讼中的“直接利害关系”标准。由于每个村民对村集体财产享有潜在的财产份额分配利益,因而每个村民均可以自己的名义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无论是从村委会的主体地位还是村民的原告资格方面,都显示了将其纳入行政诉讼体系更利于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村民可以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寻找到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法院也可明确诉讼案件性质,以维护村民最大利益,是最佳的诉讼途径。
(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和内部追偿机制
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出台相关规定来界定如何追究村委会的责任,由谁来追究责任,责任追究又该如何落实;当集体财产因此遭受损失时,其追偿机制又应该是如何界定的。即使法院判决村民胜诉,法院却没有依据对村委会擅自处置集体财产的行为判决承担何种责任,也就意味着村委会的违法行为是零成本的。同时按照现行制度,此类诉讼费用最终需要通过集体财产来进行支付,归根结底会对包括起诉村民在内的每个村民的财产利益带来不利影响,这会对村民选择提起诉讼产生抑制作用。鉴于此,必须建立起责任追究机制和内部追偿机制,可参照《国家赔偿法》有关于对公务员追偿制度的规定,在村委会败诉并支付上诉费用之后,其责任由集体财产处分行为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村委会成员承担,减轻甚至是消除诉讼活动可能对村集体成员的不利影响。
(三)建立诉讼激励机制,适当降低诉讼费用
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村民起诉村委会并不是百分百的胜诉率,潜在风险大,潜在收益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村民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的积极性。当法院将此类案件归入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则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第13条规定法院将只收取每件案件的受理费用50元,与民事诉讼的受理费用相比,村民的诉讼成本大大降低。再者,可规定在村民提起诉讼时仍然需要预交案件受理费,在村民败诉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免去案件受理费,这样可以减轻村民的负担。[3]最后,可设立奖励措施,村民选择司法救济渠道时,都可适当的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建立诉讼激励机制,适当降低诉讼费用是必要的,是鼓励村民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的有效措施。
五、结语
村民自治实践是我国农村治理中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自实施以来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大大推进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是从集体财产分配方面进行一个阐述,针对村委会擅自处置集体财产,侵害村民合法权益,作为维护村民权益的正规渠道即司法救济仍存在的困境,致使村民在集体财产分配上的权益受到侵害无法从正式渠道得到及时救济,就有可能选择非正式渠道去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针对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并希望能够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以保障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的权益。
[1]王琳.农村集体财产处分行为的司法救济路径选择[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3,34(4):35~36.
[2]胡水,赵文明.首例村委会作为行政被告案“流产”[N].法制日报,2003-6-15(1).
[3]张旭勇.村民民主决策权的司法救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26~227,238.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雨书(1994-),女,壮族,湖南宁远人,硕士在读;邢磊(1991-),男,汉族,山西忻州人,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