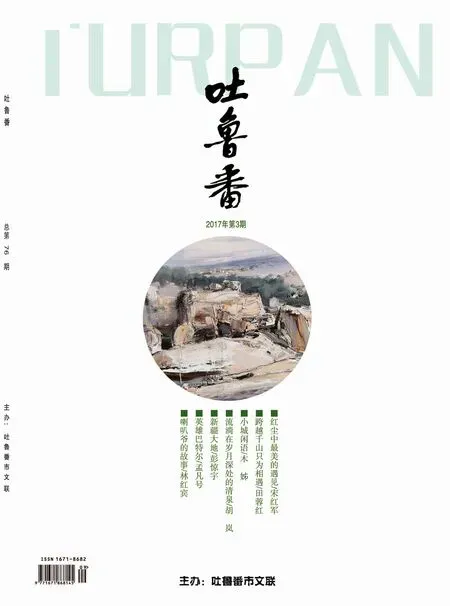桐花凉
■寒郁
桐花凉
■寒郁
1
她出生后,掐了八字,说是缺木,上过几年私塾的爷爷翻了半天旧书,不得要领,倦眼推书时看到院中的老梧桐树,其时正花开勃勃,风吹来,满枝头铃铛状的梧桐花挤挤挨挨撞在一起,叮叮当当的,都是摇曳的香气,爷爷临时起意,我孙女就叫“欣桐”了!——名字里有木不说,小户人家的女儿,叫个欣桐,有花开,有生机,好养活。
然而,在她生命中第十九个桐花开放的春天,花还是热烈绯然,天也在渐渐回暖,可欣桐却感觉一阵阵飘零般的薄寒。黄昏的时候,母亲要她去果园挖些荠菜来。母亲刚才的话还萦绕在她的耳边:
“不是我唠叨,指望着你爹,今年咱家的果子又要烂在果窖里,眼看着辛辛苦苦一年又要白搭,邵老板来咱家饭都没顾上吃,就急急忙忙打电话,几句话下来,人家就给咱联系上车了,欣桐,你想想人家图咱个啥……”
欣桐一听这话,就气了,脸色急转直下,把手里正在择的菜狠狠丢在筐子里:“你说图啥?你不知道吗?有你和我爸这样的吗,不吭不响也没和我商量一声就把人彩礼收了?”因为气愤,欣桐憋出两眼的泪,她的声音很大,“你俩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妈,你想过没?……”
做母亲的一下子怔在那里,不但没有达到劝说的目的,反而被欣桐将住了,索性直接摊开来:“咱家是啥样你还不知道吗?说你一句呢你就能强上十句!我还没说你呢,邵老板一来你就耷拉个脸子,你也不睁开眼看看这方圆几十里家世背景有谁比得邵家,你还想啥……”
欣桐的隐忍的眼泪还是迸了出来,“你开口闭口就是人家的钱势,你咋不看看他是什么货色啊,妈!”欣桐掂了篮子往外走,心头刀剜一样的疼。
到了果园,经过一冬天雪水滋润过的土地,到处是新长出的草芽,野荠菜贴着地面,连成墨绿的一片。欣桐放下篮子,挖了一会儿,想一想方明,就伤心了,眼泪止不住地落,欣桐抬起头看着天上,天上的雁群慢慢飞远了,落日也要下山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欣桐捂住胸口,委屈而难过地喊一声,方明……晚风吹来,夕阳里,欣桐空空荡荡的心底涌起一层薄薄的凄凉。
2
“方明,上来,咱爷俩把这段墙垒了。”老百顺在脚手架上喊底下的方明。叫方明的眉眼炯炯的小伙子答应着,拿工具上来。
“干慢点,干慢点,慢工出细活嘛。”爱偷懒的工友二尕也挤着头凑过来,其实是因为看队长这一会不在,可以放松一会,“方明,来,点一根,解乏。”二尕顺手摸出老百顺上衣兜的好烟,先叼上一根,再借花献佛给方明。
方明也笑着点上。抽烟。干着活。说话。东拉西扯中二尕伸手向公路上打招呼,“咦,你看,那不是邵老板吗,邵老板今儿咋自己开车送楼板,底下人呢,也没个人护驾呀。”
邵千贝也笑骂了一句,把货车靠路边停下,来到工地,撕开烟,一人一根,高低也都是做的这一行,经常碰面。他有楼板厂有起吊机,爹是村里的大队书记,遂没人叫他千娇百宠的名字。“这不是得给方明村西头户老三送的,晚上正好顺路得在老白家喝点,哥几个要有空也去热闹热闹。”
“噢,我说呢邵老板,敢情去老丈人家,那这事不能耽误,得亲自去。”
邵千贝又扔给二尕一棵烟,“扯淡我看你最在行,也看着点儿,别把墙垒歪了。”
“嘻,你问他垒歪的还少嘛。”工友小涛插话,“邵老板,啥时候喝你的喜酒啊。”
邵千贝陡然笑出一脸春色,“不急,不急兄弟,少不了你的。”又依次敷衍了几句,“那行,哥几个先忙着,回见。”
邵千贝掸掸衣服,开车走了。照例把关于他的话题留在身后。
“这狗日的混的,叫一个得意呀,啧啧,白家这叫什么,一把撞上狗屎运了。”二尕不免羡慕嫉妒,酸酸的口气。“白家那个小女儿,叫什么来着,欣桐?对,欣桐,听说长得那个俊呀,你看你,我跟人家方明说话,你瞎反应激动个啥,哈哈……”二尕笑闹着用石子掷了一下还是光棍的小涛的某个部位。
小涛不甘示弱,“哥,还不是因它想嫂子了”。
二尕又说,“方明,还听说上学时欣桐和你有那啥来,真的假的,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艳福还真不浅呐,来过来说说……”
老百顺看他们几个顺竿子往下流的话题上扯,阻止道,“队长来了,干活,赶快干活。”
3
下半夜的月亮清瘦,星光细碎,旁边的河水悄悄流淌着,两岸的开花的梧桐,偶尔掉落一朵殷红。
欣桐把手轻覆在他紧锁的眉心,“我妈收了邵家彩礼了,我和她吵了一架,你说该咋办呢,咱俩……”
方明坐在河沿上,随手带出一个土块砸动水里的月亮。许久,“也不能怪你妈”,就又不说话。
“我哥想进矿上,他那个好吃懒做没主见的死样,一听邵千贝矿上有人,能给他安排个安闲的活,恨不得要我马上就嫁过去”,又说,“恨死我了。”
欣桐她哥那一茬村里小孩多有小儿麻痹症,到现在,还是有一点跛。他哥懦弱,从小玩耍就是人家使唤推搡跟前跟后的小喽啰。
方明并没有叹气,只平淡地说,“到底是矿上来钱,也不怨你哥。”
“我爷爷那事你也知道,看了一辈子山,就因为没火葬,抚恤金年年扣着发不下来……”(公职人员按规定死后必须火葬,才能领到政府抚恤金,但村人仍愿按风俗土葬。)
方明仰面看天上瘦弱明灭的星,兀自苦笑了一下,“这下好了,都凑巧了,还不是人家的一句话。”邵的一个伯父管着县民政局的章。
因他这句话,欣桐抬头看着他,举手打他,是真打,欣桐忽然感觉伤心了。打过了,握着他的手,欣桐想哭,想哭欣桐就哭了。欣桐的眼角慢慢泛起点点凄凄的潮湿,摸着他静默的眉脸,委屈地喊,“方明”、“方明”。
苇间水鸟偶尔受惊于一颗流星,或者几声零星的狗鸣。天地都静。
“方明,你敢不敢带我跑。”欣桐眼睛里忽然闪起小小的火苗,一闪,又一闪的。
他坐在那里,轻轻用手指梳着她的头发,“傻丫头,又不是上学赶上课迟到,能往哪里跑呵。”
欣桐的火苗一点点熄灭了,颓颓地偎着他,不再说话,听他和她心跳的微微时差。
上初中的时候,方明从家到镇子里要沿着河岸步行三公里,就经常会迟到,欣桐本来有漂亮的自行车,但是她不爱骑,她也走路,那因为路上有他。经常走着走着远远地听见校园里急促的铃声,他就拉起她奔跑,有时还是会迟到。有时还会受罚,站在外面,不准进教室。欣桐不忘他牵着她奔跑的感觉,慌张,芬芳,奔跑的惊喜不定和呼吸心急近似于一场小小的冒险游戏。
“反正你不带我跑,我就自己跑,要不我就投河,就是不要嫁给他!”欣桐扑在他怀里,真的哭了,“你不知道他吃喝嫖赌样样不落啊方明……”
他知道。但是他只能抱紧她。
4
邵千贝拍着李义廉肥瘦相宜的左肩,带着度数的右脸靠过去,再拍黄瓜似地狠拍几下,大着舌头说,“李义廉啊李义廉,礼义廉耻你他妈单缺个耻字,你整个就是一个无耻小人,哥们,再喝一个,你承不承认。”
李义廉一副笑眯眯的黄脸黄眼,一边倒酒,一边把住邵千贝东倒西歪的身子,心想你大爷的就你那德行也配给我放这些闲屁,但仍然奉上酒杯,嘴上只是随便调侃一句,“俺哥,要不你还喝羊奶去吧。”
事出有典。上中学的时候,刚一开始要学英语,老师都念不成句,就别说学生了,学一句个个都是用汉字注在下面,这天,英语老师叫起在后面正说得眉飞色舞的邵千贝,让他念念课文,让他打架他擅长,第一句,what’syourname?他吭哧了半天没吭哧上来,旁边大楞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用汉字告诉他,也不知是咋听的,他还特得意的器宇轩昂大声念出——“我吃羊奶不?”爆笑之后,遂成经典。
只此一句,邵千贝哈哈一声大笑,酒水顺势弄洒了李义廉一身,“哎呀,不喝羊奶了,马上要喝俺家欣桐的了。”
李义廉再满斟一杯,转着相书上说主淫亵的黄中带白的眼,“玩腻了,别忘了让兄弟也喝点露水,当年想着她的可不止你一个呐。”
邵千贝顿顿酒杯,“给你!?这是哥哥的自留地,见了面你得叫嫂子。”
“不会吧俺哥,没喝多吧,你要说你玩玩那我还信,你还真打算和她结婚啊,大好年华这要浪费在一个女人身上那多可惜啊,真准备定日子了不成。”
邵千贝故作高深,砸吧着嘴,慢慢吐着烟圈,江山美人势在必得的样子,“老太太老催着抱孙子,不管咋说明年我得让她抱上不是。”咬着烟蒂,“她爹娘早出手摆平了,就是这女人老是拉着一副死脸子,啧啧。”
李义廉啜一口酒,“不会是那个什么方明这小子还和她那啥吧。”
邵千贝听着坐起来,“你不说我倒忘了狗日的这茬子事了,我咋说呢,这样一说就对了”,喝口酒,“嗯,你别说,有可能。”
“要不兄弟找人给你平平,保证不留后遗症。”李义廉顿杯,一扬头,做个凌厉的手势。
邵鼻子里“哼”的一声,猛喝一杯,“这点事,用不着,八万八的彩礼都收下了,嗨,事儿还由得她。”
李叫道,“八万八”,差点惊出嘴里的酒水,并拇指食指翻来覆去大大的比划了几下,“这可是八万八啊,你也真舍得啊,这钱你说我得让底下的妹妹们加班加点的刻苦多长时间呐。”李义廉在城里开着“洗头城”,毋庸多言你也知其内容。
“嘿,兄弟那是你没见,我给你说,就一个字,值!狗日的比上学的时候还正点呐。”
说的李义廉也黄眼放绿光,做了一个猥亵的动作,两人哈哈大笑。
李义廉看看有戏,他今天这顿饭主要是想让邵帮他周旋着弄点私煤生点财路,遂顺承着说:“这样,哥,春夜漫漫呐,这不小弟店里新来了几个鲜货,水嫩嫩啊,没敢用,等着你来检阅呢,咋样,要不走吧。”
“我这快结婚当爹的人了,哪能老跟你们这帮人一起混。”
“得了吧俺哥,趁还没结婚还不赶快争分夺秒快活几天,到时候你能不能拿住白欣桐还是另一说呢。”
邵猛转头,急赤白脸:“你说我拿不下她,我拿趴下她!到时候才得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小彩旗飘飘,”且伴以手势,“走,验验你那些小娘们儿,”一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姿势,“说好了,哥这可是最后一次。”
5
“妈,他都答应了,保卫科,你想整天穿着制服拿着个电棍就这样晃晃,”逢春示范地晃了晃,“多神气,保卫科,还是正式工,妈,你就赶快再劝劝俺妹啊。”逢春两次把“保卫科”三个字念出个抑扬顿挫。
“我劝得还少?”母亲使劲往灶里添了一把柴,或许是柴禾潮湿,几至呛出了母亲的泪,“你没听见天天嚷着还要出去打工,天天和我吵吵,你们几个,唉,哪一个能让我省省心。”
逢春又是那样一副色厉内荏,“出去?她上哪儿去,她哪儿也别给我想去,打工能挣几个小钱,搁着邵老板这现成的……”
母亲捶她仅有的不成器的儿,“祸害哟,你要算是有一点正经样儿我也不舍得你妹妹嫁他邵家,天天就知道东溜西逛,一说你还满不在乎的死样,我哪天死了也省的操这份心。”
逢春退出厨房,一脚把门口的盛水葫芦踢多远,“我不管,我反正不想跟着俺爹天天撅着个腚种这几亩破地了,受够了。”对那弹回的葫芦又跛着腿狠狠补了一脚。
白逢春气哼哼的走出家门。出门不远碰见他爹,也不搭理,楞着头走开。“逢春,该吃饭了你还上哪去?”
“死去。”逢春头也不回。
家里,吃饭前欣桐忽然说,“妈,我跟巧祯姐打过电话了,她那厂里还要人,过几天我想走。”
母亲在围裙上擦筷子,筷子掉了,母亲说,“噢”,许久,又“唉”的叹一声。母亲吞吐了一下,还是说了,“欣桐,妈不是想和你吵,妈知道你看不上邵家的人,但你总得嫁人呐,平心说咱上哪儿能找邵家这么好的人家,从过年提亲到现在你也看到了,人家忙前忙后的给咱家操办这操办那,图个啥,还不就图你一句话,这么重的彩礼都收了,这你让咱咋给人回个话?”
“又不是我收的,一直我答应了吗,”推了一下碗,垂目加重了口气,“好好的你就不能让我安心吃顿饭!”
“你说咱咋能不收,媒人一次次来,说是先缓缓再说,谁知道几封馃子里装的都是钱啊,你问人家,媒人只笑,说不知道这事,都不知道这事,这钱你说咋退?”母亲喘口气,“就咱家这个样,人家不给咱拿架子,找媒人掂着礼一次又一次地跑,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几张老脸,妮子你就不知道这中间的难!”再喘口气,“你非着再学你姐才好,在厂里不吱声谈好了,说一声就嫁过去了,要啥没有啥,这么远遭委屈受罪,做娘的都不知道啊……”做母亲的眼角湿了。掀起围裙擦擦。“连你这不成器的哥,人家都给体体面面安排了工作,我看千贝这孩子是对你一片的心,依我说,咱也不能太不上线了。”
“我不上线?你光知道邵家有势、有钱、咱家有脸面、我哥有工作,可邵千贝吃喝嫖赌你咋不说?”欣桐撒落了筷子。
母亲已经平静的开始夹菜吃饭,“世上的事哪能占个十全,再说,没结婚前男人谁不有点儿浮浪,你看你隔壁二叔以前不也这样,结了婚还不稳稳当当,千贝这孩子我看也不像不听劝的样儿,结了婚,安了心,再劝劝不就好了。况且他看你看的这样重,会不听你的?”
“那是,你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欣桐欲起身回卧房,不想再听。
父亲洗了手从外面进来:
“吃饭。先吃饭。”
6
说也奇怪,不善言谈的他却总是能把她轻轻几句话就惹哭或惹笑,一串笑撞弯了欣桐的腰,或者,转眼间眼睛就下雨了,再把她哄好。当然,后者很少发生。
那时头顶阳光灿烂,心情也正蓝,有那么几次,和他一起因迟到在廊下被老师罚站,听着教室里以及隔壁教室的起哄,他会很窘,欣桐倒淡然。欣桐常想那河沿两边寂静又热烈开放的桐花,是不是也有他们洒落的笑声惊醒的几朵呢?
河水虽然流的仔细、缓慢,但是一转眼,就已不止十年。
然后作为家中老大,初中之后他下学学了木匠,挣了钱帮衬两个弟弟上学。她学习不好,没上高中,一晃眼,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彼时沉默寡言的单薄少年,已经长成身高肩宽结实的男子汉;而欣桐的美好,也是愈来愈鲜艳,惹人垂涎。
下学之后,人时近时远,不常见面,但心在那里。
这天,欣桐也随人看邻家瘦弱的妹妹伴着古老的婚曲,在吹吹打打的唢呐声中,最后被一袭半悲半喜的婚纱裹走了十八年的黄花。
临被新郎抱上租来的花车的最后一项,是乡土风俗里流传的哭嫁,欣桐看着邻家妹妹哭的真真假假,被抱上车了。
欣桐仰起脸,望着院中盛开的梧桐花,捡起一朵,放在手心,久久看着,那小喇叭一样的花朵,似乎在喊着什么……她想,自己嫁人那天,不知道会哭吗,还有,抱她上车的那个人,会是他吗?
7
“爹,我在城里头撞着人了,喂,喂,你说话啊?”
逢春爹丢头愣过神来,握着电话筒,胆战心惊,“乖儿,咋会这样,撞得严重不?”
逢春转眼看看沙发上的邵千贝,再看看李义廉。邵千贝面无表情地抽烟,李义廉黄眼里堆积的是憋不住的笑意,摆手示意继续演下去。逢春一顿脚,叫:“我都给弄到交管所饿半天了,你说严重不?!”
“乖唉,逢春啊你别急,爹这就坐车去城里,你说楞不登的咋会出这事唉。”
“你来,你来顶个屁用啊!你别说了,赶快叫俺妹去找人家邵老板啊,你听见吗?快!要快啊!”
他爹忙不迭地答应,“哎,哎,我这就打电话,这就打电话。”
“叫俺妹打,赶快求人家想想法。你就甭来了,来了我看也没啥用,我得挂了,听见吗,你不要来了,叫俺妹去求求人家!挂了!”
李义廉至此终于憋不住从沙发上滑下来弯腰将积着的笑大口倒出来,“这狗日的可以去演戏了,弄得还真像那回事啊。”
随即,这边邵的手机就响了。“嘘——”,邵千贝抓起手机,“喂。噢,是叔啊,啥事你说——”转向这边装模作样,“李老板我先接个电话,待会咱再谈”,接着那边,“没事,看你说的叔,不耽误,不耽误,有啥事你说。”
“呃,这个,唉……逢春这个不成器的祸害打电话说在城里撞了人了,还被扣在交管所里呢,也不知道咋样了,唉,你说这弄得算啥事这是……”
邵打断,“叔你别急,别急,我这就开车去看看,家里也忙,你就不要来了,我就当是自己的事办,放心叔。”
“你看这,唉,我觍着个老脸,又得给你添乱。”
“叔,你要这样说就外气了不是,那我这就去看看啊,不会有事的,不是还有我嘛……对了,上回给欣桐买的衣裳试了吗,咋样,合身吗?”
“哎,千贝你等一下啊,我叫她给你说话,”那边喊,“欣桐,欣桐,快来,给千贝说说话,你这孩子,你哥还在交警手里呢!”
邵已慢步踱进另一间屋子。迟迟,始传出一声清澈孤立的“喂”,仍然迟迟,没有下文。如石子叩水,邵千贝把手机稍偏离耳旁,斜眼看欣桐这一声“喂”在空气中漾开的波纹。他带着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清冷笑色,等着欣桐接下来怎么说出一些取悦的词汇和柔软的话,他拿着手机,静静等着。我看你这回还能对我骄傲吗?
在父亲的再三急斥催促下,欣桐说话了,“衣裳都合适,我穿了,心里喜欢。”欣桐有细碎的泪不由地在眼里打转,“我哥的事就麻烦你了,有空来我家吃顿饭。”欣桐放下听筒,回到自己卧房,眼泪突然落下。
邵千贝合上手机,骂了一句,眉眼都笑了。走到客厅,回首向李义廉,“先把逢春带你那店里玩几天,过不两天把你弄矿上的事就成了”,走到院子里,问逢春,“你这破车多少钱买的?”
逢春哈腰也踹一脚他破破烂烂的摩托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要了我两千多呢。”
“屁,这样连两百也没人要,”邵千贝抄起地上的建筑钢管照车身上猛砸了几棍,“得专业点儿,好像个撞了的样儿。它还震得手疼!”把钢管丢给逢春,“你来砸,等我结婚的时候给你弄个新的骑骑,那才架势。”
逢春接过钢管,忙答应,“嗯,好嘞。”
黄眼李义廉和邵千贝在一边吸烟说上次煤的事,期间,黄眼瞥一眼一五一十在那儿吭哧吭哧砸摩托车挡板的逢春,“嘁,这憨货。”对邵,“没看出来啊,你还真经雪的萝卜冻了你那花花绿绿的心了啊,还跟真的一样整那么复杂,至于吗?”
邵千贝扬头把手里烟头弹飞,“你没看出来的多着呢,哥不缺个女人,哥要她的心!”
8
河岸边的桐花于不经意间已染红了四月,空气里浮动着醉人的馥郁。这一种朴素的芬芳,萦绕在欣桐的心头,思前想后,都化作了久久弥漫的忧伤。
有一年,同样桐花飘香的晚上,他从沿海的城市做工偶然回家,给她买了一枚心形玉坠子,来不及安顿彼此的牵挂,只看着他唇角的弧形,真真切切地喊她一声欣桐。他的手臂是这么结实、有力,紧紧拥着,踏实了,她双眼忍不住就是一阵落英,但心是这样的欢喜,这时欣桐心底才细细涌起平时念想的凄凉,满心殷红的心事如同满树的桐花,尚不及向他倾泻,在他怀里,一切似乎都停止了,只剩下漫山遍野的香气浓烈……
“我想好了,方明,过两天我就走,再也不回来。”欣桐伏在他肩上,“除了你,这辈子我谁也不嫁他!”仰起头看着他,“方明,你说,你会娶我吗?”
方明一声叹息,“我娶不起你,欣桐。你家里也不会愿意。”
欣桐眼神殷殷,“我不管,我要你说你会,你会。”她眼角渗出细碎的泪。
方明拥着她,“欣桐,我会,我会的!”
欣桐眼睛幽幽,牵起他的手,十指交扣,放在自己心口,“你不会我也不怨你,要你这心就够了。”
他唤一声,“欣桐……”
欣桐含泪笑了,摸他的眼睛,“还说我,你也哭了。”
“方明”,欣桐轻轻喊他,“抱紧我。”
9
户老三大声招呼:“师傅们,下来吃饭了,有酒有肉,吃饱了再干啊。”
“好嘞,这么快晌午了,走,下去吃了饭再干。”二尕最先回应。
工人们于是应声从脚手架上下来洗手洗脸,吃饭。再有一层楼板就封顶了,新屋即将落成,按照惯例,东家要管工人们一顿像样的饭。
邵千贝和东家以及建筑队里几个管事的安排在一桌,工人们也就了座,开始欢庆着粗糙地吃喝。陪工头们喝了几杯,东西闲话了一会,邵千贝拎着好酒,敬了一圈,“哥几个,说点正事,我那楼板厂缺几个人,哪村上有闲着的给兄弟介绍几个能干的。”
二尕接过,“邵老板儿您看我行不?”
“喝酒扯淡你还行”,邵千贝笑,“方明,还出去不?”问方明。
“干完这个月再说吧。家里事多,就怕走不脱。”方明回答。
“就对了嘛,老同学,我那儿一早就缺个能指住的人给我领领,干完这个月,就来吧,亏不了你,只会比你在外面挣得多。”
二尕帮衬,“那是,邵老板一向工钱上,仁义!”倒酒,“方明,你得喝一个!”
“二尕哥,好,别倒多,你知道我不能喝。”方明看逃不脱这杯中物。
盛情难却,怎么说不喝,还是喝了一满杯,方明有些反胃。但是邵千贝又倒了一满杯,众人也只好随上,“方明,先就这样说了,还有点事,哥几个慢慢吃着。”
“嘿嘿,还有事?想去村东头老丈人家就直说是了”,二尕快嘴笑谑点破,“欣桐在家备着好酒,等着你馒头夹肉。”照例一通浪笑。
邵千贝附和一笑,看了一眼方明,随即起身转着敷衍一圈,乘着点酒兴,顺路向东。
“来了,坐,屋里坐,刚说做好饭让欣桐喊你呢。”欣桐爹在固定猪圈栅栏,一见,忙停下手中活计。欣桐娘也从厨房出来招呼,“欣桐她在里屋,先去和她说说话吧,这就好了。”
进了里屋。
欣桐停针,起身,神情不火不温,倒了一杯茶,放在几上,仍坐回床上,针针在枕上绣她的祥云鸳鸯。
“昨儿我见逢春……噢,咱哥,”邵找话说,同时因改口连逢春这样的也得叫哥,不免觉得恶心,“咱哥捎话说在矿上不错,上下都照顾他。”
欣桐深入浅出一针,“嗯。”
但邵并不觉尴尬,“我说你这衣裳穿的有点素了,”见欣桐抬头冷冷看他一眼,忙改口,“素了也好看。”兀自咧嘴补上一笑。
欣桐并不说话。但是邵千贝不转脸直勾着眼看她。他坐在那儿叉开腿,她想出去都得绕过他。他就直眼看着她。
欣桐实在受不住,但只能隔着窗户,“妈,还不该吃饭吗?”
母亲在外面自作主张的响亮应声,“这就好了,再等会儿。”
邵千贝眯眼笑了。喝了一口茶。还看着欣桐,但是走近,“我看绣的啥?”说是看,眼也不在上面,顺势握住欣桐的手,挨近她脸,酒气扑面,“嗯,好看。”再挨近一点,“鸳鸯成双,挺好,结婚时咱枕。”说着就欲上嘴亲吻。
欣桐奋力推他,边躲边闪,却躲不开、闪不迭,强撑着想千万不能倒在床上,在屋里还不能喊骂。太丢人了。万幸的是僵持中邵的手机响了,是催他回西头工地开起吊机,他按灭,红着酒醉的眼,还想再看,但枕巾已被欣桐护在怀里,情急中拿花针扎他手心,却还是被他劈手夺过来,“这就是床上的人了,还这么狠心!”邵居高临下看着举着针满面怒色的欣桐,并轻佻吮吸自己手心的血珠,瞥眼看清两方枕巾,鸳鸯戏水,伴以祥云,名字虽绣得很小、很隐,像她的心,但已针脚分明,一方“欣桐”,一方“方明”。
忽然间极静。
邵千贝并没有发怒。拿着枕巾在欣桐脸前抖动着晃了一遍,又晃了一遍,咬牙,鼻子间出一口气,笑,说,“好”,掷在欣桐脸上,大步回走,“我让你还想着他!”
到院子里,对着满面堆笑迎过来的欣桐爹妈分明放出一句话,“叔,婶,您最后再问问欣桐到底嫁还是不嫁!”扭头走了。
工地上,楼板在地上两头被勾着,然后被起吊机徐徐吊起,升高,起吊杆摆过去,楼顶上有人招呼着,悬空把楼板放在既定的位置,落下,松掉钩子,接着下一块。说让二尕上去接应,二尕说“这我不行,忒高,头晕!”装作真晕的样子,恨得队长笑着踢他,遂队长在楼顶一旁摆手作起落指挥,老百顺和方明在上面一边一个接应,楼板被吊着悬空,稳如一叶之轻,无非是拨动着一块挨着一块的合上缝隙。邵千贝把机器循例开得很耐心、很稳,不急不慢,把地上的楼板一块一块转移到楼顶。
一间屋九块板,三间都封顶了,最后一间也就差几块了。方明瞅了一眼地上仅剩的几块楼板,松了一口气,谢着接过百顺大爷的烟,没有点,想着完事了再下去得喝点水,上午酒喝得现在口渴,头还有点晕呢。
正想着,擦了一把额头的碎汗,方明还抬头看看远处的河边,河边红彤彤的,似乎有云彩在飘,想想才知道那是连片的桐花,再想想曾经和欣桐在河边的时光,就笑了。
忽然间队长大叫,大力摆手,急令邵千贝刹住起吊杆,方明转头一看,呀!——原来稳稳当当下落的楼板,忽然间起吊杆上下颠簸震了一下,楼板还像树叶,开始在链子上来回剧烈地打晃,晃着,一头的钩齿猛然松落,眼看楼板倾斜着砸下来,这时它已不再是树叶,而是结结实实近千斤的钢筋混凝土了……
队长在楼顶嚎叫着奋力摆手……
老百顺从惊疑中愣过神来,恐惧地吆喊,“方明,快躲开!躲开!……”
邵千贝看上去也在手忙脚乱制动刹车杆,出人意料的手忙脚乱……
工人们在脚手架上,地上,闻声张着嘴惊恐地仰望,望着楼板冲向方明……
方明站在楼顶边缘,恍惚间看着楼板像是一缕纱带,或者那一片红云,向着自己轻缓缓地飘来,飘来……
邵走后,欣桐在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猛然间心口感应着一痛,浑身上下一个激灵,迈开步就往村西头奔跑,路两旁盛放的桐花似乎都往后倾倒,她跑啊跑啊,跑的眼泪都出来了,欣桐心里喊他,“方明啊方明……我嫁……”
欣桐一路流着泪奔跑,脖子上的玉坠子跳了出来,寂静而殷红,在心口像火苗一样跳动、闪耀,欣桐流着泪跑啊,跑啊,远远看见,她哭着喊,“我嫁……我嫁还不行吗……我嫁……”
方明刚好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