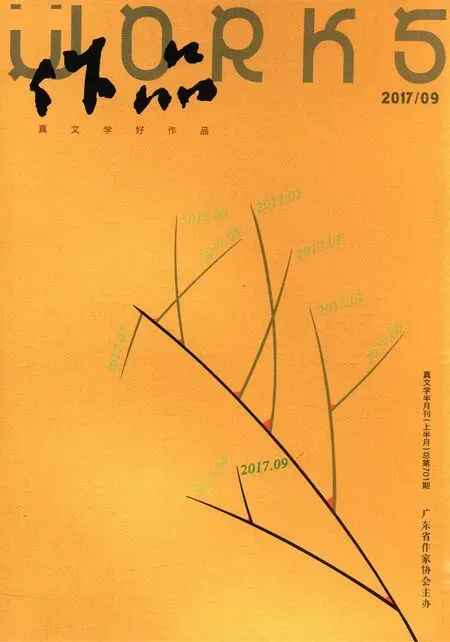花儿锁
文/林渊液
花儿锁
文/林渊液
林渊液
1970年代出生。饮韩江水,说潮汕方言。已出版散文集《有缘来看山》 《无遮无拦的美丽》。作品见刊于《人民文学》 《花城》 《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并入选各种选集和年度选本。曾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五届老舍散文奖,首届林语堂小说奖。
一
那男人永远不会知道,他刚一进门,我的心就为戚美玉活动了一下。他长得高大俊朗。戚美玉的心也活动了一下,之前我误以为她不稀罕各式男子,原来不是。
那时节,戚美玉在案前慵懒地做着活。近午了,室内有些烦闷。初春天气,戚美玉竟有微汗,身子与我紧紧相贴,我贪婪她身上轻淡的肉气。
戚美玉做活很少这么没生气。这是不对的。我应该着急。可是急也没用。她阿姑小惠说过,这活,要用气滋养。
戚美玉做的纱灯是赵子龙,只有八寸高,潮汕歌谣《百屏灯》中说“七八子龙战张郃”,也就是说,这是一百屏纱灯的第七十八屏。泥头、纸胚身子都已完成,这道工序是彩贴。喜兴时,戚美玉的十个指头都可以快速糊贴。经她裁剪的布料,增之一分嫌长,减之一分嫌短。每一贴,留下多少贴位,云肩拼多长流苏,裙子打多少褶裥,水袖如何与衣身对接,那都是有分寸的。她做武生的铠甲,常常是随手抓起一把芥菜子大小的银布片,像抛掷暗器,刷刷刷地就拼贴上去。外人看来,惊叹不已,以为她在变魔术。我是在小惠做活时就看惯了的,论技法,她比不上小惠。当然,她的心比小惠活,不时发出新叶芽。
戚美玉她肯定肚子饿了,可是外卖着实吃腻了。那男人我从未见过,奇怪是,一看他的样子,我就断定他不止可以带戚美玉去海滨路,边观海景边用餐,还可以发生一点什么。
我瞥了一眼他的名片,什么什么工艺精品公司的老总,姓氏被戚美玉的左手拇指遮挡住,只看到名字“文卓”。
这么说来,是做塑料精品的,澄城的塑料业发达,私家的塑料作坊到处都是,但戚美玉入眼的甚少,她经常用塑料来形容那些不堪的人和事,比如,“这人看起来塑料塑料的。”我替他担心了。
做塑料精品的人,找电脑设计公司、找模具行、找树脂行,文卓他找戚美玉的纱灯行做什么?
戚美玉把观海的位置让给那男子,自己坐在背海的一面。我猜,长长的横窗是他面对的一帧名画,画面上,春日的阳光,闪烁的海,海滨路上匆忙的车流,通通都是为了衬托戚美玉。她不年轻,已经四十出头,可是,她看起来娴静而美好,有着单身女人所没有的饱和光泽。上一次清晰看到一个男子眼睛里的爱意,那是什么年代?算来有四十多年了。那爱是给小惠的。但他会把小惠和我一起端详,把小惠和我一起爱。文卓的眼神一直在戚美玉脸上转悠,不瞅我一眼。我有些失望,有些恼火,有些嫉妒。
“是貂蝉罗裙上的那款吗?我把它叫做‘插红萸’,是我手工制作的,做纱灯用,从未给过别人。”
“就是手工作品,才觉稀罕。”
原来是求花边来的。人家叫做花边的,到了纱灯这里,尺来高的人儿,一个花边当得半幅罗裙了。我听他说“手工作品”这几个字,心内乞乞笑个不停,对菜了对菜了。
文卓的朋友开婚纱公司的,新设计的中式系列婚服,看中戚美玉的手工花边“插红萸”。戚美玉的纱灯行做得有些奇崛,前日有个潮剧戏服行的要来定一款珠花,今天又有婚纱行的来定花边。不过,她的手工活都是重工的。戏服行的生意被她推掉了,这婚纱行的活儿她接是不接?
我看着桌上的菜式,咽了咽口水。究其实,不是这菜式的丰盛,而是这餐桌旁氤氲着的一层风月味,美美的,还带一丝酒气。戚美玉啥也没吃,只顾着与文卓说话。说什么来着,怎么说着说着,给他普及起花边的历史了。他做塑料精品的人,还需要学习花边吗?不过,他倒是有做婚纱的朋友。一个朋友亲密到什么程度,需要他来越俎代庖。这个朋友我必须见识一下。插红萸是用绣花加钩针编织的,戚美玉说,丹麦一位研究者写过,最早的钩针编织来自于南美洲的一个原始种族,据说……
“它是用于思春期仪式的装饰品哦。”
这是戚美玉在说话吗?我内心往下一沉。不对了,一切都不对。怎么可能,她对一个相识不到半个时辰的人讲这话,戚美玉真是疯了。要不是我一直跟她一起,定会怀疑她被谁打了催情剂。
文卓入神地听着,眼眸里闪着晶晶的光。现在,我对他充满了敌意。我得提防着,我的戚美玉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伤害。
饭完了,戚美玉也把插红萸的活计应承下来,这下,文卓没有了继续逗留的理由。我寻思着,插红萸制作流程繁复,纯手工制作供应婚服根本不可能。戚美玉倒是有钩针编织机,把设计编程操作起来,后期效率是不错,但上手慢。也就是说,两人如果需要一个合理的见面时间,那还得等。澄城虽然离海阳市不远,不到二十公里的路,可是,看他们不动声色的焦灼,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人远天涯近。
文卓欲言又止,道别之后心事重重。戚美玉把波涛藏在内里,我知道,再回到案前,活儿她根本做不成了,赵子龙不用做,张巡不用做,夏侯渊也不用做了。她还算矜持,把一切藏得好好的,脸上还是平静的微笑,把他送出门口。文卓走了几步,掉转头来,再看了戚美玉一眼。这时候,午后的阳光照在我蓝盈盈的身上,荧光播散开来,他终于看到了我。他对戚美玉大声说:
“你的玉真美!”
戚美玉并没有低头看我,她依然微笑着目送文卓。他像赴难一般,大踏步往前走去,越走越远。
二
对了,我的名字叫做花儿锁,是一枚罕见的蓝水翡翠,据说,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我没觉得自己那么老。我佩着一朵小花,妩媚地在锁眼那里招摇。据说,我是同心锁的一枚,另一枚叫做叶子锁,可我从未见过叶子锁的样子。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世事洞明,有时候又觉得懵懂无知;有时候觉得自己超然剔透,有时候又觉得混沌下沉,玉身犹如肉身。
戚美玉与文卓的进展,是我始料不及的。戚美玉交往过几个男人,不曾有人真正走进过她的生活。她也与他们做爱,但只是做爱而已。我感觉得到,当他们快感来临时,常常是两只青蛙腿一蹬,人就叽里呱啦地叫,然后,趴了。如果之前,戚美玉对他们还是容忍的,到了此时,已恶心无比。那具动物尸体一样的躯壳,被她拎着下了床。我就居住在戚美玉的前胸,我敢保证,她的上半身还是处女之身,连接吻都不曾给。他们中的任一个,于我来说都是面目模糊的,也从未被他们拉碴的胡子扎过。
我不知道,这样的戚美玉,是否与小惠有关。戚美玉还在妙龄时候,每当有男孩子前来找她,小惠总是挡在她的房门口,眼睛像把铁铲一样,看一眼就能把人铲伤。有一个问题我是后来才想到的,小惠把我送给戚美玉,是不是让我随身做一个盯梢。
文卓的身上,是有不同的品质,但我依然难以置信,在他们相识的第八天,他们决定去打结婚证。小惠如果在世,她会同意吗?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不,第三次见面。第二次见面是在……他们第一次分手的三个小时之后。文卓并没有返回澄城,在海滨路兜了几趟来回之后,他重新来到戚美玉的面前。
他们约定了,戚美玉去澄城看一下文卓的工艺精品公司,然后,一起去民政局。
这一天,狄小红出差在外。
狄小红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刚刚出现,我便开始抬头望天。她就是婚纱公司的老板。狄小红的婚纱公司在二楼,文卓的精品公司在三楼,两人各自的办公室在四楼,楼下是两家公司卸货、发货的场所,他们租赁的是同一座工场。我有一种预感,两家公司根本就是嵌顿在一起。文卓说,他们是在租赁工场的时候认识的。
文卓对戚美玉不曾隐瞒,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能力和表述能力,在戚美玉面前刚刚够用。是的,刚刚够,不是游刃有余的那款。所以,他的话不滑,偶尔还有点涩,这听起来更加真诚。
文卓还给戚美玉透露了一桩秘密。当他还是懵懂少年,一天午后,被生病的母亲支使去巷口抓一帖中药,药店大敞着,人不在,以前听母亲说,这时节买家少,店员或许正在楼上值班床偷歇。上楼看到的一个景象,把他吓得眼睛直了。在蓬松的药材中,有一个只穿红色小背心的女人,正在满头大汗地剧烈运动着。他猜,那旁边还有一个人。他拼命地逃跑下来,根据回忆和拼贴,他发现,那个红色小背心女人,原来就是药店门口摆摊卖青草药的,母亲经常去她那里抓蜈蚣草、鱼腥草和荷包兰,煮一大锅全家喝了退火。也不知道火气为什么总那么大。戚美玉听到这里,禁不住笑,她小时候,阿姑也是这样,时常逼她喝凉水。文卓关于性的最早记忆,就这样与中药味连在一起。他第一个结婚的对象,是中药店的药剂员,他给她买了许多红色的小背心。不到半年,他们就离了,他发现自己错了,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从那以后,他就更懵懂了。
或许,对戚美玉,文卓本来就是真诚的,是我成见太深。
那一天,戚美玉跟在文卓身边,像偷情一样,有着不为人知的甜蜜,随着脚步的临近,也有点脉脉的惊心。
门房伯哈着腰迎接文卓,为他开了钢栅门,对戚美玉例行瞧了一眼。戚美玉看到,门口的对联写着“经营不逊陶公业,生意常怀晏子风”。书法写得很业余,文卓看戚美玉的眼光,有些赧颜,戚美玉回报了一笑,倒有一种踏实的家常感。有情的人,眼前蒙着一层朦胧的糖纸,整个世界都是甘之如饴。
一切如期进行,顺利得让我心内莫名发慌。
打完结婚证,戚美玉带文卓去乡下看戚氏家族的老房子榕荫山房,然后一起回海阳市,在金海湾大酒店开房。现在,他们是夫妻了。当他们成为夫妻之后,我是否该改变主意,为戚美玉开心?
其实,文卓的温存是令人感动的。我几乎不知道男人的温存是怎么样的,或许,就是文卓温存时的样子。他与小强不同,小强是只有十八岁的大男孩,他的爱是奔突的,激烈的,强硬而又稚嫩的,自我的,令人无可适从的。而中年的文卓,他的爱是深婉的,沉甸甸的,令人安心而信服的,一经发起就声势浩大,却又千回百转,天上人间不知今夕何夕,等到缠绵过后,人在床榻,只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美玉,花儿锁我先拿走,去找找她的叶子锁。”
别!别!我心里嚷嚷道。戚美玉出生之时,我就随着她,不曾离开过半步。我这是担心她呢,还是自己心里恐惧?我有一个古老的预感,我们的分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戚美玉听懂我的话,只要她安静下来,便有一颗玉的心。可是,这个重色轻友的丫头,这关头她什么都听不见。她把我摘下来,交付文卓。
我耸了耸身子,挣扎着,文卓慌乱把我握住。奇怪是,文卓宽大的手掌像有避震装置,我不再动弹,静默下来。
未来的命运,像敞开在我面前的一条暗暗的长长的隧道,某个地方,或许会有几缕光亮。我有忧心,也有好奇。
三
“这款种老、水好。现在找不到喽。”
“老缅甸玉啊,工艺也老。”
“蓝水蓝得这么正,罕见罕见。”
随在文卓身边,走过的桥比上半辈子走过的路还多。这几天,文卓一直奔波在海阳市周边的古玩店,寻找识货的高人。
这些赞语,说的是我么?在小惠和戚美玉身边,我根本不知道,关于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评判。原来,在我所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更大的世界。这个更大的世界,对于一个人、一件事、一种东西的评判是使用标尺的,这种标尺冷面,僵硬,没有人气。我对自己玉的身份产生了极大怀疑。一枚玉的品质难道仅仅因为她的质地和雕工?她的存在难道只是为了炫耀和展示?如果一枚玉没有心,如果她的存在不是为了感知和体悟,那么,生有何欢,死有何憾!
夜晚,我被文卓安置在工场四楼休息间的抽屉里。他还像往常一样,回到狄小红的那个家。独处的时光里,巨大的黑暗像这个世界鬼影幢幢的帐帷,我竟毫无惧色。各种疑虑以更强大的姿势拷问着我:我到底来自何处?欲往哪里?我为何留存世间?像考场中一个没能把题回答的小孩,我想着想着,头壳越来越疼。以往,为小惠失眠,为戚美玉失眠,现在,我终于为自己失眠。
早上,文卓前脚刚进办公室,狄小红后脚就到了。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形属玄幻。狄小红的故事,文卓是在第一时间讲给戚美玉听的。戚美玉不以为意,或许更为他加分。这桩秘密,规模更加宏大。用通俗易懂的话说,他们是一女两男住在同一屋檐下。狄小红的名下,有一个丈夫和一双儿女。当然了,这个丈夫,并不是文卓。家里蓦然住进一个陌生的独身男子,对丈夫,狄小红得有一个说法,潮汕俗话,说是拿筷子遮眼睛。这双筷子显然有些单薄,狄小红说,文卓是她婚纱公司的司机。这个司机好人物,还是塑料精品行的老总!狄小红丈夫的眼睛谅必不大,他把狄小红的说法认下了。这个丈夫很特别,宽厚些说,他是一个极度单纯的人,刻薄些说,他的心智差了一点点。潮汕也有一句俗语,说是欠煮了一捆柴草。这个丈夫,我也很想见识,只是文卓不曾把我带回家,至今缘悭一面。因为司机这个身份,文卓每天载着狄小红出双入对,也就顺理成章。这个司机无家无室,就在狄小红家里搭伙吃饭。文卓说,在那个家,他是人不人鬼不鬼。
狄小红熟络地关上门,把文卓推搡进休息间。隔着一个抽屉,我闻得到她的肉气充满了舒张的欲望。他们是一同进厂的,分开不到十分钟,至于吗。她抱着文卓的腰,缠绵起来。文卓警觉地躲着她,开始拿话说:二楼的下水道出了问题,我已经联系了清通,很快会到。狄小红“哦”了一声,又拿胳膊往他身上磨蹭。文卓又说,你那批出口婚纱,海关归类编号查到了,稍等,我看一下。他掏出手机报了出来:Z2006-0382。狄小红又“哦”了一声,停顿一下,重新调整了情绪,索性往床上一坐,把文卓往身边拉。文卓说,哎呀时间真不早了,我去三楼工场交代一下,得赶往机场。狄小红终于泄气。是的,潮汕机场已搬迁到邻市,航班延误不得。
如果没有猜错,狄小红今天穿的是一套孔雀蓝的套装,风格庄重,气场颇足,泄露春消息的,是它的低胸设计,一挺胸,一拉肩,便有风情万种。这个女人从一乡下丫头,一路走到现在,能是省油的灯吗。
文卓向戚美玉介绍过她的发家史。她在几个一线大城市打过工,做的都是婚纱行业。听听,乡下丫头出外打工,赚个温饱,伺机把自己嫁出去,这是大多数人做的事情。狄小红不,她定了心思专门去做婚纱。一件婚纱的程序,她是倒着学的。一开始,她做装饰和缝珠,这都是手工活,在乡下学过,没太大的技术含量。接着,她学着做车工,车缝是高档婚纱定型的关键,走的线条非常讲究,她可以做到,直线从不偏斜,弧线圆顺而通融。做完车工,她请求做整烫。她天生地对各种面料所需要的温度非常敏感,在烫台上,手一摸,熨斗一过,胚衣就整出来了。然后,她学做立裁、剪裁、制版,得了,除了设计,其他的一应流程都学成了。返回家乡后,她凭出挑的技术成为了一家婚纱公司的技术员,后来又升为主管。再后来,她被老板看中,当了他的小儿媳妇。乖乖,这个小儿子,可不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从此,她以公司为家,业务在她手头不断壮大。
家族式的企业就是这样,复杂的人事关系与复杂的亲戚关系交叉叠加,撕裂争斗。她的心大了,家族企业却没有给她应得的待遇。终于,在某一年的年终岁暮之时,她发动了一场玄武门之变。婆家人都沉浸在拜神过年的氛围里,她却奔跑澄城,租赁工场,购置设备,在春节放假期间,她把在厂里预先囤积的布料和辅料搬走,并挖走了几名技术工。等到大家明白过来,她狄小红的帅字旗已经在澄城的工场高高飘扬。
在这场兵不血刃的政变中,她亲爱的丈夫,站队,默许,支持,他永远与她在一起。
骁勇善战如狄小红,戚美玉哪里是她的对手。听着狄小红高跟鞋嘎嘎嘎渐行渐远,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狄小红知道文卓飞的昆明,她却不知道,他意不在昆明,而在大理。文卓没有说谎,他不是善于说谎的人,只是,他把实话说了一半。
四
文卓是在一个玉贩子低矮的小平房里,下定去大理的决心的。那天,他在海阳市区金陵路的一家古玩摊上,不带希望地把我秀出来。哪里知道,那玉贩子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算您运气好。我这就收拾,带您回家去看。绝配了。”
玉贩子住在老平房,七弯八绕,崎岖逶迤。文卓竟信在这地方会有奇迹,我是不信的。
缎盒子展开时,文卓和我都有些吃惊。不同的期待,相同的吃惊。
叶子锁!
深紫色的绒布上,蓝盈盈的翡翠锁,在锁眼那里,插着一片叶尖微卷、风流俊雅的叶子。好个玉中男子。看着这么眼熟,却唤不起我任何感觉。我侧耳倾听,听不到他的心跳,我故作矜持地向他打招呼,他却更加矜持,不予回话。文卓一会儿把我们并排放在一起,一会儿又把他放回盒子。
玉贩子一改猥琐,挺直腰杆说:
“找到我是您识货!您知道这对同心锁的故事?是榕荫山房的东西。”
榕荫山房?!
“疍夫人听说过吧?她是榕荫山房戚老爷的九夫人,戚老爷从疍家花船把她买下的。老爷尽管已有八房夫人,但娶疍夫人,是正妻之礼。戚老爷说,有前人可学的。那个钱,钱,钱什么就是这样。这对同心锁,是戚老爷与疍夫人的定情之物。”
玉贩子话锋一转,把翡翠的品鉴经验“浓、阳、正、俏、和”滔滔谈起。他取过一把聚光电筒,照开了:
“您看,水头这么长……这个价位不会低,没有大六可买不到。”
文卓无意听他唠叨,他是被戚老爷打动的,这个故事,连戚美玉也不曾听过。文卓深情地把叶子锁再次端起,我突然看到一道异样的蓝光。
文卓文卓,我们上当了,他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他是人工注色仿冒的。
完蛋了,文卓不是戚美玉,他何尝听过我说话。
文卓突然把我攥紧了,在左手心,他的右手心同样在用力。我被攥得有些窒息了,他的双手才敞开来。
“师傅,您自己试试。我的玉是凉的,您的玉已经生温了。”
明白人都会懂,高下已分了。玉贩子的话里,汤水中有多少肉沫都没用,相一枚玉,真的并不是所谓的行业标准可以解决的。我对文卓开始刮目相看。戚美玉的眼光不错。他虽然不懂玉,但他会用心聆听。
就在此时,他打开手机,定下了去往昆明的机票。走出玉贩子低矮的房门,他把电话打给戚美玉。
戚美玉正在赶做“插红萸”。文卓心疼她:
“早知道就不强求你接这个单了。”
“不接这个单,你会返回来吗?”
“当然了。我再怎么装,海滨路的海风是骗不了的,还不得乖乖回到你跟前。”
戚美玉便在电话那头笑。然后,坏坏地说:
“你,不对她愧疚吗?算我替你还一个情债。”
文卓怔了一下。心内的柔情层层漫涌,恨不得立刻把她揽入怀中。
“我明天去大理。同心锁的事情得先办了,我才心安。”
三人成虎,在人类的江湖里,这是颠扑不灭的。这些天,文卓面对的古玩高人,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去大理找找看吧,兴许还能找到原石。
戚美玉显然也是对此前途未卜:
“没有见你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枚玉是单品,就像我自己一样。”
“放心啊,放心。”文卓的话不知道安慰的是什么。
“你回来以后,我们就去榕荫山房哦。”
“会的,结婚那天答应过你的。我们关掉手机,去那里住一段。”
“好,那我让他们先打扫南楼的小阁楼,阿姑小时候住过,我喜欢那间房子。”
榕荫山房虽是私家园子,但两百年过去,世事变迁,子孙开枝散叶,产权归属变得十分艰难。村里戚姓老人成立了管理委员会,收拾几个房间供给海阳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来这里写生,赚点小钱用于修缮,戚姓的华侨和族人也不时自发捐款。小惠对山房感情深,常常是倾其所有。过世之后,这个事情是戚美玉在做。
他们年轻人不知道,我对山房的感情,比任何一个人都深。小惠不在了,只有我,还能够诉说对于山房的记忆。小惠怀上小强的那个孩子,也是在山房的小阁楼呀。
为什么一提起小惠,我就忍不住悲伤。
五
我悲凉地倚靠在躺床上,望着舷窗外的白云发呆。白云一片一片的,像戚美玉自己做的云片糕。我的眼睛一直不曾离开,很快地,头开始眩晕起来。
还是在文卓的身边,还是他带着坐飞机,可现如今,我的悲情有谁能懂。这美丽的牢狱竟是文卓亲手建造的。我轻蔑地瞥了一眼身边的那个人。
是的。他确实是一枚叶子锁。
在大理,文卓觅得一块三公斤重的冰种蓝底老料,无裂,还有手镯位。只是他无意手镯,只为了一枚叶子锁。这么浪费老料,玉雕师实在于心不忍。玉雕师说,手镯位的里面,还有坠子位的。文卓说,这虽是明料,但看到的也只是牌面。况且,做了镯子,叶子锁就得避让。不可能是最好的那一枚。
是的,他确实是最好的那一枚。可是,他怎么可能与我匹配得成。我的心里,山川江湖,沧海桑田,而他,不管外人看来如何与我般配,他的内心,还是天地太初,寸草未长呀。
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撇开我的个人悲剧不谈,文卓是应该加分的。作为生意人,很多人天生地具有一种价值次序的规划能力,利益永远是排序第一的。文卓不是。这已是我第二次对他刮目相看。或许,我应该抛弃成见,为戚美玉和他祝福。
这些日子,我经常会想起传说中的疍夫人。那天,文卓给戚美玉讲同心锁的故事,戚美玉是知道疍夫人其人的。听说戚老爷作古之后,戚家嫉妒冲天的八位夫人终于可以报得一箭之仇。疍夫人被重新送回疍家花船接客,在风雨飘摇的南海上,不知所终。
如果玉贩子所说属实,疍夫人正是我的第一个主人。我是在她怀里开眼、慢慢成长起来的,还与叶子锁青梅竹马,两情缱绻。这一段记忆也不知是何时失去的。失忆这件事,是外来力量的干预,还是我自己痛苦的选择?
我是在小惠怀里复苏过来的。记忆只从小惠开始。
小惠是一个白胖白胖的女孩。如果你看到的是成年之后她枯瘦的面容和身板,你一定会感慨造化弄人。
那时候小惠不满十四岁,榕叶铺村的人都算虚岁的,所以她十五了。小惠读书时,班里男女同学老死不相往来,但偶尔会听到谁谁喜欢上谁谁。村里女孩儿堆在一起做手工钩花,最爱嚼的就是这些。小惠稍稍有点憨,她还拿不定主意,隔壁的小强是不是爱上她。小惠住在榕荫山房。那时候,榕荫山房住得挤挤挨挨的。她与哥哥、堂姐三个大孩子挤在一个房间,就是南楼的三楼小阁楼。小强常常会送给她一些小礼物,中秋节吃柚子时,他送给小惠的是柚皮罐子。他把柚子蒂切下来,还有本事把柚子肉掏出,整个柚子皮却完好无损。蒂子当盖,柚子皮当罐子。做柚皮罐子还蛮费事,要在柚子皮里塞上废纸撑起,然后送去太阳底下晒,在它还没有被晒得坚固之前,不时得跑过去捏形状,圆球形或者柿子形。小惠在小阁楼上远远看得见小强家的院子一角,小强忙活的时候有时会转过身来朝小阁楼张望。等到柚皮罐子晒好了,小强在家门口随手摘下一片榕树叶,卷起来吹一哨。听到号角声响,我和小惠便都有了心事。小惠得揪准时机,避开哥哥堂姐的耳目,一噔一噔下楼去见他。小惠很喜欢这个柚皮罐子,拿它来装盛体己的小东西。有一次,小强不知道哪里来的贼胆,竟然借了村里人的一辆破单车,跑去海阳市的南生百货公司买礼物。榕叶铺村的人,买东西都去镇上的小集市,最威武的也就去澄城,还没听说有人敢去南生公司。路途遥远不说,还得搭两轮渡船。小强是等到榕叶铺村的人都吃完晚饭,才回来的,小腿上还有点皮外伤,说是进村子时,路黑,自行车冲上沙堆,摔下的。他从内口袋摸出一件小东西送给小惠,是一只缀着珠花的小发夹。小惠心内非常喜欢,但她不敢戴上去,寻思着把它藏在柚皮罐里。
我还记得刚把珠花发夹送给小惠的那个小强,他的双手不停地甩着,好像刚刚参加完一场战役,又立刻会返回战场。小强对人一直非常腼腆,他的腼腆和他对小惠的勇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魅力。那时候,他们躲在山房南门外的一颗大榕树下,榕树的虬干宽大而有遮蔽性,有人在这里供奉了一尊关公神,初一十五都会偷偷来祭拜。关公红红的脸膛和斜挑的剑眉让我有些害怕,小惠和小强见面时我总是低着眉目。
那个时候我总是莫名地心惊。见关公会心惊,听到大队的广播里说“红色电波传来了某某某的最新指示”我也心惊,晒谷场那里有什么批斗我也心惊。
不说了,远离那段日子总是值得庆幸。可是,人世间的烦恼哪里有得尽。
跟戚美玉在一起,虽然有孤寂,有无力,但日子安静有致,像山涧的溪流一样,涓涓静好。现在,人随飞机穿行在云里雾里,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闯出来一个不明飞行物。这种惊扰,与小惠时代不同,那个时代惊扰是外来的,现在,惊扰来自人的内心。
最庞大的不明飞行物迎头撞来,却是在文卓下了飞机之后。
狄小红双手抱肩,酷酷地倚在文卓办公室的文件柜,眼睛里透着金属的寒光。夕阳从窗棂射进来,与她的眼光交锋之后,折到了门口。文卓拿着钥匙的手搁在半空。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还是得回来的吧。”
两句话都是狄小红说的。一句说了然后才是另外一句。
“她是谁?”
“就是上周一前来观摩的那个女子吗?”
依然是狄小红在说。
“一起去大理,游蝴蝶泉、看白族歌舞,花巨款……”
“啧啧啧,I 真服了you。”
文卓杵在那里,我换成他,也是如此吧。狄小红从哪里知道这些消息的。文卓也在脑子里转了几转,对了,是工场门口的监控视频。当然,是她的心先起疑了。然后,她去查他在昆明的业务来往,然后,查他的银行卡花销,然后,她开始掺入想象。
“怎不带她回来呀。让我好好瞧着,这个相好是什么货色。”
听到这句,文卓怒了。是的,我对他的发怒很满意。
“住口。她已是我妻子。”
什么?
狄小红傻了。
狄小红突然变了一个样,她脸上的凌厉之气不见了。她像一个天真的无知少女,脸上慢慢地绽上了笑,她的眼神在向文卓问询,在向这个世界问询:
这是什么意思?
文卓放弃了怒,垂下头说:
“我们登记了。”
狄小红突然又变了一个样,她脸上的天真之气不见了。她像在一刹那间老了,老得像一个得道的高人,世上万事都可淡然处之。她苍老的声音说:
“哦。是结婚了。”
文卓痛苦地闭上了眼。
狄小红突然高尖着声音,像砧板上的切菜刀,一个字接着一个字,源源不断地滚出来:
“你要结婚是不是!我离婚,我们结婚!你不能不声不响地就结婚!你要走,就把孩子领走!是你的,两个都是你的!”
狄小红面无表情地重复:
“两个都是你的!”
六
我是被狄小红裹挟着走进这个家的。她搜过文卓随身的皮包,把一对同心锁搜了出来。像缴获赃物一样,转移到了自己的皮包,斩钉截铁地说:
“这个事情交由我来处理!”
狄小红手里有幌金绳,一会儿紧绳咒一会儿松绳咒。她说:
“大宝发烧了。”
说这话,她就是一个无助主妇。
说完这话,文卓就乖乖地开车回家了。
我曾对这个家充满好奇。可现在,我的心已凌乱至极。
狄小红和文卓进门的时候,大宝宝妹挤在门口叽叽喳喳欢迎他们。
“妈妈”“妈妈”。
“文伯伯”“文伯伯”。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文卓就是姓文,前面再没有什么姓氏了。
大宝虽然发着烧,可是活蹦乱跳,不愿意稍停一下。文卓把他抱起来,感觉他小身子还是滚烫,鼻息也重了些。
喂了退热药。二宝羡慕地问:
“文伯伯,妈妈说,你回来了,明天可以带哥哥去海阳……”
“咋啦?哥哥去医院看病呀。”
“他明天去海阳,不上学?”
“嗯。生病了就不上学了吧。”
大宝围过来:
“宝妹上回牙疼,也是可以上海阳去的呀。”
全家人都笑。
文卓这才明白,原来去海阳是他们心中多么幸福的事情,与去海阳比起来,生病算什么。
大宝喜冲冲地奔向他们的爸爸:
“爸爸,爸爸,我明天可以去海阳喽。”
这个时候,文卓和狄小红才被提醒,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爸爸。他一直在大家的身后。
那个叫做爸爸的男人,看起来乐呵呵的,似乎从来也不知忧愁叫什么。他很快与两个孩子打闹起来。大宝把锅盖盖到宝妹的头顶,宝妹把它盖到爸爸的头顶。他蹲下对宝妹说话,宝妹的一只食指,说着说着就戳到了他跟前。他用手掌把那只食指覆下,顺势把宝妹抱了起来。宝妹一蹬,他就滚到了沙发上。宝妹的蛋糕裙平展展地铺在他的身上,像是开了一朵花。
文卓说过的,当时为何会住进狄小红的家,是因为她怀了大宝,希望他去照顾。去医院生产,把她抬上产床的,一头是她丈夫,一头是他文卓。生了大宝生宝妹,日子就像水流一样过下去。狄小红一直说,两个孩子是他的。这事情怎么证明?两个孩子长得像她狄小红,爱玩闹又与他们的爸爸亲。他文伯伯在这个家,终究是外人一个。
夜了。我跟着狄小红进了她的房间,他们的房间大,安放着两张大床。不知道往常这家人是如何安排床位的。这晚大宝发烧,狄小红拉他睡在一床,丈夫睡在另外的一张床。文卓睡在隔壁。二宝跟着保姆是在另外一个房间。
这样的夜晚,不知道有多少失眠之人。与更加艰难的他们比起来,我与一枚不曾相爱的玉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
回想起文卓与戚美玉第一次在一起,哦,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文卓幸福得找不到北,抱起戚美玉在屋子里又啃又叫。我还记得戚美玉被吓得大叫起来,文卓更加来兴了,把她抱到窗口,对着小区里的人工湖大喊:
“我很幸福——”
现在想来,他的幸福也很简单,醒来时有爱着的女人在身旁。可他这个愿望,一直也没能达成,直到遇见戚美玉。
狄小红的丈夫倒是心底无私,很早沉沉睡去。她半夜爬起来,去敲文卓的门,没得回应,趿着拖鞋蹑手蹑脚折返回来。叹了口气,上床睡去。
我在黑暗中,想念戚美玉。
七
像一场龙卷风,平地而起,把一切连根拔起,摧毁殆尽之后,呼啸而去。戚美玉满目疮痍的世界和内心,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
每天,戚美玉会去一个地方,亲子鉴定中心。
常常是,她静静地坐在走廊的座椅上,看着各式人等进进出出。
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进去,又慌里慌张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从办公室出来,打电话给亲人,小声说,材料太少,会耗尽的,我们犯得着做这个吗?对方不知道叽里咕噜了什么,他一边大声咳嗽一边走了出去。一个老男人蜷缩在角落里,一看到开门就迎上去,可是,没有人搭理他。
有些人的故事是紧致的,故事中人是共谋关系,他们来了就离开了,故事封存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有些人,故事是缺裂的,故事中人是拮抗关系,撕裂开的口子长长地敞着,风吹日晒。那个老男人就是。发生纠葛的是他儿子。儿子当年在酒吧与一外地女子发生了一段婚外情,分手之后,那女子把一个孩子扔给了他。怕影响他们夫妻感情,独居的父亲把孩子接手过来抚养,爷孙一起过了近十年。可是,儿子对于这个孩子的狐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个孩子的存在也成为了他在妻子面前的死穴,有一天,他终于走进了亲子鉴定中心。鉴定结果不出他所料,他与这孩子并无亲缘关系。他背了近十年的黑锅,终于可以卸下。可是,老屋子长出的榕树根,早就不分你我了,爷爷与这个孩子的感情已胜似亲生。为了留住孩子,爷爷每天守候在鉴定中心的门口,希望鉴定人员可怜可怜他,给他修改一下鉴定结果。
有一个鉴定,最终却是没有做成。但那个男人进进出出已经好几趟。他是很感激鉴定人员的风险提示的。是的,鉴定结果完全有可能与委托人的意愿不相一致。那个男人是为王奶奶而来的,他是王奶奶的弟弟。王奶奶的儿子在外经商,听说与另外一个女人过起了日子,但她只认家里的儿媳妇。王奶奶怀疑,自己的儿子没有生育能力,家里的孙子哪里来的,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媳妇对她好,还为他们家留根,这就够了。问题是,意外发生了。王奶奶的儿子发生车祸死亡了,他的生意全盘操纵在情人的手里。王奶奶最终放弃了鉴定。遗产多少没有关系,这个媳妇和孙子她必须得保全。
戚美玉本不是来看人间百态的。
她心里已有了足够多的苦。
看过狄小红对文卓发动的第一场战争,就知道她用什么策略对付戚美玉。狄小红头次见戚美玉,带来的东西有三件,一件是文卓和她与工场出租方的二十年合同,一件是文卓与大宝宝妹的大尺寸合影,一件就是精美盒子里边的一对同心锁。是的,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戚美玉身边。
展示第一件物品,狄小红是有火药味的,她温和的口气里,她才是可以与文卓一起策马疆场,闯荡江湖的人。展示第二件物品,她是含情带哭的。她说她爱文卓,更爱两个孩子的父亲。孩子们出生以后,他们就不是两个人的爱,而是一个家。文卓就是大宝宝妹的亲生父亲。最后,她把一对同心锁展示了出来。我多日未见戚美玉,她竟瘦了一圈。她拥有婚姻的这段短暂时光,文卓不在她的身边,我也不在她的身边。而她,每天都在赶活,赶插红萸,赶百屏灯。百屏灯是榕树铺村三月初八游神祭神活动要用的,日子不远了。
“对不起。我只能这样选择。”狄小红接着说:
“这价格不菲的叶子锁,与你的花儿锁果真是一对。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狄小红说的这些话,戚美玉听来都是不同频道。她只想听听文卓怎么说。说到底,其他人与她毫无关系,有关系的只是文卓。可是,文卓被狄小红安排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大宝。
这么说来,父亲对于孩子,孩子对于父亲,皆是多么重要。
戚美玉说:
“如果两个孩子是文卓的,那么,他走吧。”
这一句话,戚美玉预见到后果了吗?狄小红一听,整个人变得不同起来。她杂沓的焦灼骤然间停下,脸上的表情肌和顺地归拢一处,很快地积聚了一种力量。她用尽所有的力量把这句话抓牢:
“一言为定!我们立刻去做亲子鉴定!”
戚美玉与亲子鉴定中心的缘分就是在此时确立的。她多次看到鉴定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取鉴定结果的三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男人紧紧地抱着孩子,亲着,贴着,不愿意离手。女人高昂着头,像女王一般。
戚美玉想,或许,那个男人就是文卓,那个女人就是狄小红。只不过,他们的孩子有俩。
狄小红把司法鉴定意见书拿给戚美玉看过。那份有着红盖章的鉴定结果写得果然专业。结论:文卓和狄小红是大宝和宝妹的生物学父母,从遗传学角度已经得到科学合理的验证。前面还有一段数字分析,“经计算,累积夫权指数(CPI)为1.28×108,相对父权概率为99.9999992%。”
戚美玉向来对数字不敏感,想不到这次却一下子印入脑海。在这个结论上面,还有他们父母孩子四个人并列的大头像。与狄小红作为利器出击的父子三人合影比起来,这一张,无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卓难道能够不被击中吗?
戚美玉有些感慨。以前看过太多的女人,必须依靠儿女来确立自己的尊严,如此看来,原来男人的人生,也需要凭此确立。
回到了狄小红的那个家,文卓所有的感觉是不是通通改变了。在这个家,女人是自己的,两个孩子是自己的,平畴万里的江山,一转瞬间,已经易姓了。
戚美玉是决绝的。当狄小红把同心锁留下,转身离开之时。戚美玉把我拿起来,戴回身上。然后抓起那个盒子,连同那枚叶子锁:
“请带回吧。它于我没有任何意义。”
狄小红说:
“让它留下吧。我的心会稍安。”
狄小红尚未走出戚美玉的小区,身后传来了人工湖溅起的水花声。
八
农历三月一开始,戚美玉的百屏灯就被接到了榕树铺村,制作成一百支大型的香烛,阵容盛大地插在双忠公祠后面的山脚下。海阳周边的几个城市,喜欢民俗的朋友奔走相告,过来看热闹。
“韩江两岸是名城,街头巷尾尽歌声。”有人边看纱灯,边把《百屏灯》唱了出来。以前的纱灯,是为元宵节观灯做的,等到小惠时代,是做成工艺品,用玻璃橱罩着,摆放在家里当摆设。文卓说,狄小红给他讲过,小时候家里有一屏纱灯,是八宝与狄青的,但她们姐妹每次走过那屏纱灯,都戏谑地嚷嚷:飞龙刺狄青。好像一提起狄青,如果没有飞龙来行刺,多么不够刺激。可惜到了戚美玉时代,纱灯业已经衰颓,不管她做得多么精妙,游神活动过后,这些工艺品都会作为供品,付之一炬。
因为纱灯身上的悲剧色彩,人们对其珍爱更胜往昔。有游人把戚美玉的纱灯拍下来,制作成视频,在网上和微信里展播。戚美玉那些精致超微的手工,被大家在屏幕上一点点地放大。不论放大到什么程度,它们都是同样的精致。开始有人建议人肉搜查纱灯的作者,开始有人抖出戚美玉的名字,戚美玉的手工故事开始变本加厉地传播,越来越变形。在传说里,戚美玉更像是一个孤胆英雄。只不过,她挑战的敌人不知是谁。有媒体多方联系采访,一连几天戚美玉干脆把手机关上了。
戚美玉还是经常去亲子鉴定中心,似乎成瘾了。在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中,戚美玉有时会把自己代入其中,问自己,如果是她,或者是他,愿意如何选择,能够如何选择。她发现,所有的角色,可以选择的路径非常少。她更发现,在自己之外,不幸的人何其多!
初七那一天的夜晚,榕树铺村盛大的游神活动敲响了开场鼓。戚美玉自己来村里看百屏灯。也只是远远地看,然后,她回到了榕荫山房的小阁楼。这一天,她甚觉倦怠,看日子,却是对的,原来例假应该到来了。突然,手机响了起来,她因意外而受到惊吓。出门前,手机倒是开了的。
是文卓的声音:
“美玉,我们见一面吧……”话没能说完,早已泣不成声。
狄小红给戚美玉下战书的那段时间,文卓不是没有联系过戚美玉。他每次打的电话、发的短信,说的内容大致两类。一类是“不要做出承诺,等我。”戚美玉的简单理解是,他在徘徊。另一类是“我在医院照顾大宝”、“我发了烧,头晕脑胀的,宝妹也病了,正在看她输液。”据说那段日子,他们家大人小孩四个先后都病了。戚美玉知道,他是真忙。
劫后,这是戚美玉听到文卓说出的第一句带感情的话。
我已经沉默多时了。在戚美玉独自疗伤之时,我不愿意聒噪不休。但此时,为了戚美玉不再受到伤害,我不得不断喝一声:
“戚美玉,不要再见他了!”
我老了,戚美玉听不到我的声音,她定了定神说:
“我在榕荫山房。”
榕树铺村早已人山人海,村里的八个壮汉,用两乘大轿抬着双忠公的神像,从村南游到村西,又从村西游到村北,最后在当年的那个晒谷场停下来,大型的民俗表演开始了。榕荫山房远远地观望到晒谷场,有不少人找了关系,进来寻找合适的观景台。戚美玉从山房的南门把文卓领进了小阁楼。
文卓一步一步地踏上小阁楼。
这个阁楼不大,只是屋檐和栏杆的木雕花牙做得古朴雅致,小惠时代,这些花牙是被水泥糊住的,后来才重新修复。
这是他们办结婚证分别之后,第一次见面。恍如隔世。
文卓的眼光一步都没离开过戚美玉,戚美玉的眼光一直在栏杆外。
晒谷场的人海发出一阵阵的波涛声,整个世界都在对此回应,天和地似乎都动了起来。
戚美玉先开的口:
“天地真大,有时候觉得,每一个个体的人,根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文卓的眼泪大滴大滴嗒嗒地落下来,戚美玉听来,以为是落雨。
戚美玉望了望阁楼:
“这个阁楼,是我阿姑住过的。”
我很怕戚美玉把小惠的故事讲下去。但是,她已经开讲了。
小强来阁楼看小惠的那天,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小惠因为右脚外伤,请假在家。小强是逃学前来看望她的吧。小惠穿着吊带娃娃裙,白嫩白嫩的肩膀和胳膊像莲藕一样,让人恨不得啃一口。对小强小惠有很多好奇,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去海阳有多远,曾经迷路吗?一个人去怕不怕?南生公司都卖什么东西,与镇里的小店是不是一样?海阳也有小镇上的那种遮遮掩掩的照相馆吗?小强问,为何没看她戴过那个珠花发夹。小惠移过柚皮罐,啪啦啪啦把它找了出来,小强就势帮她别到头发上。他们靠得那么近,小强一下子就把小惠抱住,抱住了就亲,亲了就更冲动……
五个多月之后,天已经冷了,小惠穿夹层裤的时候,发现裤腰头根本提不起来,让堂姐帮忙堂姐也帮不了,只好去找妈妈。妈妈被惊呆了,女儿的身孕掩也掩不住……
“爷爷奶奶为了挽回戚家面子,起诉小强强奸,阿姑还未满十四,小强的罪名更大,他犯的是强奸幼女罪。”
戚美玉讲的是久远的故事,但文卓听来寒风阵阵。
“宣判大会就在晒谷场,小强被押着游街,从村南到村西到村北,走的就是今晚游神的路线。阿姑闭了窗户不敢往外看。第二天,阿姑终于搭了两轮渡船去了海阳。她被送往医院,剖开子宫取出胎儿。从此之后,小阁楼的这些窗户不曾为谁开过。”
戚美玉转向文卓:
“阿姑把手艺传给了我,连同她身上被加上的锁。”
文卓绝望地看着她,她安慰道:
“我不是阿姑。上工艺美术学校之后,我把阿姑的纱灯工艺进行改造,一同改造的还有其他。我怎么还可能是她。”
戚美玉走过来,脱下文卓的外套。文卓一把把她抱住:
“美玉,给我时间,让我想想办法。”
戚美玉挣出两个肩膀:
“大宝宝妹需要你,你也需要他们。过了今夜,你就安心走吧。我只是需要一个仪式来帮助自己下定决心。”
戚美玉觉得下腹的深处已经暗流涌动,可是,有什么庄严的仪式,是可以因此停止的。她一层层地脱下自己的衣裳。到了最后,她抓起胸前的花儿锁,咚地一声抛了出去。
九
我是在被抛出的时候忽然恢复记忆的。
当年,我正是在被抛出的时候忽然失忆。
那时,我已经快落地了,顷刻之间粉身碎骨,可是,我的叶子锁哥哥冲到了我的前面,他落地有声,珠玉迸溅。我坠落在他破碎的玉身之上,得以保全。戚老爷过世,疍夫人被遣送回花船之时,所有人都对我们这对同心锁恨之入骨。他们恨的,是他们没能够得到的爱情。
这一次,没有谁能够保护我。
我在空中划了一个美丽弧线。
我的眼前,是红闺雅器,湘帘低垂。
我的眼前,是小阁楼被水泥糊住的木雕花牙。
我的眼前,是戚美玉被抱起时,窗外那一湖平静的水。
时空倒错,我终于要落地成灰,归于静寂了。
晒谷场疯狂的人潮已经退去,天地安静下来。文卓很累,他已睡去。这一场高强度的运动,他是从未有过地用心用力,却又力不从心。戚美玉睁着眼睛,脸上有一种被平刮过的洁净,这使她的秀丽有点险峻,似乎一脚踩空,就万丈深渊。她任由经血从身体这口泉汩汩流出。红流浸渍了床单,又弥漫开来,把两个人的身形勾勒出来。她一动不动,红流又一阵汹涌而来,竟成了海,波浪翻滚……
戚美玉是否熬得住?“插红萸”还没有做完……
(责编:郑小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