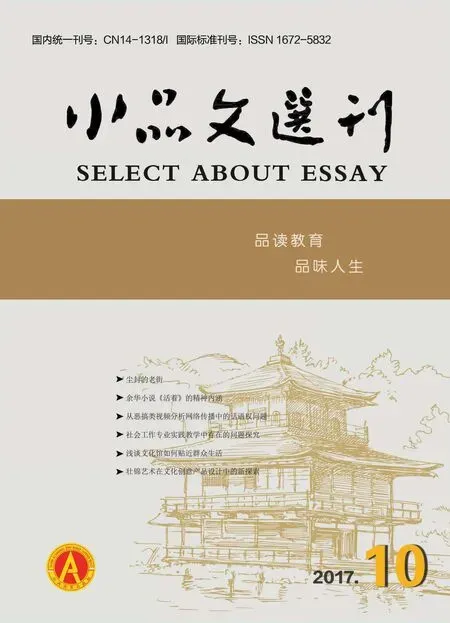延安文艺中的家庭想象
——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为例
王俪颖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00)
延安文艺中的家庭想象
——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为例
王俪颖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00)
延安《解放日报》是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其文艺栏和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综合副刊是当时全国报纸中发稿最多、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文艺阵地,是当时延安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其作为延安文艺政策的晴雨表、解放区文学的档案馆,记录了延安文学发生、发展以及逐渐规范化的全过程。而延安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因为与政治意识形态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上乘五四文学传统、下启当代文学规范而受到高度关注,且报纸作为现代传播媒介为其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报纸的文艺副刊保留了当时文艺创作最为珍贵的原始史料,使得众多研究者们在各个时期对《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改版前1941年9月16日至1942年3月30 日“文艺栏”专刊阶段,以这一时期有关家庭的作品为重心,试图探讨延安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家庭想象”,从而对延安文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1 “文艺副刊”的生成
作为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报纸,《解放日报》“文艺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代表着当时延安文艺新潮的主要探索方向,《解放日报》副刊“文艺栏”作为一个独立的文艺副刊,是“八大专刊”之一,共111期,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由于编辑丁玲采用大度、宽容的编辑方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较为自由、开放的文学环境,相比较于改版之后影响更大、引导性更强的《综合副刊》,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文艺栏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繁华景象,鲜明的体现出了新旧交替时期文艺发展特点,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在内容形式上仍然以五四传统为主,另一方面作为延安文学体制化生产的前夜,已经明显有了新的气息,关注这一阶段的文学,对于还原延安文学体制化生成及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在1941年9月16日至1942年3月30 日“文艺栏”专刊阶段,丁玲共主办了102期,后由舒群接任主编,对于“文艺栏”的创办,编辑丁玲说过这样的话:“文艺占着解放日报的八分之一的篇幅在边区出现,是第一次。以前是不可能有。这时因为党报的扩大,需要以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的作品。同时,来到延安的作家们也缺少发表文章的地盘(在去年这时只有一个文艺月报)。加上边区对文艺生活感到缺乏,他们要求着文艺的学习。而且许多青年的作家,也愿意有那么一个地方能把自己的作品供给大家来征取意见。因此在解放日报一开始,文艺栏即担负着这几层任务。第一、团结边区所有的成名作家。第二、尽量提拔、培养新作家。第三、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第四、提高边区文艺水平。文艺栏始终在此种根据中进行工作”。①这段话体现了丁玲的编辑策略,反映了党的文艺方针及党报对文艺栏的指示,影响巨大而深远。
2 家庭题材与《解放日报》
家庭问题天然地地与社会规划联系在一起,家庭绝不仅仅是个人情感寄托和生活场所,更是构成一个政权的社会框架,个体对于家庭关系的认知,更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社会发展面貌,因而当对一个社会进行重新规划时,更要从改造家庭入手。在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文学剧变时期,家庭题材首先会出现在作家们的视野中,而文学作品中的家庭题材,一般多侧重与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在这两代、两性冲突之中,伴随着的是现代化的步伐,是“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家族中的认同和尊重。纵观20世纪中国文坛,作家们在思考着的始终的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不论是子君、莎菲这样都市中小资产阶级女性人物,还是远处于封建落后农村中的女性,要实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理想,就必然要建立新的现代民主国家,变革社会制度。而这一切,只有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才可以实现。延安是新时代新文化的摇篮,延安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蜕变的时代,新的事物层出不穷,同样旧事物也未完全消退。而作为延安大型文艺阵地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则成为了记录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文化标本。这一时期“文艺栏”聚集的文人,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均以“文艺栏”为阵地,张扬自身的文学理念,以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文艺栏”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学传统”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过渡时期,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采取批判的视角,按照人性的价值取向和民间的伦理逻辑聚焦人物、观察世态,此类带有独立批判意识和探索性的作品,对其他解放区作家也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延安时期新的生活给作家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促使着作家们以明媚的积极的笔调歌颂新的生活,表达对新生活无比的喜爱。这两种不同基调的创作,同样出现在以婚姻关系为主题的家庭题材的作品中。
3 婚姻主题:有批判有新生
3.1 人性审视下的批判
当我们把目光转到以婚姻为主题的家庭题材作品时,会发现延安文学依旧延续了五四时期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批判,与五四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不同,这一时期启蒙的主体是根据地的农民,同样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根据地农民面临着思想观念、行为标准受到严重冲击的挑战,在40年代初的延安,民主思想观念的传播还处于初始阶段,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封建伦理道德对与边区农民,尤其是广大妇女的禁锢依旧牢固,政治经济上已经开始当家做主的农民如何在个人生活上做主,如何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敏感的作家们发现了这一主题,在创作中进行了揭示。
在丁玲的作品《夜》②中,作者提出了离婚这一严肃命题,故事情节很简单:乡指导员何华明不想再继续和年龄大且“落后拖后腿”的妻子在一起,与同样年轻而婚姻不幸的“妇联会委员”侯桂英之间差点越轨,而最后在“都是干部”“闹离婚影响不好”的压力下没有出轨,最后,“天渐渐的大亮了”,一切矛盾似乎也都消散了。故事虽简单,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内容却很深刻,远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深入到文本细微的层面,则还有许多更有意味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现。从何华明的角度出发,婚姻于他而言,是他加给自己及其所爱的人的一副精神枷锁,作为指导员的何华明,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然而旧的婚姻制度,传统的封建观念“闹离婚影响不好”则深深阻碍着他个人的幸福生活。解放区的农村有了新的变化,然而旧式家庭观念仍然顽固存在,人们在政治上翻身做主,生活上有了崭新的开始,然后旧式的婚姻观念却牢牢锁住这些新人物,故事中的侯桂英也是一个不幸者,她被“革命”从卑贱的地位中“解救”出来,获得了女性的“自立”和“自尊”,并且,她还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当上了“妇联会的委员”,然而个人生活却是不幸福,“闹离婚不好”这样旧式传统的婚姻观念将其牢牢锁住。这样折磨着三个人的婚姻,却因为旧式婚姻制度而无法将其打破,作为边区农民的领头人的何华明,还尚且不敢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正当情感和正当权益,无法冲破陈腐的封建意识的困扰,最充分地说明了在边区的土地上,要彻底驱逐封建道德观念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3.2 太阳下的新生
虽然有批判有暴露,但是光明始终占据着延安文学的主导面。“太阳的升起,最终改变了民族历史的走向,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纪元的开始”③太阳的气息洋溢在整个延安地区,《解放日报》常常以“太阳”比喻党和革命领袖,在这里,有着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新气息,全新的生活也带给了作家们全新的感受,尤其是解放区中的农民也不断地觉醒成长,反映到婚姻题材上,也表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二不浪夫妇》、《夫妇》、《自由—新野风景之一》都从婚姻角度表现了延安农民的思想觉醒。《二不浪夫妇》④中,老实巴交的农民丈夫总是怀疑妻子与八路军干部“白同志”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因为妻子“长得很苗条的善于卖弄风情的”,甚至怀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长期的猜疑导致夫妻关系严重不和。而妻子最终在白同志的教育劝服下,与丈夫重归于好,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梁彦的小说《自由—新野风景之一》掀开了乡村爱情伦理关系的新篇章,“无论是小寡妇巧珍,还是丈夫牺牲的大媳妇金兰嫂,都没有重复鲁迅笔下祥林嫂、单四嫂子等寡妇的生活方式,而是以新的姿态开辟着新的生活,她们不再为礼教的束缚而忧心忡忡,也不再把礼教的规范作为生活的原则,她们以新的社会主体的身份和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主动追求个人的幸福生活,寻求感情的慰藉”,而在新的社会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了初步的民主思想的社会群体也不再是“传统礼教的负载者”和“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而是“宽容、同情地理解与支持着寡妇们的生活方式”。⑤
从这一时期家庭题材作品中关于婚姻问题的讲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前文艺创作的温和与宽松的氛围,知识分子依旧坚持五四时期传承下来的人文精神的立场,凭借着自己对生活敏锐独特的观察进行着巧妙的取舍,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独特的理解。
注释:
① 丁玲:《编者的话》,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1942年3月12日,第4版。
② 晓菡(丁玲):《夜》,《解放日报》“文艺栏”1941.6.10—6.11,第二版
③ 胡玉伟:《“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173页。
④ 灼石:《二不浪夫妇》,《解放日报》“文艺栏”,1941.8.1—8.2,第二版。
⑤ 韩晓芹:《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与现代文学的转型>,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7页。
I206
A
1672-5832(2017)10-00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