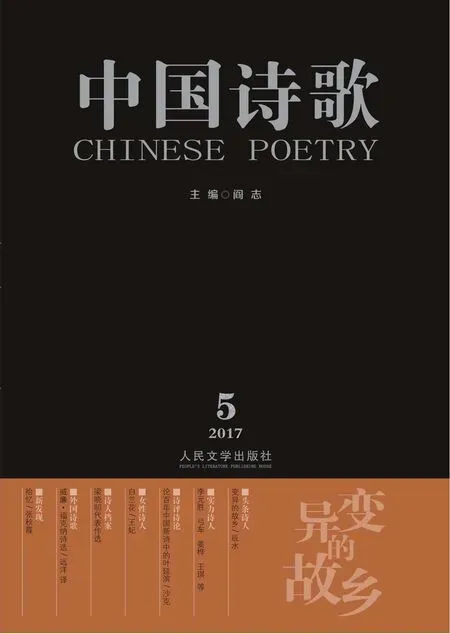与一个村庄的距离有多远
□辰水
与一个村庄的距离有多远
□辰水
“面对一座即将飞走的村庄,我常常会梦见自己坐在上面,去了远方……”
这远方便是我与一个村庄的距离。然而,它到底有多远,我也说不清。在目光所及之处,远方是群山,是落满彩霞之地;而在心中,远方是自由之地,是圣洁的幽兰空谷。可事实上,我与一个村庄的距离,并不遥远。
十多年来,我曾在自己的诗里多次写到过自己的村庄,细致到每一条路,每一个沟沟坎坎……可这个叫作安乐庄的村落,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有时是细微的,比如老梁家把他家门前的一棵树砍倒了;有时是巨大的,比如一条泥泞的道路被覆盖上黑色的沥青。
可突然到来的变化,让人不可思议。一座座池塘被填平,一排排房屋被拆倒,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这一切似乎比马尔克斯笔下那个叫作马孔多的小镇,更为魔幻。在每个清晨,即便是在偏僻的乡下,挖掘机的轰鸣声依然会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记得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在一百多年后,还乡似乎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哪里还有自己的故乡?标准的红色楼房,严肃的红色标语……到处都是面貌相似的村庄,哪一个真正属于你?
相对于这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心中固守的那种“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犹如福克纳的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每天都上演着淬火般的浴火重生。那些捡钢筋头的人、搬运砖头的人、装修门窗的人、承包工程的人……他们各自都在这方土地上实践着自己的梦想。
谁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进程。在这次轰轰烈烈的新农村的变异中,诗人何为?他们是否有能力书写当下,成了检验一个乡村诗人的试金石。
可在当下的众多诗歌里,充斥刊物的依然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题材诗歌。我姑且不说那是一种假,但也真实地反映了诗写者,一种无力触及农村深层次问题的能力。对照这些诗歌,我常常检阅和反思自己的作品,怕它们跑偏方向。
我以一种睁开眼睛仔细观察的方式,来写作乡村题材诗歌,而不是闭上眼睛,想起从前在乡下的苦日子,然后在偌大的老板桌上,写下一首首饱含热泪的诗歌。
好在我依然还保持着与故乡耳鬓厮磨的关系。我在距离村庄二十多里的县城工作,有时在街上还会遇见打零工的乡亲。说到底,我还是一个没有离开故乡的土著民,只不过我的劳动在纸上,工具换成了一支秃笔。
隔三岔五,我就要回到村庄里转悠转悠,有时还要和母亲一起扛着锄头去田地里劳作。田地越来越少,劳作者也大都到了五六十岁以上的年纪。这土地迟早不是我们的,母亲似乎半信半疑。而村里的年轻人也一个个越走越远,这些土地以后到底是谁的呢?
我与这些土地的关系,若即若离。过分地美化和丑化,都是一种不真诚的体验。从内心里出发的感情,必须经过朴素这一关。
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我眼里的村庄,我所居住的村庄,它终究会像古体诗一样消失在社会的进化之中。无论怎么惋惜,怎么感叹,都会无可奈何花落去。
可另一座新型的村庄,它一定会以另一种探索的形式出现。尽管,这一切看来似乎有些魔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