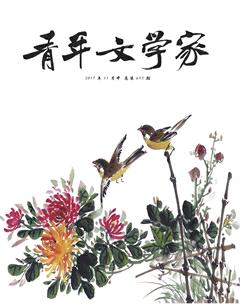中国学术状况细节研究(4)
郁燕敏 李士金
基金项目:本文为李士金教授指导的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2014届毕业生郁燕敏同学学士学位论文,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2015ZSJD010),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资助(PPZY2015C20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2-0-02
数百年来,朱子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历来倍受学者关注。黄震是大学者,他分析说:
《汲泉溃奇石诗》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阴重。观诗至此,唤醒处多。”[1](P162)
古人语言简单明白,但实实在在,含义极为深刻,上述“唤醒处多”决非泛泛而论,均为深刻体会之心得也。回到现实生活,我们考察2005年学界公开发表的朱熹文学研究论文,又有新的学术生态细节发现。有的学者真才实学,自然流露,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有建设意义;有的继续以怪奇生新之词奢谈朱子美学,威风凛凛;有的学者对于朱子淫诗说大感兴趣,议论纷纷;有的继续研究朱子的文学创作,改头换面;有的学者把朱子的观书有感诗翻出来继续欣赏;等等。可谓气象万千,驳杂无比。当然,少不了一个21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生态细节,那就是引用朱子原著的错误多多,不一而足。
一、从2005年朱熹文学研究高论管窥中国学术生态细节
时势造英雄,学术界亦不例外,在科研量化管理的体制下,中国学术生态中涌现出许多学术大腕,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活动能力一流。考察朱熹文学研究领域,也能发现这样人物的身影。朱子的美学思想本来很具体实在,渗透在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中。比如朱子评论石介诗歌:“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2](P4327)朱子承认“不见其全集”,这些诗是“小说诗话中”引用的。就此称道其价值,认为其诗风一般的豪放诗风要佳胜。在“缜密方严”中隐隐透出“雄豪”的气质和本色,这就是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3](P164)而现代一些研究者研讨朱子的美学思想往往背离实际文本,空言无当,令读者头晕目眩。比如宁宇、苏长忠的《朱熹<诗经>接受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一文中的许多话令人无法理喻,比如说朱熹“只能努力将情与理、美与善统一在一起,实现他的美学理想”,乃是因为他“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4],这样说来,若是不出现那不可避免的矛盾,朱子即不会“努力将情与理、美与善统一在一起”了。朱子一生没有讨论过所谓的美学,可是现代人为了完成论文任务苦工分养家活口,或者更多的功名利禄便不顾事实,硬是把许多莫名其妙的新名词贴到他的身上,朱子灵魂有知必然痛苦,可怜他已经长眠地下,无法争辩。本文把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5](P3371-3372)写成了《读吕氏诗托·桑中篇》,小小差误,可证本文作者写作态度。浮夸不实、大言欺人的造作论文,根本就是学术生态的恶性肿瘤。
流沙河《朱熹所谓淫奔》一文[6]可读性很强,这在中国学术生态中别具一格,值得赞扬。他对朱子的淫诗说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是,研究论文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发表见解必须顾及全面,不能以轻薄的戏谑的语气随便乱说一通。比如流沙河戏谑道:
一代大儒想象力之发达,吓死人了。如此侦探眼光扫射之下,《诗经》三百篇,到处见“淫奔”,太可怕了。
这样的语言表达倒是明白易懂了,可是其影响却十分恶劣,一般读者看了对于朱子的印象必然产生极大的扭曲。以为朱子的淫诗说是胡说八道,是神经过敏的侦探眼光,且以这样的眼光,《诗三百》到处见淫奔。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朱子研究《诗经》,态度极为严谨,几十家的注解都烂熟于心,经过多少反复深思探析,才发现《诗经》中的一些篇目内容是男女感情关系的描述,有的很露骨,在他看来就是过分的,这就是所谓“淫诗”。《诗经》三百零五篇,朱子认为淫诗的不过三十,不到全部《诗经》总数的十分之一。这该是很明确的事实状况。可是,到这位作家的笔下,却成了朱子眼中诗三百篇到处是“淫奔”!究竟是朱子“想象力之发达,吓死人了”,还是流的“想象力之发达,吓死人了”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从重复的话题可知,创新固然不易,胡说则可信笔写来,这又显示出中国学术生态的一个细节:通俗易懂的文风使得文章可读性强,但若是思想内容扭曲其影响更复杂更危险。
二、从2005年朱熹文学研究论文引文错误看中国学术生态细节
田恩铭的《论朱熹的唐诗批评》[7],集中探讨朱子对唐诗的批评有积极意义。但本文引文错误很多,大大降低了论文的公信力。有的错误非常明显,如文章引《朱子语类》卷140,把“本既立”写成了“本即立”。文章引《朱子语类》卷140:“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却又混成底气象。”在后面的21个字当中,竟然有四个差错!(一)“句法”應为“句语”之误;(二)原文中没有“却又”二字;(三)“混成”后面的“底”字原文中也没有。(四)“意思”后面漏了 “亦自有”三个字。
正确的原文是: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语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2](P4326)
这样的错误就不是偶然的失误或者字形相近问题。可以断言,作者根本没有认真阅读朱子的原著,否则,怎会出现如此离奇的错误呢。
研究朱子文学创作古已有之,21世纪初期这方面的论文增多是好事。可是许多论文引用原著错误太多[8],大大影响了读者的信心。陈家生的文章把著名的“为有源头活水来”写成了“为有源头活水来”[9];引朱熹诗《兰》:“漫种秋兰四五茎。疏帘底事太关情。”[10](P550)把“谩种”写形成了“漫种”。
黎列南、黎皓《多重美感 多种境界——读朱熹<观书有感>(其一)》[11],有这样的小标题:“意象微妙——‘塘‘鉴之间见匠心”、“巧设题目——对智慧来源的体悟”、“诗外功夫——人格魅力的闪耀”。其它不论,单说“巧设题目”就绝不是朱子的本意,这完全是以自己的心理设想《观书有感》,恰恰相反,朱子始终反对“搞文字游戏”[12](P421),朱子一生对文学的“巧”持极为慎重的态度,基本上不提倡“巧”[12](P365-369),本诗更无巧设题目的可能,题目是后人加上的。即使朱子有题目的意向,也是实实在在,根本不存在“巧设”之事。本文引用《朱子语类》大多只在原文后写加括号的“《朱子语类》”。这样的注释等于没有。因为《朱子语类》有140卷,几百万字之多,即使有什么错误,也很难查证。其中有一条引文写明是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五”。这样虽然没有具体的页码,但范围大大缩小了,所以在发现可能有错时,可以查证。本文所引文字如下: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看了这段引文,我们会发现在用词上有不合逻辑的地方。朱熹作为思想大家,在文字上的深厚功底尽人皆知,记录朱熹说话的学生也都是饱学之士,不至于说出“一书不读,则缺了一物道理”的话来。这句话只能是:“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否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果然不出所料,正确的原文是这样的: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3](P447)
“阙”和“缺”,古文可以通用,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尊重原文,但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可置不论。而这段引文漏了“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就严重影响了读者对朱熹说话的理解。可知越是词语翻新、故作姿态的论文,越是缺乏真正扎实的学问工夫。
李家树的《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14]引《读吕氏诗记·桑中篇》。
“有难言之者”的后面漏了一个“矣”字;“不出于正”的前面漏了一个“无”字;“此言之约且尽者耳”应为“此言之约而尽者耳”;“所以为吾惊警惧”应为“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邪”应为“惩创之资耶”。正确的原文是:
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15](P3371-3372)
有的文字錯误尚不过分影响原文的意思,有的可能存在版本差异,而有的则一字之差,意思完全相反。如上文所说“不出于正”的前面漏了一个“无”字,就使文意完全相反。
考察2005年朱子文学研究的论文,会发现从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中国的学生生态处于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学术杂志增多,论文数量增多,研究领域拓宽,论文的质量总体上则大大下降了。最突出的表现在大量的引文错误上,这是这个时期学术浮躁的无可争辩的最形象的说明和证据。引文错误难免,本不必苛责学者,但引文错误太多而离奇,大大影响论文的思想内容之准确表达,不可不加以探讨分析。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大言欺人,虚空不实,生造词句,让人读了如堕五里雾中,这样的论文不但不能发挥学术文化传承之作用,反而使得大众讨厌论文、远离论文,败坏了学术研究的名声。严格地说,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教育学术,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学风文风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王运熙先生以自己七十年做学问的经历体会告诉我们,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16],值得现代学者学习参考。“上下交争各欲利其身,必至于篡弑,则国危矣!论语曰:放于利而行多怨。”[17](P17)天下无处不利,人人离不开利,然必须义为利。人人逐利,则内耗残杀,人人无利可言。
参考文献:
[1]黄震著《全闽诗话》卷四,《文渊阁本钦定四库全书》。
[2]《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4]宁宇、苏长忠:《朱熹<诗经>接受中体现的美学思想》,《岱宗学刊》 2005年第2期。
[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流沙河:《朱熹所谓淫奔》,《文史杂志》2005年第4期。
[7]田恩铭:《论朱熹的唐诗批评》,《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第6期。
[8]李士金:《从引文错误看编辑责任的失落》,《编辑学刊》,2007年第3期。
[9]陈家生:《格物致知 即物穷理——朱熹咏物诗歌的理学思想内蕴》,《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0]《朱子全书》第二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黎列南、黎皓:《多重美感 多种境界——读朱熹<观书有感>(其一)》,《名作欣赏》2005年第12期。
[12]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13]《朱子语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14]李家树:《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6]参见李士金:《王运熙先生谈学风文风》,《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17]汉赵岐注 旧题宋孙奭疏音义《孟子注疏》,《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195册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