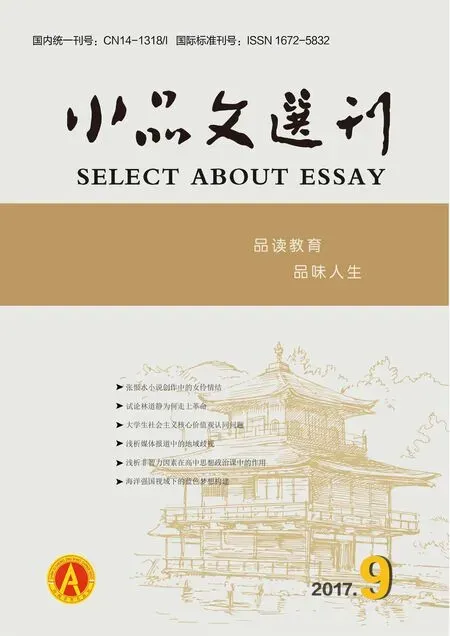浅议“六书”与“三书”
许文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浅议“六书”与“三书”
许文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六书”作为最早的研究汉字构造的理论,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经过后人不断的改善与再解释,已逐渐成为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学说。但是,这个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现了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学者,在“六书”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种更加完备的新的理论,来更好地归纳汉字构型系统,本文简要地归纳了这两种学说的内容,并简单地谈谈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六书;三书;汉字
1 “六书”的提出
汉字是一种古老的自源文字,其产生时间应当在夏朝以前,但是研究汉字的萌芽却是从春秋时代才开始出现的。当时对文字的考释,多散见于表达政治理想、哲学思想的著作或记载历史事件的文献中,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于文止戈为武。但是这种零散的解释并不成熟,也不成系统,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到古代学者以形体为基础的字义考释的雏形。《周礼·地官·保氏》中首次出现了“六书”的名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但是并没有具体阐释其内容。
直至汉朝,班固、郑众、许慎等人才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六书”的说法,尽管名称和次序均有差异,但是为传统文字学的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后世持“六书”观点的学者,基本上都在沿着这一条思路不断向前探索。
一曰象形。这一类汉字保留了大量原始图画的特征,对事物进行客观的描写,对象多是肉眼可见的客观事物。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举了“日”、“月”两例用以说明。
二曰指事。就是为了突出事物的某一特点,在象形字的形体上标注记号。例如“上”、“下”、“本”、“末”等字。
三曰会意。即会合两个象形字的意义组成一个新义的造字方式。如《左传》中所举的“武”字,本义是“用武器打仗”,于省吾在《释武》一文中解释得非常明确:“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象形”是“指事”和“会意”的基础,是原始图画向汉字演变的重大成果,也是汉字孳乳的重要的材料。之后出现的形声字,则在假借字的基础上,使汉字焕发了新的生机。汉字正式由纯表意文字,转为了可以记音的注音文字。
至于“转注”和“假借”,则历来争议较大,总体上是围绕“造字”和“用字”的争论。清代的戴震段玉裁师徒坚持认为这是汉字的两种“用字之法”,并提出了“四体二用”之说,影响巨大。但是到近现代,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转注字不是用字之法,而是汉字自身发展和延续的一条重要的法则,是汉字系统趋于完善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唐兰与“三书”说
在“六书”研究不断向前演进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能够跳出“六书”的圈子,从新的视角对汉字系统进行归纳和解读。唐兰在他的《中国文字学》一书中,指出了当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六书”系统的不足。
首先是指事。唐兰认为这种造字方法只是在象形字中引入了一些符号,只能算是图画文字的一种,而不应该单列一类。其次是会意,会意是会合两个形体的意义表达一个新义的造字方法,虽然与象形、指事有所不同,但仍是表意字的一类。形声字在六书系统中是有着明确界定的,但是其中的一些“亦声”字,并不能很好地和其他造字法(如会意)进行区分。至于转注和假借,则应该只是用字之法,而不应列入造字的范围中。
接着,唐兰在书中又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于汉字系统的独到见解——“三书”。他认为,根据汉字形、义、音的特征,应该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三种。
象形字在唐兰所归纳的“三书”系统中的划分是非常严谨的,不存在独体象形、合体象形之分,这一类字仅指独体象形,保留了大量原始图画的特征。第二类是象意字,唐兰指出,“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发生才算成功的。”[2]与象形文字相比,象意字有了更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有了更强的表达力,代表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但是这一个阶段,仍然没有脱离图画文字的影响。相比起来,形声字在汉字系统中则占有更大的优势,它的出现,代替了本有的象形和象意两种方法,成为了汉字孳乳的主要方式,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关于唐兰新提出的“三书”说,学者所持的意见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批判和反对的声音,不容置疑的是,唐兰在“六书”基础上为我们今后研究汉字系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更有一些学者,在唐兰的基础上对“三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3 “三书”理论与“六书”说的关系
文字为记录语言而产生,语言又是一种用于交际的社会行为,它是不可能有着极为明晰的界限的,更不可能被量化成一个个中规中矩的孤立的个体。这就导致了“六书”说在划分汉字结构的时候,有很多字需要用“某兼某”的方式去模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界限。
“三书”说,其实仍然继承了“六书”的思路,只不过它把汉字结构进一步归纳,扩大了汉字构型理论的指代范围,这样一来,很多游离在“四体”之外、定性不明的汉字,最终都有了归宿。要想让一种理论能够涵盖更多的实际事物,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像郑樵、朱骏声、王筠那样不断细化原有的理论,力图涵盖所有的汉字,而是去归并和概括已有的汉字构型理论,扩大该理论的外延。
唐兰之后的裘锡圭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书”理论,其本质上都是为了用更为规整和简洁的分类方式去整理和概括极为庞杂的中国文字系统。例如陈梦家,他将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类,并指出,“象形、假借和形声是以象形为构造原则下逐渐产生的三种基本类型。”[3]而裘锡圭则将汉字分为表意、形声、假借字,并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分列三章,具体地论述此“三书”的构成。可以说,“三书”说的出现,是在“六书”的基础上对汉字系统的进一步归纳和整理,虽然仍有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但是仍然为汉字结构的探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尝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 杨天宇. 《周礼》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 唐兰. 中国文字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
[3]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 中华书局. 1988
许文静(1994-),女,汉族,硕士在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H02
:A
:1672-5832(2017)09-00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