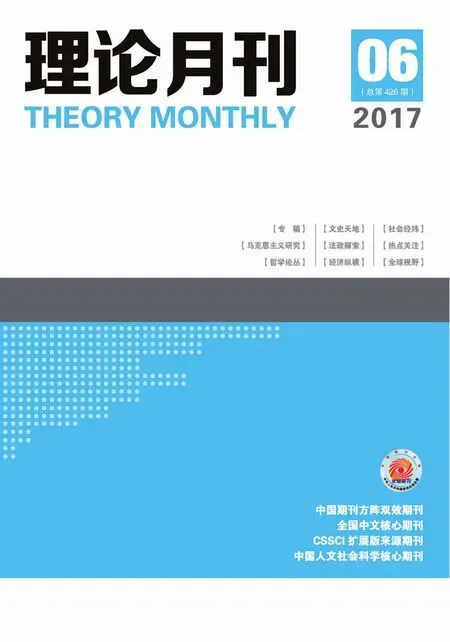从史学的“近代”之争与“近代化”视角论“近代手工业”的起点
熊元彬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 411105)
从史学的“近代”之争与“近代化”视角论“近代手工业”的起点
熊元彬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 411105)
无论是对“近代史”的分期,还是对“近代工业”“近代手工业”等概念,学界仍争论不休。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的仅次于农业的手工业而言,撇开传统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分期,结合“近代”这个渐趋全球化的发展特征,专门从“近代工业”和“近代手工业”的内涵及其差异来论述“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以“近代化“过程中机制洋纱与传统手工织布的开始结合为界标是较为合理的,这个起点应为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英国机制洋纱的输入。
近代手工业;近代化;棉纺织;洋纱;起点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看似一个无须再议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学界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诚如1991年蔡开松所言:“迄今为止,史学界大体提出了10余种分期标准”[1]。并且,学界几乎都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着眼,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起点界定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未结合中国传统手工业向近代的转变和近代渐趋全球化的特征,以“近代手工业”自身皆具近代化机制成份与传统手工并存的双重特征及其变化为其界标。基于此,本人仅求能撇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分期标准,从“政治史”的分期模式深入至“近代手工业”的专题研究。
1 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开端”之争及其成因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历史教研的价值所在,而历史分期的目的则在于更加直观地把握各时代不同的特征,其首要任务就在于找出这个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历史本无断代之分,但是为了人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各时段的特点及其主要内容,因而历史分期成了历史研究的中心和首要问题。诚如林增平所言:“正确地采取分期的办法去研究和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才能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作综合的探讨,找出贯穿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线索,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全面的系统理解。”[2]。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学界研究近代史的中心和首要问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性较大,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不同步性,以及学者所持的标准不一,因而一直争论不休。检索知网可知,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分期”为题的论文就在30篇以上,其中胡绳在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之时,鉴于解放前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及线索不明的问题,首次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80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从而明确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鸦片战争[3]。195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组织了一场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专题讲座,会上胡绳再次强调:“我们所说的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止这80年的历史。”[4]215
自胡绳首次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以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已多次发表论文,对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有学者主张以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认为“比较1840年鸦片战争开端说,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如安庆失守、总理衙门及安庆内军械所的设立,因而“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5]。
也有学者从内部趋向史观着眼,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始于明清之际,如徐中约的1600年说,以及其他学者的1644年说。其中,许苏民不仅反对1840年鸦片战争说的“冲击反应”模式,而且也否认“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从“内发原生”模式出发,从而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6]然而,晁中辰则认为隆庆元年(1567年)东南海禁的开放才是“近代”的开端,“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不仅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而且“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甚至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与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简言之,晁中辰认为“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7]
但是,总体而言,学界从政治史的视角,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界定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其中,1926年吕思勉在其讲义中从“冲击反应”模式着手,肯定了鸦片战争对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标志作用,认为“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8]33。1938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也直接将其起点明确为鸦片战争。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史”以何年为开端,吕思勉和蒋廷黻均未作明确说明。时至1939年,胡绳才明确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它的近代史”[5]406。新中国成立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已得到了基本认可。
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长期争议,其原因甚多,除了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性较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步调不一致有关之外,还与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密切相关,使学术研究被政治化。其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之所以被毛泽东认可,并成为50年代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其着眼点就在于“力图证明中国的历史演进符合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的历史必然性”[9]。5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史学界又改为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从而使我国史学界大多学者也相应改变了原有的分期界标。其中蒋孟引最先响应,于1955年发文论证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端说[10]。
客观地讲,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进行界定不无合理之处,但是作为前苏联外交部官员的齐赫文斯基对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阐述,实际上是在打着马列主义幌子的前提下,歪曲中国的历史,不仅将1644年入关的满族称为“征服者”,而且还将汉族之外一切的少数民族称为“非中国人民”,企图分裂中华民族,为沙俄推行霸权主义制造舆论。更为重要的是,就近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而言,其开端则应延至鸦片战争时期。然而,为霸权主义考虑,不仅一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追溯至明代中叶,以西方传教士来华作为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化”的开端,而且东方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还在其《东洋文化史研究》的著作中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前到了宋朝时期。
虽然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开端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几乎都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论述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题研究,使诸多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及其论文都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开端,从而忽视了近代经济史自身的变动过程。实际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不同步性,因而“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11]478,而不能一味地以政治史的分期来论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2 有关“近代化”与“近代手工业”概念的鉴别及其分期的阐述
“近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处于兼有传统方式并渐趋现代化的一个中间阶段。即“所谓中国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12],是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全面而又综合性的变化过程。正因为如此,清末梁启超在有关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曾明确指出:“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一姓兴亡而划分时代”[13]270。具体而言,“近代化”主要有三方面:一、生产力方面从手工操作渐趋机器生产的转变;二、政治方面从封建专制渐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转变;三、生产方式上从封建主义渐趋资本主义的转变。
纵观史学界的发展历程可知,向来学界多将“近代化”与“现代化”相混淆,甚至同义而用。其中,罗荣渠就曾认为:“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14]16。之后,吴承明又用“早期现代化”的概念来研究“近代中国经济”,认为“讲历史,多用‘近代化’”[15]236,与尚钺将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作为标志一样,将“近代化”的起点追溯到了明朝中叶。对此,黎澍专门撰文指出,以资本主义萌芽作为界标存在着将“明朝的中国历史近代化的倾向。”[16]
但是吴承明则认为“16世纪以来的变迁,实即我国的现代化因素的出现”[17],甚至许纪霖还按照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模式,认为从19世纪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已开始从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18]2。从此可知,罗荣渠及其后的吴承明都认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化,而未能将“现代化”与“近代化”的概念相区别开来。
此外,理清“近代工业”和“近代手工业”的分期问题,不仅有助于打破传统的政治史分期标准来论述工业化和手工业,而且还能透视出“近代工业”与“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历史往往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历史研究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客观真实性,更在于其思想性与时代感”[19]。在以往的研究中,“近代工业”一般指的是采用动力或机器生产的工业,或者是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不分,如刘佛丁就认为在旧中国,“近代工业”通常是指采用动力或机器进行生产,并雇佣3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它与人力手工小规模的传统生产有别[20]135。
如果按照动力或机器生产为准绳,那么中国“近代工业”应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求强”时期,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贵则应始于洋务运动后期,即80年代“求富”阶段的冶矿业。但是,就“近代手工业”研究领域而言,则应从其自身的界标而论,而不应成为“近代经济史”或“近代工业”的附庸。因为任何研究对象都有其自身的内涵和发展特征,而“近代”本身就是居于“古代”与“现代”之间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而“近代化”则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化的一个过程。
从经济方面而言,“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渐趋发展的过程,“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但是“近代史”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史。“近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并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经济上表现为分工明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受打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形成和扩散。由于不同研究领域和地域都有着不同的“近代化”界标,因而在研究各个领域或地域之时,尤其是对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的中国而言,加强不同地区、不同手工行业的研究就尤显重要。
但是,笔者并不否定宏观性的研究,而是认为如果真要进行宏观性的手工业研究,那么就应当尽可能地找到一个合适的界标,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的情况下,综合西方工业国和整个中国的近代历程,以手工业中最为典型的棉纺织原料的变更——洋纱的输入作为“近代中国手工业”的标志[21]。然而,从已有研究的成果来看,学界在研究“近代中国手工业”之时,往往受“政治史”分期长期的影响,无论是在汇编“近代手工业”的资料之时[22],还是从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来看,其研究都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其标志。
实际上,明清江浙一带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并不能将这个“点”概括为整个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明确指出,中西学者在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时,通常有两种基本考虑,即“如果不是定在明末(着重于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冲击)”[23]13。在这方面,与彭慕兰观点相左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从两者激烈的论争中可得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方面,国内外史学界都较为客观地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并取得了重大进步,主张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的确,欧洲是世界最先步入“近代化”的地区,因而学界在研究之时,无意间会以西化的界标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的切入点,将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开始。但实际上,中国的“近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从欧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变动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吴承明所言:“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24]。
在研究近代手工业方面,虽然王翔以洋纱等作为“近代手工业”的标志,但却仍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划分,将其起点界定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25]1。此外,学界在研究“近代棉纺织”之时,也往往是以19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为其标志[26]114。即使是在研究贵州近代土布业之时,学者也仍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其着眼点,将其后大量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作为近代的起点[27]。
实际上,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后云贵等地的手工业并未立即受到影响,而且上海机器织布厂也并不是完全就使用机器生产,而主要为手工操作,存在着手工与机器互补的生存状态[28]。因此,无论是从地域间的影响面,还是从手工业存在的长期性而言,以1840年和1870年代分别作为“近代手工业”、“近代棉纺织”的起点都是不科学的。
3 近代化与传统因子的结合:机制洋纱的最初输入及其影响
近代手工业的起点是近代化机制洋纱与传统手工织布因子的最初结合。棉纺织作为手工业中最为典型的行业,是工业革命变革的先导和19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产业,其原料变革理当成为近代手工业起点的标志。对于中国棉纺织,学界已有了诸多的研究成果①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联经出版社1977年版)等,论文方面更是举不胜举。,但是对于“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起点,学界却受政治史分期的影响,将其定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实际上,19世纪30年代才是“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之前中国棉布曾行销于欧美及东印度群岛,之后则在洋纱的冲击下由输出国转为输入国。
机制洋纱的输入打破了中国区域间产棉不均的瓶颈,不仅促使传统的纺织发生了分离,出现了机制洋纱的机器成份和传统手工织布操作的双重特征,而且无论是从东、中部等较为发达的地区而言,还是从地处偏僻的云贵而论,洋纱对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1851年,在两广客商“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29]的带动下,云贵形成了独特的“洋纱→鸦片”式双向贸易,与东中部棉纺织一样出现了机制成分与手工操作并存的特征。
当然,由于纺机比织机速率高,加之中国存在尚多的闲散劳动力,因而洋纱排挤土纱比洋布排挤土布的效率更高。如在近代云贵手工业中,棉货运销发展最快,棉纱始终占据首位,取代了之前购买川、鄂等省棉料。洋纱作为原料输入,不仅使棉花在云贵进口中“占棉货进口总值之比数量少”[30],而且还促使本来产棉甚少的云南“本省之棉”也“转售外人”,如永昌特产的五色绵和采帛、武定的羊毛布和棉织的宜良布、丽江的氆氇、永昌的斜纹布,以及临安的通海缎和东川的苗锦等等,这些昔日的特产在云南“竞有询其名而不识者”[31]。
洋纱还对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在苗族地区,“由于英国棉纱棉布大量输入,苗族农民衣料多改用洋布”[32]182。德宏的景颇族,原来“都自己植棉纺纱,近几十年来,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棉花的种植很快就绝迹了”[33]63。贵州的水族、苗族、布依族,“他们特别喜欢(兴义所产的)这种结实保暖的大布”[34]18。此外,洋纱的输入还带动了其它手工业与外界的贸易,以及商人之间的频繁往来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如在贵州兴仁,鄂、粤商人“贩运洋棉、湖棉至县出售。迨洋棉衰落,乃经营商务之得擅胜场者厥惟洋纱。纱商多系外省人。”[35]23。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棉纺织遍及全国各地,但由于各区域间差异性较大,因而华南、江南等产棉地区受机制洋纱的冲击极大,而对于产棉甚少的云贵等地而言,机制洋纱的输入无意间还是手工业中的一种资源革命,有益于落后地区手工业在受打击的同时,加强与外界市场的联动和资源的整合。棉纺织是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产业,其“棉纺织品也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商品,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棉纺织品市场上的争夺也尤为突出”[36]156。
虽然早在170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将1116担原棉运入厦门,并以每担5.5两在中国首次成交[37]128-130,但是那仅是原棉输入,而尚未出现近代手工业中的机制洋纱,而且英国所需之原棉也大多源自印度。印度是棉花种植的发源地。16世纪末尼德兰工人移居英国,从而使英国棉纺织得以兴起。但在17世纪中叶英国兰开建立棉纺织工业之前,所需的棉纺织大都源自印度的印花布。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从而开始了机器织布,“使织工在既定的时间里生产的棉花数量是先前的两倍”[38]15。
传统手工业以棉纺织的紧密结合最为典型,因而棉纺织的分离成为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织布业技术提高之后,亟需大量的棉料,继而促使纺纱业也须作相应的改革。基于此,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的“珍妮纺纱机”,时至1770年该纺纱机已从8个纱锭增至16个,1784年更是增至80个,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纺纱的效率。但是,该纺纱机纺出的机纱仅能作织布的纬线,仍不能满足织布机所需的大量棉料,于是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应运而生。水力纺纱机的出现使棉纺织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开创了机制纺纱的新纪元,其纺纱不仅坚韧结实,而且还可用作织布的经线、纬线,从而使机纱大大地取代了传统的亚麻纱。
之后,英国棉纺织更是有了较快的发展,如在1774—1779年间,织工克朗普顿结合珍妮与水力两种纺纱机的优点,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该纺纱机不仅可利用水力纺纱机滚简,而且还可采用多轴纺纱机的前后滑动,使产品不仅坚韧结实、精细均匀,而且在质量方面还胜过手工的印度棉纱,可用作织造平纹细布。时至1825年,英国又出现了罗伯特“自动走锭精纺机”,不仅在质量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还使棉纱产量也大为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棉纺织的变革,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
但是,就英国机制洋纱的销售来看,最初从事棉纺织出口贸易的商人并非英国人。“当时出现了一股外国人定居曼彻斯特的热潮,他们开始从事(棉纺织品)出口贸易,主要面向他们的祖国和所熟悉的其它市场。”[39]5但是,就销量而言,1780年英国棉纱、棉布出口总值不及36万英镑,时至1785年才增至100万英镑以上,1792年又猛增至200万英镑以上,1802年更是猛增至780万英镑以上[40]251。可见,在短短的20余年,出口额就增加了20余倍。
从1820—1840年英国棉纱、棉布的出口对象来看,主要为欧美、非洲,其中欧洲占了一半以上。但是,随着欧美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英国棉纱在欧美的输出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820年的95.66%降至1840年的77.55%[41]92。当时,英国也有少许棉纱、棉布输入中国、日本、爪哇和英属印度群岛,但是从最初英国棉纱、棉布的总体输出情况来看,输入中国、日本、爪哇及英属东印度群岛的分量甚少。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时至19世纪20-30年代,中国开始批量进口英国机制棉纱,打破了之前进口原棉的传统,使近代机制手工品与传统手工操作的双重特征得以出现,开启了英国工业品对华输入的历程。
19世纪30年代之前,由于清政府只设广州为开放口岸,因而中国进口的原棉甚少。1817—1833年间,中国源自西方的产品货值不及东方产品的三分之一[42]292-293。但是,由于一部分中国人已开始使用洋经土纬进行织布生产,因而英国洋纱的销量逐步增加,从1829年进口的50万磅英国洋纱增至1831年的95.5万磅[52]283-284。
可见,机制洋纱代替土纱,作为手工织布的起点应始于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广东的部分地区。但是,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强烈的影响下,时至1832年洋纱贸易已成为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43]102,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但洋纱已成为中国进口洋货中第一位的商品,而且还成为了中国进口增长速度中最快的一种半工业品。当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洋纱输入全国各地的时序有异,因而各地近代手工业的起点略有不同。如地处偏僻的云贵,其传统手工棉纺织就晚于广东等地,直至1851年(咸丰元年)才开启了云贵近代手工业的历程[44]。
综上所述,不仅“工业化”与“近代手工业”有着不同的界标,而且即使是在手工业这一领域,“近代棉纺织”或“近代手工业”的界标也应不同于学界所谓的19世纪70年代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出现,更有别于诸多学者从“政治史”角度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说。相对而言,无论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发展特征而论,还是从近代整个中国手工业的影响面和地处偏僻云贵的波及范围而论,以19世纪30年代和1851年分别作为中国近代手工业和云贵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以及以机制洋纱的输入及其使用作为“近代手工业”的标志事件都是较为合理的。
[1]蔡开松.中国近代史分期标准综述[J].求索,1991(3).
[2]林增平.中国近代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3]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J].历史研究,1954(1).
[4]胡绳.胡绳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王明前.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近代史分期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
[6]许苏民.“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J].河北学刊,2003(2).
[7]晁中辰.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J].河北学刊,2010(6).
[8]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讲义[G]//吕著中国近代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赵庆云.何为“近代”:中国近代史时限问题讨论述评[J].兰州学刊,2015(11).
[10]蒋孟引.世界近代史为什么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5(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2]虞和平.试论中国近代化的概念涵义[J].社会学研究,1991(2).
[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5]吴承明.吴承明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6]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J].历史研究,1956(4).
[17][24]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18]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19]林文勋.纪念李埏先生百年诞辰·主持人发言[J].思想战线,2013(5).
[20]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1]熊元彬.云贵近代手工业曲折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9-19.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49):第1卷[M].上海:三联书店,1957.
[23]李伯重.中国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G]//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5]王翔.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2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27]戴鞍钢.近代贵州土布生产的演变[J].贵州社会科学,1988(4).
[28]彭南生.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29]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第10卷[M]//商业志·概述.安顺市志编委会1983年铅印本.
[30]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第75卷·商业二[M].
[31]刘盛堂.云南地志·物产五·商业[M].1908年复印本.
[32]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
[33]景颇族简史编写组.景颇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34]林兴黔.贵州工业发展史略[M].成都: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8.
[35]贵州省兴仁县史修志委员会.兴仁县补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6]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M].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38]THOMAS ELLISON.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M].Bristol:Thoemmes Press,1968:199.
[39]SYDNEY JOHN CHAPMAN.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M].Bristol:Thoemes Press, 1999.
[40]夏炎德.欧美经济史[M].上海:三联书店,1991.
[41]D.A.FAMIE.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 1815-1896[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
[4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3]M.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sity Press,1951.
[44]熊元彬.机制洋纱引发云贵内外市场联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2-20.
责任编辑 文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6.010
F429
A
1004-0544(2017)06-0054-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14ZDB047);湖南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16YBQ064);湖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项目。
熊元彬(1982—),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硕士生导师。
——传统棉纺织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