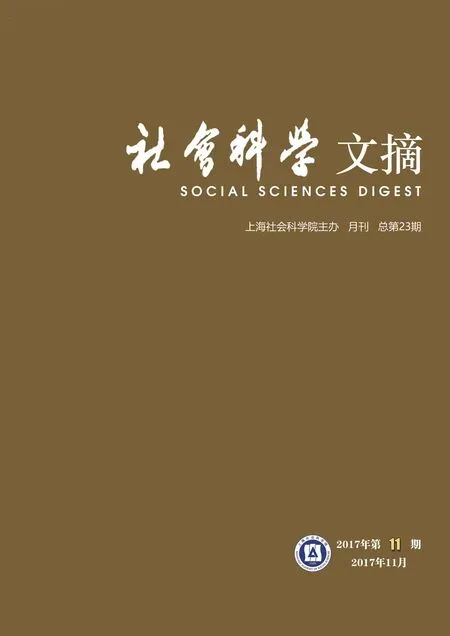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
文/梁晨 任韵竹 王雨前 李中清
分析大学生源构成是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的关键之一。基于民国上海8所院校(国立交通大学、暨南大学;私立大同大学;教会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市立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学籍数据的量化分析发现,若以“从什么地方来”、“从什么家庭来”和“从什么系统来”三个角度衡量,民国上海大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较为同质化,地理来源比较集中。民国上海教育精英的来源与其教育机会的表面开放和社会经济成功的经验不尽相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高等教育中蕴含着的不平等性和社会流动上升渠道狭窄的状况。
家长职业的同质化
统计发现,在所有上海8校中,商人家长比例均高居第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居第二位。这两种职业群体比重之和,除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外,在其他7所大学都超过了一半,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更接近9成。暨南大学在7所大学中相对较低,可能与其招生主要面向华侨和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往福建有关。其他高校基本或主体未离开上海,不管是国立交通大学,还是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等,学生家长职业构成均偏向于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
从动态角度看,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优势是持续的。圣约翰大学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商人家长比例一直最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长之和更高达80%到90%多。大同大学两类职业家长比例之和一直在75%到80%多之间,1947—1949年间,专业技术人员家长比例超过了商人。交通大学商人家长也一直是最有优势的群体,两种职业身份相加,多数年份在70%左右。不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和1947两年,两种职业的家长比例一度下降到不足6成,而以“农”为业的学生家长从5%左右增加到16%左右。通过家庭住址分析,这或与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上海,江浙地区学生进入上海高校有关。
作为上海中上阶层的主体,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优势当与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有关。对照19世纪20年代末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城市大学生的年花费,“大学教育是需要经济的”,不仅上海的一般产业工人家庭无法承受,即便是小康之家,培养出一名大学生也非常吃力。上海的大学教育费用还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高额的经济成本成为民国上海大学的一道隐形门槛,把缺少足够经济条件支持的家庭子弟排挤在外。
此外,由于教会大学不仅收费高于公立和一般私立大学,外语氛围或要求也更高,这使得其学生来源更向商人家庭集中。而相比较于其他城市高校,上海大学中的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更高。
家庭地理来源的本地化
以籍贯衡量,8所院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以江浙为中心的东部沿海省区;但若以家庭地址来衡量,绝大部分学生来自上海本地。以材料规模较大、时间连续性较好的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三所大学为例,三校学生籍贯以江苏、浙江两省为多,上海本地并不显著。但若以家庭地址来衡量,三所大学的上海学生比重几乎都呈现出10倍左右的增长。大同大学从8.7%增加到86%,圣约翰大学从5.5%增加到52.1%,交通大学从3.22%增加到40%。
从动态角度看,上海大学生以江浙沪为主的地区性特点一直存在且较稳定。三地生源中,大同大学一般占9成左右,交通大学在7成以上,圣约翰大学在6成左右波动,地区优势也十分明显。全面抗战爆发后,各高校江浙沪生源有了一定下降,这可能与其他地区人口涌进上海尤其是租界有关,但这种下降程度有限,并没有影响到江浙沪的优势地位。而从1944年开始,这一下降趋势停止,江浙沪学生所占比例又逐步升高。
从比较角度看,上海高校的学生地理来源也较集中。如作为上海高校中学生地理来源范围最广泛的国立交通大学,学生多集中于上海及附近江浙地区,中山大学基本以广东为生源基地,但清华大学学生来源全国化趋势明显,江苏、平津、浙江、山东以及湖南、四川等比例都较高。据此推测,民国高校中可能只有清华大学以及暂缺数据的北京大学等具有广泛的全国性影响,其他高校主要是区域性或本地化的。就上海而言,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沪上名校基本是地区性的高校,大同大学等私立大学则是本地性的高校,主要培养的是本地社会精英的后代。
上海高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于本地和周边地区可能与民国时期大学招生通常是由学校而非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安排有关。学校组织招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点设置有限,通常只限于学校驻地或极有限的少数大城市。如上海交通大学1922年首次招生时,考点设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汉口五市,而1931—1937年间,招生考点减少到上海、北平、广州和武昌四地。检索《申报》记载的上海其他各主要高校招生简章,除东吴法学院因文、理科在苏州,部分年份在上海和苏州两地同时招生外,圣约翰大学与大同大学等校一般均只在上海本地招考新生。限于民国时期的交通状况、信息传播渠道等,考点设置在有限的大都市中,显然提升了远离大学和大都市青年的投考成本和难度。而若进入战争动荡时期,这种地理阻隔更难以逾越,外地生源更受限制。
其次,上海本地更为商业化的氛围和浓厚的消费文化形成的高成本,也可能进一步抑制了包括国立大学在内的上海各类大学的外地学生来源。或是“居大不易”的缘故,民国上海大学生的年均花费要高于外地不少。生活成本高和私立高校多的现实对各地学生,尤其是广大农村学生的就学选择形成了影响。
最后,私立大学学生来源的本地化程度极高,可能主要和民国私立大学的经济状况和办学水平有关。私立大学往往经费有限,经济状况不佳。如开办初期的大同大学,“在物质上毫无凭藉,校舍是租赁的,校具是杂凑的,书籍仪器是少得可怜的”。1932年,教育部调查上海6所大学,其中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4所私立大学,不是“收支不能相抵”,就是“年有积欠”或“欠债颇多”,相较于教会沪江大学,其经费“均极感困难”。私立大学不仅“全赖学生缴费为收入之大宗者”,而且“收费之惊人”,“明目与手段之精明”,“较教会立者为尤甚”。尽管收费不菲,但私立大学的师资、设备以及社会认可度却往往不如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对外地学生的吸引力也自然有限。为了竞争生源,私立大学如大同大学尽管只能在上海招考学生,但它会在招生季密集安排数次甚至十数次考试,以便学生“随到随考”,同时还要设置比国立大学低的招生标准,在提高入学经济门槛的同时降低智力门槛。这些都会影响私立大学的声誉度或吸引力,从而更多吸纳的是本地有条件但进入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等名校无望家庭的子女。
来源中学的封闭化
中学是大学生源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大学生社会来源结构形成的前因与关键,对来源中学信息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国上海大学生的结构特征。交通大学有一小部分学生虽然家庭地址不在上海,但中学却就读于上海。尽管上海家庭和上海中学的比例都没有达到一半,但江浙沪相加的比例却在7成左右,可看成是倾向于本地的地区性大学。圣约翰大学尽管只有一半略多的学生家庭地址在上海,但却有超过85%的学生毕业于上海本地中学,本地化特征大为加强。大同大学学生中来自于上海中学的比例与来自上海家庭的比例都超过8成,是完全的本地化。这种情况在三所大学基本是持续的。只有交通大学可能因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外地学校学生,上海学校输送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江浙和四川等中学毕业生增多,但上海学校仍是输送学生最多的,江浙沪相加,仍旧占据多数。来源中学的分析说明,除了上海本地家庭外,就读于本地中学也可以显著提高学生进入上海大学的几率,但这对非本地家庭的子弟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看似开放的招生规定背后,隐藏着很高的门槛。
所有8所大学学生的来源中学中,有42所各自提供了超过100名学生。分析发现,这42所中学为上海大学提供了超过一半的生源,其中只有6所不在上海,占14.3%。这6所中学中有5所位于江苏,1所位于浙江,都非常靠近上海。这些中学对上海大学生的来源结构影响巨大,而它们的地理分布则非常集中。
来源中学本地化倾向的背后至少暗含了民国中小学教育体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大学常设有“附属”或合作中小学,“系统内”的学生往往享有各类优先或免试录取的待遇;二是民国上海中小学教育水平领先全国,外埠学生在考取上海大学时难以与上海学生竞争。
民国大学多办有附属中、小学,或者与一些特定中学合作。附属学校不仅在地理和管理上与主管大学成为一体,更由于“直升”、“保送”制度,在生源上也成为了一体。这使得大学人才的选拔关口实际上被前置到了中小学招生,也进一步提升了民国上海大学的入学门槛和本地化趋势。而教会大学,为了保证学生质量和兼顾本教会传教人员子女的教育,除直接建立附属中学外,还会和一些英语教学水平较高的教会中学建立合作关系,保送优秀毕业生到教会大学就读。这些举措,在导致上海大学生源多来自本地中学的同时,也促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来源中学的性质结构有所区别。教会大学学生更多来自教会中学,国立大学更多来自国立中学等。
作为大都市,民国上海的中小学教育也优于外埠,有一批管理严格、教学水平高的学校,且即便不是附属中学,不少沪上名校也常与各大学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能力将毕业生送入大学校门。上海高升学率的著名中学在成为晋阶大学通途的同时,既巩固了本地学生在大学招生中的竞争优势和大学校园中的比例,也成了稀缺性社会资源而逐渐被社会中上阶层所垄断。这些中学学额有限、学费不菲,其生源不仅本地化,而且普遍来自商人、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社会群体家庭。城市里的工人、农民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进入这些贵族学校,甚至收费低廉的私塾也读不起,通过教育实现向上升迁对他们只是奢望。贵族化的学校和教育契合了商业化环境中大学的需要,一些中学的高升学率实际可能成为了城市社会中上阶层控制流动的工具。
余论
从家长职业到地理分布,再到毕业中学,民国上海大学生群体封闭化和同质化趋向愈发明显。概言之,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在民国上海大学中具有明显优势,在数量众多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中更是垄断群体。上海大学生的籍贯虽以江、浙两省为主,但主体却是上海居民,且大部分在上海读中学。社会中下层与纯粹的“外埠人”在上海的大学中并不常见。
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起始地,上海是开放的机遇中心和现代精英的摇篮。教育是最重要的新机遇之一,学生通过大学教育得以步入新职业领域,成为引领近代化的精英。然而,这些新机遇的开放度可能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与近代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增强,看起来并不一致但实则是一体之两面。有学者注意到,近代以来,随着大量破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新兴产业工人,一部分传统富有阶级,如官僚和地主投资工商业,成为新兴资本家以及新式学校的开办者,大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大为加强了,同时阶层的分化也大为加剧了。城市内的阶层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方式发生了转变。职业化或新式职业群体的出现改变了科举体系下“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选择,社会中上层的来源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城市人口总体异质性增大,但经济文化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布以及如教育等重要资源在地域和城乡中的分布极不均衡等也造成社会阶层间的分化大为加剧,中上阶层出现了自给自足或封闭的趋向,新的阶层固化或资源垄断在迅速形成。
具体到民国上海高校的学生来源上,由于民国政府教育投入的匮乏和对教育资源掌控、布局能力的缺失,民国大学在经济上非常依赖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与有产阶级,在地理分布上则主要集中于城市,这不仅导致了教育体系中学校布局与教育水平的区域不平等和公私立学校的结构不平衡,更导致了大学教育成本高昂,使得本已非常严重的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渗入到教育领域。因此,尽管上海地区大学的招生在理论上是面向各地和各阶层的,但学生的实际来源呈现出区域性甚至本地化的特征。几乎只有具有较高资产支持和有限地区的家庭能够负担起上海各大学的高昂学费,将子女送入大学。教育的社会流动性作用并不乐观,大学教育绝非普通人成功的阶梯。
民国上海大学生来源状况或教育精英的形成机制,还能为更深入的思考提供研究的起点和后续空间。晚清近代以来部分江南精英家族出现了由仕途转向工商业、从“谋官”转向“谋财”、从“绅士”转向“商人或专业技术人员”的现象,他们在自己进入城市的同时也把子女带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完成了家族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这一转化改变了过往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以及支持家乡办学以保持家族社会经济地位的模式,反映了社会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带来的阶层流动机制的改变和精英阶层因势调整社会分层策略的可能。对中国精英家族或有条件家庭来说,这种策略是开放或可选择的,不同家族甚至同一家族内部不同家庭的选择并不相同,不同地区和职业背景的家族对子女接受新教育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预示了传统精英家族群体内部的分化与变迁。社会精英作为“有组织的少数”,在社会变迁与演进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因此,对这些选择的系统研究很可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新理解,有待学者们继续深入挖掘。
另外,上海虽然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奇迹和近代化的标兵,但这里既存在李欧梵笔下的“摩登”,繁华与现代,也存在卢汉超展示的“霓虹灯外”的落后与贫困。同时,上海既有经济文化上全方位开放、活力四射的一面,但也有本研究揭示出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存在的本地化的封闭倾向。由此而论,民国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和国际化的样本,在成为“高峰”的同时,会不会也变成为一座“孤峰”?民国上海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很多方面,完全高于其他地区,但在形成所谓国际化、近代化系统的同时,会不会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封闭化?如果自身发展的经验与成果无法向周边辐射或传递,国际化了的上海,只有地区性的精英教育和本地化的精英来源,这无疑会加剧城市间发展的断裂和城市本身发展活力的匮乏。就此而言,上海城市史以及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城乡关系史研究还有很多新的空间值得开拓,尚有许多新的问题值得发现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