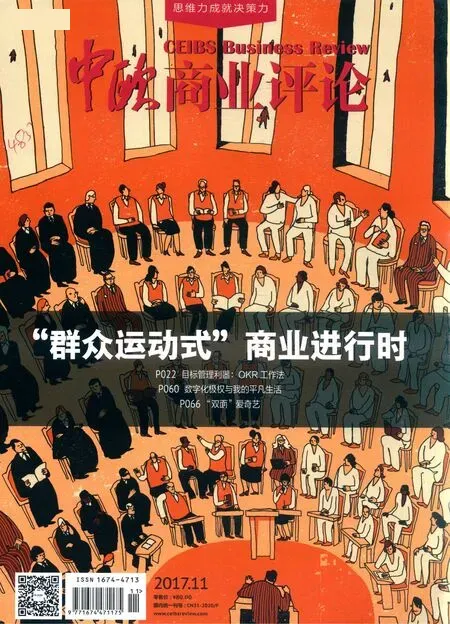创建“美丽新世界”的商业运动
文/汪洋
创建“美丽新世界”的商业运动
文/汪洋
以用户急速扩张为基础的商业,都有着某种社会群体运动的特征。
在许知远抛出“为何创业”这个问题后,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回答道,年过四十,感觉到日子是倒着数的;然后,他两眼发光地说,“半年之内成为一百亿美元估值的公司,这机会肯定存在,是因为我傻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守着这摊小生意在这儿做着……可是创业,上面有无穷层次,做生意完全是一条不归路……人最怕做无望的事情,自我提升其实就是没有进度条。”
其旗下的“得到App”估值尽管目前预计约为70亿元人民币,在罗振宇看来,这大概还是他嘴里的小生意。
一个急速变动中的大时代
马东说许知远“像是个古代人”。我们可以将作为“知识分子”的许知远视为已经过去社会运动的余波震荡后的产物,他们的情怀脱胎于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既对能扭曲公众心智的人心怀警惕,又不无羡慕。他和罗振宇的对谈,成为两个扭曲力场者的角抵。
按罗振宇判断,这显然是一个急速变动中的“大时代”。商业世界中的风起云涌确实也让人目不暇接,公司批量出现,其兴也勃,其亡也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下中国商业舞台上演出的就是一场“社会运动”,因为商业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影响到亿兆众生,并产生了如此多阶层逆袭的商业明星。
打开电脑、手机,马云做什么了,说了什么,无所不在,商业人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而这场以商业为主题的社会运动,显著地发生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时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龚焱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底层代码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个是传统经济旧世界逻辑,一个是新经济新世界逻辑。他说:“传统经济是基于对资源的加工,其底层估值是现金流逻辑。从收入开始到利润结束,最关键的测度指标是现金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另外一套逻辑体系,也就是新经济估值逻辑体系。底层代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是基于对知识和信息的加工。与传统资源的本质区别在于,知识和信息受两大规律约束:一是信息规则,二是网络效应。基于这两大规律,整个新经济的底层估值不再基于现金流,而是基于用户。今天评估新模式,人们会使用PV、UV、日活、月活、时长等一套全新的代码。”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以用户急速扩张为基础的商业,都有着某种社会群体运动的特征。创业者们以传统的现金流思维来处理商业现实,有可能会错失好局。比如易到用车的创始人周航,这个以“优雅和理性”为标签的企业家,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网约车公司,从风光一时,到黯然出局,也不过数年时间。
“叙事”改变世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导论》中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组成世界的事实,其实就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人们被连接(也可以说是被裹挟)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运动着的人群里,就像一滴滴海水之于大海,你或属于某个规模的浪,或在浪头,或在浪底,或看着某些规模不一的浪从眼前移过,既在局外,又被它波及。
如果以事实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不仅仅以事物的角度看待世界,那么世界就变得不那么坚实,改变世界的常常就只是一个重新构建的关于未来的叙事,如罗振宇口中的“某个他不知道的计划”。被群嘲的“贾跃亭的PPT”,也一度被众人狂热地相信,水滴就变成了洪流。《纽约时报》曾揶揄埃隆·马斯克“有扭曲现实力场的超能力”,与乔布斯为一路货色。弦外之音则是,他们在利用公众的心智不成熟以谋求某种利益。
在中国,也不乏场域不等的各种“商业教主”。马云曾在某次对网商们的演讲中说,经济学家的知识是关于过去的总结,而企业家们看到的是未来。虽然经济学家们不见得接受这样的说法,但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如今一个中等规模跨国企业积攒的财富,常常让一个中世纪国家望尘莫及。近200年来,人类走出了上千年的经济停滞,原因是人们发现了金融的秘密,即经济发展建立在人们都相信“未来会更好”的基础上,才有了拆借、融资以及将主要利润投入扩大生产等行为。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曾经比较过自己和马云的区别,“我们俩的区别就是盲目自信的区别,马云如此的盲目自信,以至于盲目自信自己的东西变成了现实。”
“我考了三年高考,考的是北大本科,他考的是杭州师范的专科,不光看到了长相的差别,还看到了智商的差别。我常常喜欢开一个玩笑,马云和我都是做外语培训起家的,几乎同时开了外语培训班,我一下开成了,从第一个班13个学生,第三年有5000个学生。马云开了三年,三年以后,他第一个班招了20人,第三年还是20人,没干成,只能想办法干别的,所以就干成阿里巴巴。马云不光一个公司没干成,第一个外语培训没干成,跟外经贸部合作没干成,最后实在绝望,跑到杭州拉了一帮人干阿里巴巴,用人不在于多,而在于质量,我5000多学生没有一个成为我的合伙人,马云20个学生,有18个罗汉。”
另一个关于相信的例子,则是史蒂夫·扎福(Steve Zaffron) 和 戴 夫· 洛 根(Dave Logan)所认为的,“一个企业倒闭之前数年,早就在组织成员的潜意识中死掉了,尽管谁也不想这一天真会发生”。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十分认同这个观点。马云也曾说:“大家说我擅忽悠……我忽悠得很成功,点燃了很多人心中的火焰,我会一直忽悠下去。”
“历史是畸零人创造的”
俞敏洪曾经这样开玩笑:“马云自己讲的笑话,他进了杭州师范学院很自卑,但是只自卑了一瞬间就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必须把专科变成本科,第二个目标是必须变成校学生会主席,还变成了整个浙江省学生会主席,第三个,必须跟杭州师范学院的校花谈一场恋爱。这三个目标对于我来说比登天还难,我要进了杭州师范学院乖乖毕业最后到农村当老师。但是马云毕业的时候,三个目标全部超期待的实现,不光谈恋爱,而且还把人家娶回家。我在北大除了读书以外,一无是处,两件事情从来没干成,第一,没参加任何学生活动,第二,没有谈恋爱。这是内心恐惧而来的,作为有深刻自卑的农村孩子,我是这么想的,反正也是失败,被人知道了我还丢面子,那老子还不如不竞选。我谈恋爱一定会被女孩子拒绝,拒绝会更加没面子,老子还不如不谈,谁也不知道我到底想不想谈,其实心里真的很想谈。”
这段话看似打诨插科其实信息量颇为丰富。美国传奇思想家埃里克·霍弗在数十年流浪生涯中,在一处流动失业散工收容所里顿悟到“历史是畸零人创造的”。畸零人不是某个身份标签,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认知,带有失意者、边缘人和多余人的意思。可以这么推导,畸零人创造了社会浪潮,浪潮组成了历史。
他在收容所里突然发现,自己和所里其他人都属于同一类型——社会不需要的人,“我们大部分都不能忍受单调、无意义的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徒步经过一片不毛之地,得到答案。他想到,如果让收容所里的那些人来这里拓荒的话,每个人都可能很高兴。“拓荒者不就是一些畸零人吗?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成为忙碌的实行家……而一旦尝试过有所建树的滋味,他们又想建树更多的东西。”这个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在码头搬砖,尽管后来声誉鹊起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研究员,仍然没有离开码头的思想家说。

读书时候的俞敏洪一次次走过北大图书馆的时候,应该没有意识到,他当年的那份自卑或者说失意感,与他后来的事业不无关系。再说,马云的自卑感比他更加强烈,所以对改变的向往更为焦渴,以至于产生了一种俞敏洪眼中导致马云成功的“盲目自信”。
必须再次强调,畸零人不是一种社会身份,而是对自我个体和社会关系的体认,并带有一种强烈的失意感。失意感带来了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要么自建社群,要么“忘我”地投入剧烈的社群运动,将自己掩埋在运动的人群里,以忘记由“渺小自我”所带来的不适感。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人是一条肮脏的河流,为了接纳这条河流,人必须成为大海。而这样的结果,又如社会学家约翰·帕吉特和沃尔特·鲍威尔曾指出的,“短期看来,行动者创造连接,长期看来,连接创造了行动者。”
所有的运动对人们来说都是追求改变的工具。集体情绪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以致创造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实。在霍弗看来,各种运动都是热情的发电厂,对于运动来说,热情又是不可缺少的燃料。
那些不假思索投入变革运动的人,也常常觉得自己因这场运动而具有了无敌力量。美国的硅谷神童们何尝不是这样,以“砸烂枷锁,就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热情来做事。谷歌要“管理全世界的信息”,扎克伯格则要“用技术互联全世界的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魏炜教授认为:“这类指数型企业与其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仅仅是交易层面上的,更多基于价值观和文化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种价值观和文化的交流正是上古时期,将人类由散居小村落连接成巨大的部落联盟的理由,也是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想说的,智人因为有了描述非眼前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讲故事的能力,而使得智人进行更大规模的组织协作,以势不可挡的群力爬上了食物链顶端。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
然而,我们眼前的现实又如同一道道布满了裂缝的玻璃墙。在人类历史上,商业运动第一次以文明的方式宣泄着巨大能量,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