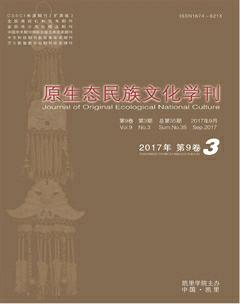湘西老司城联合村灯戏考察
田茂军+邱俊宁
摘 要: 老司城联合村灯戏是当地传统戏曲剧种之一,过去又叫“转转戏”,是老司城及周边土家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作和传承的一种民间小戏。演出剧目只有13个,表演具有浓郁的草根特色和娱乐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变迁,灯戏面临着传承断代的危机。
关键词: 联合村灯戏;历史源流;草根特色;传承断代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7)03-0147-06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集聚区,其联合村是属于吊井乡的一个村寨,与世界文化遗址老司城村接壤。联合村的灯戏作为戏曲剧种之一,根据实地采访老艺人和查阅有关资料,可知这里的灯戏可能是当地民间产生较早的一种曲艺。联合村灯戏由来已久,相传在改土归流前后盛行。永顺县联合村灯戏是湘西土家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作和传承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孕育在民间,生长在民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浸透着土家人民丰富的情感和愿望表达,在下层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块活化石,使戏曲文化从抽象的精神领域回落到了现实世界。正如刘祯所言“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最常态的表演和范式”[1]。联合村灯戏作为民间小戏的一种,它原始古朴,内容丰富,在道具、服装、行当和声腔等方面都较为简单,但是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其艺术表演特色主要表现在教化性、草根性、趣味性等几个方面。
一、联合村灯戏的源流
永顺县隶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土家族的发源地及世界文化遗址——老司城的所在地。当地人口绝大部分是土家族后裔,有着其独特的土家族传统文化特色。同时永顺县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可谓是“咽喉”地带。正因于此,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使得这里留下了诸多的文化瑰宝,比如摆手舞、哭嫁歌、毛古斯、打溜子、土家山歌、梯玛歌、傩戏、阳戏等等,灯戏就是这些文化样式中的一个小品种。
联合村是永顺县吊井乡所管辖的一个村落,这里紧靠老司城村,人口分布主要以土家族为主。联合村顾名思义,是几个村子联合而成的一个新的行政村落,它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惹巴枯、泽巴郎、龙沙湖和钱家湾四个自然村寨(小组)联合而成。惹巴枯是四个村落小组的交汇点,处于永顺县城去老司城的交通道路边,目前灯戏就是在这里传承。
灯戏是民间小戏的一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到联合村的灯戏由来已久,据灯戏团长向顺龙介绍,在土司王统治时期,就有了灯戏的存在,他们向家的祖先就是给土司王唱戏的,可知灯戏能传承并发展到今天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相传当时的灯戏主要是为土司王表演,并且出现在重大喜事的庆祝活动中。也正是因为彭氏土司高度重视土家族传统曲艺这一艺术, 使得灯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土家族人民的族群或民族认同感。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灯戏艺术在老司城这一带有着老司村灯戏和联合村灯戏之分,只是各地的叫法和表演形式稍有差异,后面老司城灯戏被联合村的灯戏所取代。我们还从采访对象的口中了解到联合村灯戏的前身叫“转转戏”,是百姓晚饭后因为没有其他的活动形式,于是自己就在屋里围绕着自家的火坑转,在围转的过程中,附带有相关的简单唱白,于是叫“转转戏”。后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与受到阳戏、汉戏等大剧种的影响,当地居民就在转转戏的基础上,丰富了唱白的内容,穿戴相关的服装,还配上了锣、鼓、钵、二胡、京胡、唢呐、笛子等乐器,从而形成了联合村灯戏这一艺术形式,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结晶。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传统、优秀的联合村灯戏艺术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断层现象。一次是在1958年的时候,另一次是在1971年以后。2014年老司城为了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村灯戏作为一种集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于一身的曲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着广大群众的心声,仍然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民间审美意识与整个民间文化长期保存着一种交织互叠、浑然一体的关系。因此,民间审美意识的各个方面——审美观念、审美意识、审美标准、审美情感、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等等……都由于这种关系,而与民间大文化背景下的功利价值准则和追求相关联”[2]。
二、联合村灯戏的基本内容与特色
湘西自古就是巫儺文化的摇篮。当神奇的巫傩绝技、神秘的咒语与神意灵动的歌舞相结合,便具有了神奇的艺术魔力。湘西地区的民间艺人在本土巫傩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和借鉴汉文化的因子,创造出了具有湘西特色的灯戏、傩戏、阳戏等。那么,联合村灯戏就是灯戏中的一个元素。谭达先在《中国民间戏剧研究》中说到:“与农村的民间舞蹈乃至劳动动作有密切联系,直至近代仍有不少民间小戏没有较为固定的表演程式,但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载歌载舞、兼重唱做的特性。”[3]联合村灯戏为湘西民间的小戏剧种之一,由本土民间歌舞结合汉族的阳戏元素综合发展而成。联合村灯戏孕育成长于民间,以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为后盾,记录着人民对生命价值的批判以及伦理道德取向,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由此可观本土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研究土司城社会和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我们调查到的联合村灯戏,共有大小剧目13出,由正戏和闹台戏两部分组成。正戏有12出,闹台戏1出。正戏是正式演出的剧目,主要反映民间俗事、劳动生活、男女爱情、神鬼妖狐等内容。闹台戏是演出之前营造氛围的,只有很短的时间。正戏剧目是:《二仙姑下凡》《三女婿拜寿》《李子英下科》《彩楼会》《天台会》《谢文清耕田》《安安送米》《双龙双凤》《秦雪梅观花》《王英武不孝》《山伯访友》《天官赐福》。闹台戏只有一个:《贾瞎子算命》。下面进行具体介绍。
(一)以感人的故事情节, 表现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在联合村灯戏的十几种剧目中,有不少劝人行孝、积善积德和酬神还愿的剧目。如《王英武不孝》《安安送米》等。《安安送米》这一剧目,它直接取材于《二十四孝》,在这一剧目中一共由六场组成。它从正面的角度来描述了安安经过千辛万苦,为因误解被赶出家门的母亲旁三春送钱粮的感人故事。剧目本身通过安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旗帜鲜明地宣扬了“孝”作为传统美德之一,它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此外,另一剧目《王英武不孝》则不然,它是从反面角度描述了王英武把双亲赶出家门的故事。通过这样一个反面的事例来告诫人们要懂得“孝道”和提倡“孝道”,并且要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及时行孝。endprint
在联合村灯戏的这两个剧目中,不论是从正面角度出发还是从反面角度刻画,它们的共性都是在主题上颂扬了以“孝治天下”的道德规范。人们通过这些特定的曲艺体验与观赏,强化着以忠孝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的宗族制度。而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族群中,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形成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并一直经久不衰地流传下去。
(二)以滑稽的表演,表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
联合村的灯戏长期深深地根植在民间,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是民众表达愿望的最好手段,正是这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历史造就出这独特的民族艺术。联合村的灯戏内容丰富,其中有对封建专制思想和等级制度的批判,有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积极反抗,有对善的颂扬,对恶的鞭挞,有对权贵的嘲讽,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如《李子英下科》, 小戏中的主人公李子英因家境清贫,唯一的愿望是希望能考中功名后回家好好孝敬父母,但不幸的是李子英在去京城赶考的路上遇到一山中大王并将他捆绑在树上,而后被山大王的妹妹所解救。尽管李子英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了性命,但他离考取功名的这条道路越来越远。正是这样的一台小戏,在主题上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动乱,反映了青年反压迫的强烈愿望,使之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现实意义。又如《贾瞎子算命》,借贾瞎子给一对母女算命的现象,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怪诞,也反映出人民生活的艰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极富人民性。
(三)以曲折的情节,表现了人民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联合村的灯戏中,有反映男女渴望爱情美满、婚姻自由的剧目。如最典型的是《天台会》,全剧主要以两男两女用对唱的形式来了解对方、认识对方,最后结为夫妻的故事。这台小戏,打破了当时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的封建婚姻的传统,表现出下层民众的婚姻观念和对自由婚姻的追求。
又如《彩楼会》取材于历史上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在剧目中,薛平贵家境贫寒,从小父母双亡,只能靠乞讨求生。有一天他误入王府花园,并在花园里休息,被正在赏花的王宝钏看见,两人一见钟情,定下誓言要结为夫妻。但由于当时门第等级森严,他们的爱情变得异常的渺小,这时王宝钏就决定用抛绣球的方式嫁与薛平贵。不料,全剧以宝钏在抛绣球的过程中被一乞丐抢走而结束。全剧从薛平贵的不幸命运开始,以薛平贵和王宝钏的爱情因门第森严而受到了阻碍。从中可以看出剧目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反映出他们敢于追求的性格,并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追求。
联合村灯戏这一艺术缘于生活,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所反映的内容,大多都取材于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点滴,可谓是一部下层民众的生活史。
三、 联合村灯戏的艺术价值与功能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特性,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4]也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功能,联合村灯戏也是这样。作为湘西民间艺术的一种存在,它在演出与传承中,老艺人们为满足观众与自身的需要,创作和传承的特定文化,使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色。总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化性
就一般的歌舞表演艺术或其他形式的艺术而言,寓教于乐、雅俗共赏是其共有的特征,使观看者在表演艺术中体会到艺术带来眼观上或是心灵上的一种唯美与教育。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 “我们要丰富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娱乐主义、个人主义,乃是求人格的尽量发挥,自我的充分表现,以促进人类人格上的进化。”[5]联合村灯戏尤为突出的是它的教化性特色。
灯戏特别注重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强调孝道。首先是它的角色定位,大多是姑嫂婆媳,男角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不过是读书人、公子之类,女主角不过是小家碧玉、小姐之列。几乎没有仕宦公卿、公子王孙、名媛闺阁等上流社会人物。这些角色几乎全是下层劳动人民,都属于小人物系列,在表演的戏中就是以他们为人物形象,所表现的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其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喜怒哀乐,所表现出的道德价值观念就是尊重老人,孝顺老人。如《谢文清耕田》中的主人公谢文清和他的小媳妇杨秀英。《安安送米》中的主人公姜安安和他的父亲姜师、母亲旁三春及婆婆。《李子英下科》中的李子英。《王英武不孝》中的王英武等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物,都是凡夫俗子,但是善良、忍让,饱受磨难,最后得到福报。好像就在观众身边,与观众擦肩对话,朝夕相见。正是因为这样,观众不仅不觉得陌生,反而感到亲切,平易近人,適合百姓口味,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迎合观众的内心世界,从而引发他们的共鸣。
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便于观众接受,灯戏的表演语言,均采用本地方言口语,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无论是在说唱上,还是在对白上,他们的戏剧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同时插入大量的谚语、俗语、歇后语,使其极具地方性、亲和性和口语化,观众在观看或听的过程中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容易引起共鸣。“方言土语有地域的限制,即只能为一方民众所熟悉,多用方言土语,虽会影响剧作的流传,但对于当地的观众来说,因是用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土语来演唱,便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因而能受到当地观众的喜欢”[6]。如在《谢文清耕田》中有这样一段对白:“旦白:‘哎!佬佬嘴巴乖。生白:‘看我还上他当,待我也跪在这里,米得人叫一声干爹,我也不起来。”在这样简短的对白中,其中的“佬佬”“米得”就是本土方言的使用,它们分别是“弟弟”和“没有”的意思。又如在《彩楼会》中有这样一个对白:“旦:‘这蓬是芙蓉,开得大不同,风吹荷叶飘飘动,这是叶叶儿红。”此句中的“蓬”也是方言的使用,它的意思就是“一棵”,“这蓬芙蓉”它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棵芙蓉”。可见,在联合村灯戏中,使用方言的情况并不少见,也正是这一元素的加入,使得灯戏在语言上更加通俗易懂和易于接受。
(二)趣味性
联合村灯戏具有趣味性是指它在表演过程中有幽默诙谐、风趣滑稽的特点,常常使人忍俊不禁。这种乐感气氛首先表现在戏剧语言的运用上,如在《贾瞎子算命》中有这样一段话:“丑白:‘一股牛尿骚,好像猪草味,这茶我不要,你们吃。”虽然这独白很简短,但它用语十分贴切,比喻十分形象、俏皮,使得整个舞台妙趣横生。又如这个剧目中的算命先生唱道:“大姐你是听(个长),甲辰年生下命,单怕四月初八生,生你那时好得很,就是有点克父亲,生你那年七月闰,要做九个志儿排生庚。八字好得很,根基稳,莫大的树,头大的根,不怕风吹来动摇,不怕大水来洗根,五行八字都排定,看你婚姻和子心,先开花后结果,五个儿女不差半分,你夫君必有亲相命,姑娘恭喜你,一品正夫人……”这些当地土话的巧妙运用,把一个算命先生活生生地勾画了出来,并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也为这个没有真本事的算命先生出尽洋相而大笑不止。这个戏里的“对白”同样风趣幽默。endprint
除语言外,联合村灯戏的趣味性还大量表现在戏中某些情节和细节的处理上。同样是在《贾瞎子算命》中,一对母女知道算命先生算得不准确,于是就先命令丫鬟给算命先生倒上一杯熱茶,谁知是一杯牛尿,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知,算命先生最终被别人算计了,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
此外,角色的安排上也体现了联合村灯戏的趣味性。在联合村灯戏的13个剧目中,大多有丑角这一角色的安排,灯戏里的小丑种类很多,但多属心地善良、幽默、滑稽类的男性。由于他们极力的夸张滑稽的表演动作,往往会使得丑角戏在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诚然,这便加强了戏剧的趣味性。如《贾瞎子算命》中的算命先生,《李子英下科》中的安童,《王英武不孝》中的王英武和《山伯访友》中的十九就是此类人物。这些角色的出现,增添了联合村灯戏的趣味性。
(三)草根性
草根性即平民化、大众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立性,使文艺作品体现出了真正的“雅俗共赏”之特点。灯戏剧目取材上多具有草根性的特点,13个剧目中,没有涉及治国安邦、为民除害之类的大题材,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嫌贫爱富、婆媳纠葛、婚姻爱情等下层平民的生活琐事,很接地气,全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平凡故事。这些人和事仿佛就是他们自己,好像是对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所表达的就是他们的情感愿望。联合村灯戏的草根性,主要表现在灯戏的演出过程中,表演者动作的简单化。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动作大多以走动为主,并没有其他戏剧艺术的繁杂,正因这一因子的存在,不得不使联合村灯戏添上了浓烈的泥土气息,通俗易懂的表演形式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联合村灯戏的草根性还表现在表演角色的构成。灯戏角色一般都是草根人物,属于“小人物”。在联合村的灯戏中,早期为“二小戏”(小丑和小旦)或“三小戏”(小丑、小旦和小生),后来慢慢地发展为“多行当戏”,那么它就会有其他角色的加入。通过我们的现场调研得知,在联合村灯戏中的剧目《安安送米》《三女拜寿》和《双龙双凤》中,演出人员达到8个左右。尽管这样,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性,在内容上都是小故事和小情节的“小人物”戏。诚然,它们在戏剧整体组合方面是小规模的,因此就构成了灯戏整个表现形态的简单、灵活。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灯戏的表演可以因地设场,可以不受场地条件的限制,它可以随时随地表演,正是这种简约的形态组合,使灯戏的草根性更加突出。
四、联合村灯戏的传承现状
联合村灯戏作为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到今天至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其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与本民族间的其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傅谨说:“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的背后,可能正蕴含着人类应对各种各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挑战的特殊策略,蕴含着人类某些特殊的生存智慧。”[7]联合村灯戏作为地方文化现象的组成要素之一,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随着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而变迁。面对目前经济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常生活的缺场与生活空间的消散。联合村灯戏艺术和许多非物质文化一样,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挖掘抢救和研究已是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下面就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一)传承人的断代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今天,在网络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冲击打破了以往安土重迁的观念。我们在与联合村灯戏剧组的交谈过程中得知,目前他们这个剧组一共由17位成员组成,其中男性占11位,女性占6位,剧团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其中团长向顺龙老人还向我们透露其中有一位成员的年龄已高达79岁。通过这一信息就可以知道,联合村灯戏团队是一个老年团队,没有一种利益的驱动来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出外打工,甚至在外地定居,几乎是重大节日才回家一次,甚至有的年轻人只有过年才回家几天,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年轻人就极少有机会与长辈交流,更不用说耳濡目染地学习灯戏。同时,灯戏的学习传承需要长期的积累,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学会的。剧团成员还告诉我们,现在要想找到一个先天嗓音不错,又对灯戏感兴趣并且愿意学习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这无疑对灯戏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观众群体的减少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得到了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也空前的丰富。现代传媒的发展,网络媒体的普及,无疑给人们的生活催生了多元化、多形式和多选择的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新兴媒体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娱乐选择。诚然,传统的联合村灯戏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并且出现了越来越被边缘化的趋势,生活在联合村的年轻人对本地戏曲感兴趣的并不多。通过采访观察我们可以知道喜欢观看灯戏的群体集中在中年老一辈中,并且主要以老年群体为主。当地的小孩和年轻人更倾向于观看现代性的流行节目。面对这一现状,联合村灯戏的观众群体日益减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也带来文化空间多元化的消失。
(三)资金运转的困难
财力和资金问题是影响民间戏剧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土生土长的联合村灯戏也不免受其冲击。剧团团长告诉我们,他们在改革开放前为了演出一场灯戏所需要的服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出布票,自己请裁缝缝制衣服。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剧团通过募集资金的形式来集资,剧团成员义务劳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钱的就多凑,经济相对贫困的就少凑,很少从灯戏演出中获得经济收益。市场经济的观念冲击着人们的生活。联合村灯戏的各项费用支出也随之庞大,如道具服装制作、误工费等。就靠一个本土农民组成的剧团来说已承担不起,需要政府的资金。随着2014年老司城申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展,县文化局下拨了一笔几千元的资金作为剧团经费开支,他们拿到这笔资金后主要用于购买演出服装和恢复部分道具等。通过我们的现场观察可以知道到目前为止,联合村灯戏剧团在演出服装和道具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演出所需要的现代音响设备也极度缺乏。所以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剧团的老艺人们,甚至也极大的影响着联合村灯戏的传承和发展。
五、结语
联合村灯戏作为湘西地区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小戏,它深深扎根于老司城这一文化遗产的自然空间与土家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联合村灯戏运用独特的灯调,融入土家族的地方风俗,与当地方言土语紧密结合,亦庄亦谐,寓教于乐,是联合村的人民自己创造,土生土长的草根艺术,是研究老司城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联合村灯戏有着鲜明的娱乐色彩和艺术价值,一直活跃在老司城这块土地上。面对文化的变迁与文化空间的变化,随着现代影视艺术的普及与电视文化的发展,联合村灯戏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面临消失的危险,挖掘抢救和研究已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如何传承灯戏艺术,是摆在当地村民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研究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桢.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J].文化遗产,2008(4).
[2]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222-223.
[3]谭达先.中国民间戏剧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0-31.
[4]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4.
[5]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1.
[6]俞为民.戏考论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7.
[7]傅谨.京剧学前沿[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01.
[责任编辑:毛家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