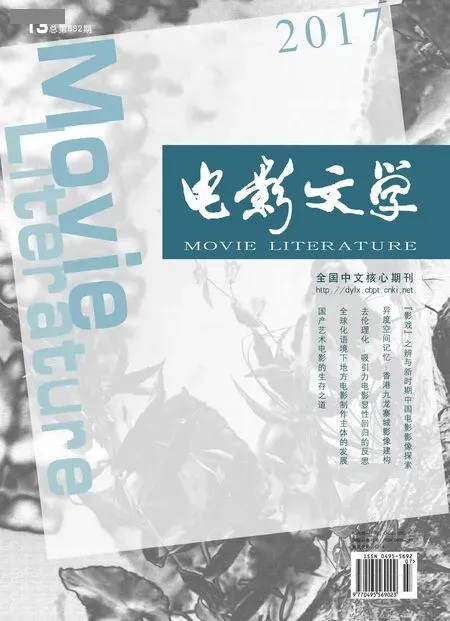荒诞与象征:现实表象下的中国故事
王春枝
(中原工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遵循最常规的因果承续的内容架构,以全知视点凝聚情节,但重情节线索轻细节骨肉的架构特点使这个因果相连、富于秩序感的故事变得飘忽而荒诞。同时,基于偶然的反讽叙事真假倒错,强化了其传奇性;方圆画幅的选取,对称构图、低饱和色彩的运用,使得故事进一步抽象写意,江南水乡背景下为洗雪自己而四处鸣冤的李雪莲,已然成为一个符号,成就了现实表象下中国故事的荒诞与象征。
一、因果承续的内容架构
(一)视点:全知到旁白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二者均为全知视点,在电影中更直接置换为旁白,交代事情始末并从旁代叙李雪莲的内心。在全知视点下,电影严格遵循古朴的线性叙述,依次讲述李雪莲生平诸事,以时间为线,以旁白点染,自然讲述了事件的因果承续。
表面看来,全知视点下娓娓道来的故事贴近现实生活,一件件因果相连,富于秩序感,但在骨子里却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在李雪莲的故事中,充满对女性身份的利用:与卖肉老胡进行交换,对老实人赵大头提出献身,但这些主动的身份资源利用并未顺利实施,反而在李雪莲决定回归女性身份和赵大头结婚过日子时,她才发现生活越来越荒诞,李雪莲似乎真的成了潘金莲。而全知视点下淡然讲述的现实和荒诞交错重叠,显得更为残酷。
此外,官员撤职事件无限放大了李雪莲故事的荒诞性,至此,影片前段的个人故事演化为社会事件,家庭矛盾演化为官民冲突。李雪莲从女主角退后为线索人物,故事的发展挟裹着无形的社会动力滚滚向前。最后到秦玉河车祸去世,故事重新回到个人,终于来到无奈的收束。当李雪莲和史为民餐馆相遇,细数当年往事,重又回到社会事件中。这期间,旁白的点染冷静又隔离,强化了这种现实的荒诞感。
电影以全知视点展开,以旁白勾连情节、敷陈因果,以旁白开始,以旁白结束,在对潘金莲的故事讲述中开场,在对李雪莲的人生评论中收尾,旁白是故事的讲述人,亦是故事的评论者,李雪莲的故事在说书人似的旁白中悠悠退后为口口相传的荒诞传奇。
(二)情节:凝聚与消解
从情节的因素考量,电影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了凝聚处理,使之更适合电影表达的体量限制。电影删减了小说中的枝节人物与事件,集中了故事发生的场景,李雪莲女儿的支线被省略,和市长吃饭的地点改在李雪莲自家开的牛骨汤饭馆里,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也从小说中的20年浓缩为10年。最大的改动是把小说中史为民“上访”的章节改为电影中的一个小吃店场景。小说结构安排奇特,前两章共17万字为序言,讲述李雪莲上访的来龙去脉;第三章3000字为正文,讲述县长史为民被撤职后的生活。前两章和第三章的故事没有交叉。在电影中,第三章的内容几乎全部删减,史为民完全没有自己的“上访”,他出现在一个新增的情节中:到北京洽谈生意时在饭馆里与李雪莲偶遇,即为完成李雪莲事件的完整性而设置。
在小说中,史为民的故事与李雪莲的故事互为参照,李雪莲一心告状申冤却最终失败,史为民利用上访回家却一举成功。两者的鲜明对比使小说的荒诞况味更加浓郁。正如作者刘震云所说:“史为民利用上访,就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目的,以荒诞来对待荒诞,他就成功了。”①第三章的标题“玩呢”也明确了这一荒诞设置。电影把史为民上访的故事删减并连缀为李雪莲故事的尾声,成就了李雪莲故事的完整性,却消解了其中的戏谑和颠覆意义。电影在两人的相遇中缅怀了过去,共同对历史进行了重述与重构,同情了李雪莲代表的上访者,体谅了史为民代表的一众官员,达成了与现实的和解。
电影凝聚之后的故事仍然按照因果承续进行内容架构,呈现现实生活的自然流动感,同时,保留了重情节线索轻细节骨肉的架构特点,使故事凝聚于上访而非细致的日常生活。因此,看似现实的上访故事显得不够“真切”,而是有种市井传奇的恍惚和荒诞感。常态化的日常生活让位于上访这一故事主干,李雪莲浓缩为一个执着于上访的人物符号,着力于表现概念而非人物本身的情绪情感。多年上访的辛酸与无奈,官民关系的紧张与对抗,在凝聚的故事中变得模糊。虽是现实故事,但似乎又出离于现实之外,形成一种飘忽的荒诞。
二、基于偶然的反讽叙事
(一)巧合作用下的故事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故事越依赖于巧合,其真实性就越容易受到置疑。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从现实叙事出发,却一路依赖情节的巧合,再加上人物细节的刻意规避,故事洋溢着与现实疏离的传奇性。事情的放大基于偶然的巧合:李雪莲借宿的宾馆恰好是人大代表的住所,于是她才得以混进去见到了高官;事情的解决也是由于偶然的巧合:秦玉河车祸而死造成了上访事件的意外解决,李雪莲失去了上访的源头,官员们摆脱了年年截访的困境;和原县长史为民餐馆偶然相遇,道出了事情的真正缘由。整个故事由巧合推动,现实事件恍若偶然作用下的吊线木偶,充满了荒诞与疏离。
(二)真假倒错的反讽
偶然与巧合作用下,李雪莲的上访故事洋溢着传奇色彩,也饱含真假倒错的反讽。故事起源于一场假戏真做的离婚,为了一间房子/一个孩子,李雪莲夫妇以离婚求得政策的空隙,结果却变成自我伤害的真戏。随着李雪莲逐级上告,家庭纠纷这一芝麻事件逐渐扩大,在撤职事件后被放大为社会事件,相关官员被惩办,但事件的源头秦玉河并未被触及,“我不是潘金莲”的命题更是无人问津。人们早已淡忘了李雪莲上访的初衷,而只看到上访本身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结果和动机的错位使李雪莲一再上访,但此时,李雪莲似乎已经不再是李雪莲了,她已被置换为“潘金莲、小白菜和窦娥”三位一体的上访符号。因此,当她表示不再上访时,她的真心话无人相信,而在她被激怒仍要上访时人们才以为看到了事情的真相。第一次,她只是想让前夫在她面前说出事实真相;第二次,曾经见证事实、相信她、陪伴她的老牛死了;第三次,她被赵大头的情话打动,三次都是她想放弃上访、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契机,也是李雪莲朴素的生活逻辑的新起点,但一次又一次,真相都被假象淹没。展现在李雪莲面前的生活,似乎阴谋处处障碍重重,阻挡她回到真实真切的日常生活中。在真真假假的演变和置换中,事实被反复重造,真假的界限已然模糊不清。
三、抽象写意的形式呈现
(一)方圆之间的写意表达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运用了圆形画幅和方形画幅,达成了对荒诞故事的写意表达。从银幕发展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种逆向选择。银幕从小渐大再到巨幕电影,宽高比从4∶3到16∶9再到2.35∶1,电影技术的发展走的是一条逐渐扩张的路线,包括画面内部的具体设置,也致力于打破银幕边框,传递更多的画外信息。整体看来,是跨越限制追求自由之路。《我不是潘金莲》以一种自我设限的方式讲述故事,画幅的主动选择着意于对现实故事的写意呈现,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制造明显的间离效果。②
圆形画幅以一种很中国的方式切入故事,师法中国传统的团扇绘画技法,以三分之二的片长表现圆形画幅里的故事。同时,故事发生的背景也从北方转移到了江西婺源,圆形画幅里秀美的江南风光为底色,李雪莲的现实故事在圆形的古典美景中仿若一幅写意国画或一出遥远戏曲,产生明显的陌生化和隔离感。
与江南的圆形写意不同,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则以方形画幅呈现,以表现帝都为代表的国家的方正。同时,画面组织也更加严谨,整体营造了一种“规矩”的氛围。方圆画幅的转换借助于电影场景的自然边框,巧妙地规避了方形和圆形的视觉冲突,处理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隧道圆形的穹顶和圆形画幅重合,火车进入隧道之后形成一个天然的黑场,自然成为从圆到方的过渡。李雪莲拜佛的场景设置了一扇圆形的窗户,圆形窗户里的主人公和之后圆形画幅里的主人公无缝切换。
和画幅的选择相呼应,电影以固定镜头为主,在相对静态的画面中讲述故事,人物运动则多从右边入画、从左边出画,再加上大量的中全景镜头,形成一种高度风格化的呈现。整体上画框感、隔离感明显,电影营造的不是对故事的深度卷入,而是对影像的疏离与评判,类似戏剧舞台的观察和透视。《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以冲突存在的故事,当把这个故事放置在精心设计的画幅里,放置在方圆之间时,用写意的平衡和谐的形式呈现,是形式的创新,也是对现实的调和。
(二)对称构图的刻意安排
与画幅的变换相匹配,电影构图放弃了常用的九宫格,而多以对称构图呈现,拍摄主体以圆心或对角线中心为画面重心,在水平和垂直分割线周围组织分布。这种构图,在抓住观众视觉焦点的同时,也暗示了人物地位的高下。字幕则放置在垂直分割线的右侧,以一种不均衡的对称保持了画面的平衡。
“喝茶”场景的设置是一种典型的刻意对称。左右的对称分置显得双方势均力敌,送上年货的情节设置则消弭了对立,走向了调和。而在此之前,请“喝茶”的场景设置也饶有趣味。李雪莲从画右走向画左,难得的横移镜头跟随她前进,当李雪莲被前景停靠的面包车遮挡,摄影机转而以克制的固定机位拍摄,观众只能透过面包车的玻璃窗隐约观看,根据李雪莲质疑的声音推测故事的走向。当面包车载着李雪莲开走,画面中留下的是被石桥分隔的山水旖旎的空镜,密集的鼓点声中,仿佛是舞台上的戏曲故事。
电影中还有一处“裸戏”的处理非常出彩。先是固定镜头下赵大头的进攻,赵大头从右侧冲出画面又很快被推回,几个回合之后,画面彻底成为空镜,观众只能从右侧赵大头和李雪莲的画外音中找寻事情进展的轨迹,电影以热烈又含蓄的方式演绎了床戏。接着,画面一转,圆形画幅把旅店的窗户裁成一个圆形的边框,前景是模糊不清的赵大头和半裸的李雪莲。这一场景和影片开始时潘金莲的扇画无形之中形成呼应,李雪莲和潘金莲至此已分辨不清。而透过纵横交错的窗格,可隐约看见古镇安静的街景。这一刻,时光停滞,一切似乎都安静了下来,如此美好,也因而在之后赵大头求婚真相揭露后显得更加残酷。
(三)低饱和色彩的意义内化
作为一个冲突强烈的故事,电影很容易把关注点放在对冲突的强调上。但对《我不是潘金莲》来说,表现冲突显然不是其着力点。电影多选取低饱和色彩讲述故事,与画幅的处理浑然一体,整体画面有着中国古典的美感。根据色彩不饱和理论,高饱和色彩利于表现外部动作,低饱和色彩利于表现思想和情感。③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低饱和色彩的普遍使用有效地内化沉淀了故事的内涵,呈现出人生的荒诞感。
同时,电影多以雨天场景出现。雨天一方面为低饱和色彩提供了理想的天气环境,一方面也与江南的地理风物匹配,风景秀美,水雾萦绕,恰似中国山水画的晕染。在氤氲的空气中,李雪莲的故事变得缥缈起来,消融在旖旎风景之中。
镜头的景别处理也与低饱和色彩匹配。中全景为主的景别处理,是低调不强加的故事讲述方式,尽量避免使用主观镜头与特写镜头,不以人物的视点带入,不以强加的方式渲染,“给她一个全景,人们更容易相信那是李雪莲”④。全景中为洗雪自己而四处鸣冤的李雪莲,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现实表象下的中国故事在充满间离意味的江南风光中晕染成一出荒诞传奇。
注释:
① 河西:《刘震云:荒诞没有底线》,《南风窗》,http://www.nfcmag.com/article/3628-2.html,2012年9月25日。
② 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指通过陌生化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从而使观众以一种保持距离和惊异的态度看待演员的表演或者剧中人。参见布莱希特:《论实验戏剧》,《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③ [美]赫伯特·泽特尔:《图像 声音 运动:实用媒体美学》(第3版),赵淼淼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④ 田婉婷:《一面喜剧的镜子》,《法制晚报》,http://dzb.fawan.com/html/2016-03/17/content_5963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