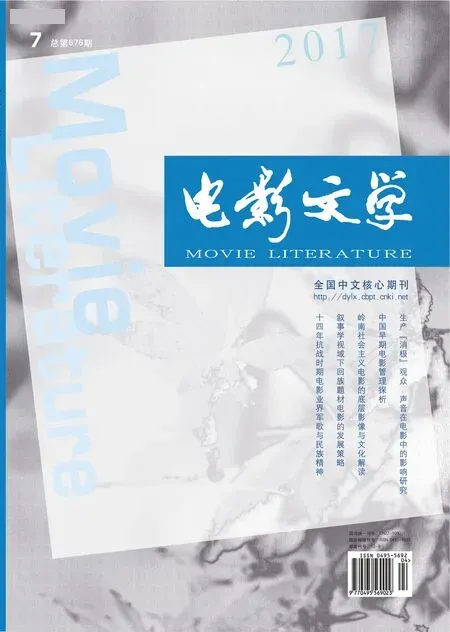《七月与安生》改编下的女性主义私语
魏子钦
(吉林省白城市电教中心,吉林 白城 137000)
2016年9月上映的《七月与安生》,某种意义上打破了现阶段国产青春影片的定式。在影片叙事上,恋爱和伦理不再是影片论述的主题,《七月与安生》既没有男女主角的旷世奇恋,也没有观众已经审美疲劳的“颓废青春”。从一定层面上,《七月与安生》的定位和眼下流行的青春影片有很大差异,本质上是一部女性成长的私人史。《七月与安生》不再围绕一个男主角展开,也不再堆砌复杂的多角关系、生离死别,而是反其道行之,荡开一笔,以两位女主角为主要的叙事对象,造就了这部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青春电影”。
《七月与安生》围绕着七月和安生两个主角展开。两个女孩从少年时就是朋友,七月静如处子,安生动如脱兔。两个性格相反的人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也因此为后来人生中的价值选择分歧埋下了伏笔。电影的叙事节奏相对缓慢,采用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也很容易让观众在观影开始摸不着头脑。这些特点既造就了整部电影文学气质的叙事,同样也可能因为文艺气息导致观众在审美取向上存在理解的误差。在《七月与安生》上映之后,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从侧面说明了国内观众在观影审美取向的提升。而《七月与安生》的剧本取材于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剧情有所改编,但文学气质在剧中尚存,两者的互文性同样也让女性主义的叙事主题相映成趣。
一、披着恋爱外衣的传记化的女性成长史
在《七月与安生》的原作小说中可以看到,故事的展开始终是围绕着两位女性进行的。七月沉静安稳,她希望过上波澜不惊的生活;而安生则恰恰相反,因为家庭的因素,安生的心愿如莫里哀的那句名言:“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为了投奔爱情,安生几乎冒着人生所有的风险,去寻找生命中纯粹的情感。在原作小说中,安生和七月的差异表现在人生选择上,同样也表现在感情的经历上。七月和安生都渴望着赢得苏家明。苏家明对于二者来说,既是爱人,也是一个象征着是否胜利的所有物。安妮宝贝在这篇写作于2002年前后的小说中也做出了符合当时女性价值的判断。在故事的结局处,安生因为生下家明的孩子时难产死亡,而七月则抚养安生的孩子和家明在一起。这一结局的设置可谓“求仁得仁”。
影片《七月与安生》的叙事视角则出现了相对的颠覆。在影片中,七月和安生的形象出现了融合。两人和小说中的扁形人物不同,在影片中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立体形象。安生虽然依旧生活动荡,但是在生活之外,她和平凡的女生毫无区别,她渴望一切美好的情感。而七月虽然依旧渴求安稳,却不再忍气吞声,她成为三人命运中事实的主导者。七月和安生的形象设置不再是一种刻意的对比,而是一种流动的展示。
在影片中安生离开七月开始独自闯荡一段中,这种角色成长则展现得相当明显。这一段采用了短平快的蒙太奇剪辑,几分钟内通过几个镜头展现安生的一段生活,旁白则作为镜头叙事的补充完成人物叙述。开始是安生在给七月的信件中诉说,她当年追随而去的歌手,事实上只是一个自我陶醉的骗子;紧接着与摄影师热恋,却最终失望地发现摄影师只是一个没担当的男人;她尝试代替七月去看一看大海,可是在下船之后才发现她自己是多么地想念七月。这种交替叙事乍看平淡无奇,但针对此情节展开文本细读可以发现,这一段经历是导致安生开始理解七月,向七月的身份特点转向的伏笔。安生在动荡中开始渴望安稳。同样交替的还有一段七月的回信,七月在生活中饱受压力。升学、求职、和苏家明不温不火的恋情都让七月感到精疲力竭。此时,她也渴望能够和安生见面,这种刻意的衔接,也让观众体验到两人人生中彼此的不可或缺。在《七月与安生》中已经不太能够看到易卜生《娜拉》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性独立意志觉醒,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性格成长角度,为两位各异的女性“立传”。这种表现手法在国内近几年的青春类型片中也是首次出现。
二、男性角色的缺失与观众的情感认同建构
影片中曾经反复出现对男性的有趣评价,安生在寄给七月的明信片里面引用了杜拉斯的名言:“世上多数男人都是很难忍受的。”随后又增加了附加条件:“除非你非常非常爱他。”这种情绪叙事的主线一直延续到影片末尾。作为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电影,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影片叙事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然而影片开始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安生抛出的论调,仿佛黑色幽默,给影片整体的建构提前安排上一种“非男性”的女性主义叙事观。
男性在影片《七月与安生》中简化为符号化的阳性指称。在影片中出现了两个较为重要的男性:一是苏家明,另一个则是“老赵”。苏家明在安妮宝贝小说中一直以隐笔描述。小说中,苏家明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导致了七月和安生之间的战争。争夺苏家明是小说前半段的中心情节,直到安生死亡,两人才最终达到了和解。在影片中则做了减法,苏家明的重要性被一降再降,最后只在影片开头末尾出现,成为“机械降神”的剧情设置的一部分,成为引导剧情发展的枝干人物,但是却丝毫不能引起观众的喜爱和认同。苏家明的形象符合青春电影中常见的“白马王子”的形象:成绩好、长相清秀。然而在优秀背后,甚至可以发现这一角色的空虚性。他一边与七月交往,一边又向往安生。在和安生同居后,又担心七月会离他而去。苏家明患得患失同时又毫无担当;看似坚强,实则遇事逃避。事实上,除了一副好皮囊,苏家明的“优质”形象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虚妄的假设。
以苏家明与安生、七月的态度相对比,也能够看出男性角色设置的刻意弱化。苏家明第一次出现,是因为安生担心七月被欺负,提前去学校警告苏家明,不要辜负七月。这一段的镜头将两人同框。安生步步向前紧逼,苏家明一边微笑一边和气地倒退。在警告苏家明后,安生离开,镜头转向以苏家明为主要视角,亦步亦趋地跟踪安生,直到安生被她的摇滚歌手朋友接走。这一段中,苏家明始终保持被动位置,即便对安生产生了兴趣,但最终依旧秉持观望态度。在七月结婚一节,苏家明则依靠彻底的失踪来逃避必须面临的抉择。他既不与安生分手,也不愿意拒绝七月。这种暧昧性导致角色在叙事立场上的彻底失语。作为一部爱情影片的男主角,这样的角色显然是失常的。
“老赵”则是男性角色形象的另一极端。这是原作小说中没有出现的角色,在影片中被安生虚构在《七月与安生》这部小说里。老赵是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形象。他成熟、包容、爱护家庭、承担责任,甚至烧得一手好菜。他和安生的故事发展来自于安生的自我虚构。和苏家明形象的“去势”相比,老赵则过于温柔和负责。在七月见到安生一节,安生已经为准备和老赵开始新的生活而学习英语,老赵则清楚地知道安生的口味,为安生准备丰盛的饭菜。在安生的朋友七月来临时,老赵只是作为陪客,而不是一个互动对话的参与者。这种背景角色在七月离开安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机场分别时,七月对安生说:“跟我走吧。”安生则对七月说:“留下来吧。”这组对话重复数次,老赵虽然一直在安生背后,却始终笑眯眯一言不发。这种“不参与”仿佛也表示出老赵与安生的关系中亲情多于爱情,理解大过占有。在安生参加母亲葬礼一节,参加葬礼者只有安生一人,这种关系仿佛也揭示了安生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缺失。换言之,老赵扮演的并非一个情人,很大程度上,他是安生的“幻想父亲”。与其说两者之间拥有爱情,不如说两人之间的纽带来自于对亲情的渴望。
软弱的苏家明和宽厚的老赵都不是典型的青春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形象。换言之,正常的男性在《七月与安生》中是不存在的。整部影片诉说的依旧是两个女生的故事。男性反而成为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环。安生和七月从小相识,相伴长大,关系好到可以在一个浴缸里洗澡。然而分享一个男友却成了两人分裂的原因。事实上,分享的男友是谁这一点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男友的存在让两人感受到了同性之间的相互嫉妒。是否拥有苏家明不重要,是否能够通过拥有苏家明证明自己胜过对方才重要。这种剧情的导向影响导致了整部影片的女性主义特质。正如同很多青春电影尝试叙说却没有揭露的一样,在女性的成长空间中,主角永远只是女性,男性只是催化剂和陪衬品。
三、以镜头代替叙说——镜头语言的女性絮语
文学叙事依靠作者的文体,影片叙事则主要依靠影片的运镜和剪辑。《七月与安生》中大多采用中景镜头。以往青春电影中常见的演员表情特写,在《七月与安生》中反倒不多见。中景和远景的运用会让影片的代入感和情感冲击降低,却能够给观众更广阔和更充裕的观赏空间对剧情进行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以影片中开场不久的浴室情节为例。年幼的七月和安生正处在刚刚开始青春期发育的阶段。两人在学校闯祸后回家,为恶作剧的成功而感到心有灵犀。两人在浴室洗澡引发了一场关于“胸罩”的讨论,此时的镜头是俯视的。安生嘲笑七月“你穿胸罩啦”,镜头扫向的是七月穿着胸罩的背部,镜头代替七月的目光扫向安生的胸部,然后七月的声音在画面外响起:“谁像你这么平。”这一段可以看成是二人性别意识最开始的表现,同样可以作为性格的基调展示。胸罩在文化的意象上往往作为自我压抑的形态出现。女性在论及胸部时,往往存在自轻自贬的语境语态,在青春期女生中,胸部发育往往和情色意识相连接。七月的发育与胸罩,以及安生的平胸和未发育,本质上已经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七月更早地意识到了情欲的存在,却一直压抑。而安生虽然不拘小节,在本质上,对爱情却远远没有七月那样渴望。这种镜头代替眼光的交错暗示了两人的个性差异。
浴室在整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作为最为隐蔽的场所,浴室所承载的叙事功能被一一放大。第二次的浴室戏份中,七月已经不愿意和安生共用一个浴缸。此时拍摄七月时,是仰视的。七月既怜悯在外奔波的安生,又难以对安生和家明之间的感情释怀,她俯视安生既表达了怜悯,同时也表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支配。第三次的浴室戏码则是两人彻底决裂,又一次涉及了胸罩。七月声嘶力竭地冲安生怒吼:“你凭什么跟我抢?你有的都是我施舍给你的。”安生则回应:“我怎么会跟你抢,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只要你说你要。”浴室场景中镜头的不对等此时发生转换,安生俯视七月,七月则仰头怒视安生。这种身份的调换仿佛也从侧面说明了两人身份的调换,而这种身份调换的原因既来自于二者心态的变化,也来自于两人争夺苏家明胜利与否导致的地位变迁。这种隐秘而微妙的机位选择和剪辑也从侧面展示了关涉女性情感的细密絮语。
在影片末尾,七月远离了三人之间的是非,独自走向灯塔,四周皆是白雪。这种接近于宗教语境的镜头也是俯视的,观众几乎以上帝的视角,看见七月孤身一人虽然不再安稳,却真正勇敢地走向了自己的生活,这种镜头的运用仿佛也代替剧情说明了七月和安生之间各自女性意识的成长与相互成就。结局不落俗套的拒绝对男女主角情感简单地给予完结,从本质上也反映出影片的价值取向——试图跳跃出传统的青春影片窠臼,以人物成长的方式,真诚地讲述一段人物成长的近乎真实的历程,这一点同样是近期上映的电影中相对罕见的。
——评电影《七月与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