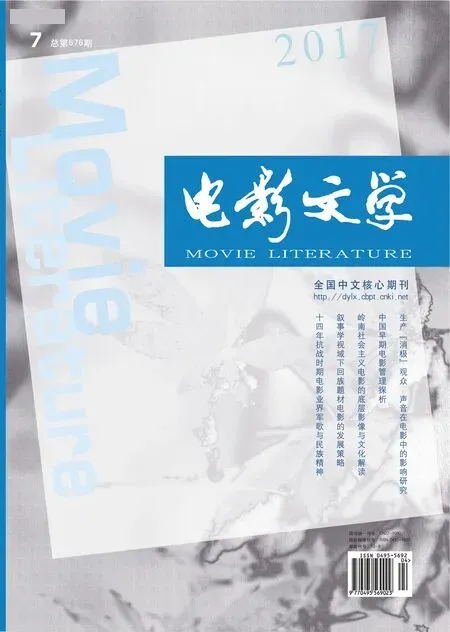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七月与安生》中的“我”与“他者”
黄闪闪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七月与安生》自上映以来,口碑一路看涨。最初,因为安妮宝贝、青春、爱情等标签,电影在豆瓣的评分只有6.7分,如今已经涨到7.6分,这也是2016年上映的国产商业片中,口碑最好的一部。[1]票房口碑的双丰收,也将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推到了公众面前。正如韩寒表示自己很羡慕安妮宝贝,因为“电影给了原著升华。敬佩导演曾国祥、监制陈可辛”[2]。这种升华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内容上的升华,改编剧本对故事情节做了大量修改和交代,更具戏剧性和合理性;二是形式上的升华,电影保留了原小说的态度,通过蒙太奇手法和无声源音乐的恰当运用,还原了同名小说的“灵魂”。套用加缪的话,伟大的作家都是哲学家。优秀的电影都是哲学电影。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在存在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和小说的诸多异曲同工之处。
一、原著小说中的女孩们:他者和孤独
《七月与安生》收录于庆山(安妮宝贝)的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七月和安生分别是两个女孩的名字。七月如名,平常安稳,就像每年的七月总会如期而至。安生却不安生,大胆叛逆,自由不羁。尽管性格迥异,但不妨碍她们成为好朋友。有时七月是安生的影子,有时安生是七月的影子。故事围绕着她们同时喜欢上一个男孩家明展开,在友情与爱情的纠缠角力下,七月与家明结婚了,依旧平静安稳;安生和一个男人远走异国,回国了,生下了她与家明的孩子,到死也自由不羁。七月与家明共同抚养安生的孩子,现世安稳。
从人物关系中的“他—她”看,庆山的原小说没有多么深刻。毕竟“两女一男”的剧情在张爱玲那里已经发挥到极致。在“振保”们的眼中,“红玫瑰”“白玫瑰”们自动陷入朱砂痣/蚊子血、白月光/饭粘子的对立身份认同中。然而,对于“她、她和他”之中的“她—她”关系,庆山的作品则显得更有深意。除了《七月与安生》,庆山的另一部小说《八月未央》同样涉及三角关系,甚至在人物关系上可以一一对应:七月—乔,安生—未央,家明—朝颜。情节从来不是庆山小说的重点,人物形象多变也不是她作品的特色,恰恰相反,庆山小说的女孩们呈现出一种同质化的倾向,她们都是彼此的“他者”,女孩们之间的“她—她”关系呈现出一种镜像表征关系。
“他者”既是符号化的他人,更是负载着社会文化意义的符号世界。小说中,七月和安生的第一次相识,就是安生邀请七月一起到操场去,接着安生爬上那里的一棵树,爬到树杈的最高处。从那以后,“树上的女孩”这个符号一直存在于七月的记忆中,“可是她始终没有跟安生学会爬树”[3]223。安生就是七月的“他者”。安生作为“树上的女孩”,她无所畏惧,她自由不羁。“总有一天,我会摆脱掉所有的束缚,去更远的地方。”[3]224即便如此,她抛不下家明送给她的玉坠,并且生下家明的孩子。可是家明“只能碰到一个”,所以安生对七月说:“你以后当我死了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还会想起你,可是我不愿意再想起你了。”[3]238七月是安生的“他者”。
“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一种镜像表征的结构关系,即“我”想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并有与他人同样的欲望。人的欲望最终来自“他者”,是对他人欲望的欲望。七月与安生也不例外。安生是七月“心里的潮水,疼痛的,汹涌的”[3]232。而安生只能惆怅,“只要一个男人能有一点点像家明,我也愿意。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家明更英俊、更淳朴的男人了。我们都只能碰到一个。”“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七月,却只能做安生。”[3]252家明是七月的。“镜像”概念是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的概念,他指出当婴儿辨认出镜中的“我”时,会异常兴奋,努力向镜子靠近。这表明人类的欲望之一在于,人想得到他人的承认。七月和安生虽然出身、性格不一,但是七月内心羡慕安生的自由不羁,而安生同样渴望七月的现世安稳,对家明的不舍实际上是她羡慕七月的一个意象。
庆山笔下的女孩们都是孤独的,这源于作家的表述方式。当庆山还是安妮宝贝时,她的小说常常采用一种冷漠的叙述语调。小说将人物对话转化为间接引语,借此消除对话的相互沟通的常规意义,同时也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认同的社会学意义。在这种冷漠语境的建构下,小说不进行深入的人物心理探索,不着墨于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共鸣,一切显得游离缥缈,各个人物的孤独呼之欲出。这也是她作品的独特魅力之处。
二、改编剧本中的女孩们:自由选择和残酷
剧本《七月与安生》 对原小说情节的修改不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升华。情节随着人物情绪的起伏而变化,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深刻,其行为也呈现出更为合理的逻辑一致性。
首先是对故事内核气质的坚持。这点可以直观地通过电影片名的英文版看出。《七月与安生》又名“Soulmate”,即灵魂伴侣。庆山曾经说过,我的文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这种“灵魂相通”就是所谓的共鸣,甚至能给读者带来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故事中的女孩们正是一对灵魂伴侣,故事虽然是两女一男的纠结关系,其实质却是两个女孩之间身份认同的判断过程。
其次是对剧情戏剧化的处理。最大的区别在于故事的结局。原小说中,最后死去的女孩是安生。七月和家明共同抚养她的孩子。但是在电影版中,有了更多的遐想空间。故事的分歧点从七月剪短发后去找安生开始:
第一个结局,安生和老赵幸福地生活着,七月没怀孕,踏上旅途——七月成了“安生”,安生成了“七月”。
第二个结局,安生独自生活,七月怀孕生女,远走高飞,安生带孩子——七月成了“安生”,安生成了“七月”。
第三个结局,安生独自生活,七月怀孕生女、大出血死亡,安生带孩子——“安生”死去,安生成了“七月”。
无论何种结局,“七月”是最终活着的那个。这和原作中的结局异曲同工。自由不羁终究抵不过现世安稳。据此,电影和小说的灵魂达到高度统一。
最后是对女孩形象定位的深刻。这种深刻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自由选择”是人的自由意志通往相应本质的中介桥梁,选择是绝对的。人越是处于逆境,越是自由,因为逆境促使人做出选择,人的自由选择机会均等。既然人人都具有“为自我”的自由选择权利,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他人即地狱。为此,须将“自由选择”置于道德审判之中,人在此无法真正做到为所欲为,只是具有相对的自由选择。戏剧文学中,萨特常常用所谓的“情景剧”来肯定存在主义者的人道主义伦理道德观,既立足于个人、本能,又不失良心、正义。通过对情境的刻画,将人物逼入二难选择之中,让他们通过“自由选择”来决定自己的本质,决定自己的命运。小说中的安生大胆主动,在小庙中,“他(家明)听到安生轻轻地说,那他们知道我喜欢你吗?”“安生说,我爱家明。我想和他在一起。”[3]228而电影中的安生对家明的感情则隐忍敏感得多,只有那句明信片上的“问候家明”、脖子上的玉坠昭示着这种情愫。如同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安生并不是非理性的人,而是坦然体验现世一切幸福和痛苦的人;她不是浑浑噩噩的人,而是尽情享受人生的人,是既能行动又能静观、已习惯并安然于荒诞命运的人。安生终究选择了“不自由”,这为她最终成为“七月”埋下了伏笔。七月也不是小说中的“七月”,就像一年中的七月,它虽不像八月那么聒噪,但终究是躁动的。学校的铃是她砸的,家明的逃婚是她提出的,她心中也有“自由选择”,但是电影显然把握了小说的情绪,将“自由”与“死亡”连在一起,终究是悲观的,这就是生活的残酷。
三、言语和影像:电影对小说的皈依
“我就是命不好”和“高跟鞋”。语言是先于主体的“他者”,其目标又是他人。语言是说给他人听的,旨在获得他人赞同的行为。安生和家明在一起的事实被七月撞见后,安生倚在沙发上对七月说:“我就是命不好。”这句话与安生后期的高跟鞋装扮完成了“身份辨别——认同”的任务。小说中这句话是七月的妈妈告诉她的:“那个女孩其实天分比你高得多,七月。就是命不好。”[3]240为什么命不好?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运”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男性是更加自然的性别,而女性是非理性的,并且被客体化。女性气质怎么样,取决于男人眼中的女人是怎样的,女人本身被视为一种“物”。根据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观点,女性呈现为男性与混乱的必要边界。她们既不在边界内也不在边界外。因为她们的边缘化,男性文化有时把她们呈现为黑暗的和混乱的,有时把她们提升为更高或者更纯粹的自然的代表,即圣母。[4]在这种“混乱/自然”的模糊框架内,被客体化的女人们完成了身份皈依。安生的“命”不好,她是女人,她需要完成框架内的自我身份认定。在自然/自由的两难选择中,她选择了前者,电影中的两次高跟鞋特写就是一种还原。高跟鞋是庆山(安妮宝贝)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高跟鞋在男人的眼中是有女性气质的,但是女人穿着它远不如一双球鞋舒服。电影中的安生最终成了一个只穿高跟鞋的女人。而小说中的安生最终死了。
“我想自由自在”和“灯塔”。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先有自身存在,然后通过自为,通过行动,才确立自身的本质。如何创造一个真正自由意义的世界,是萨特所思考的。萨特没有想明白,而电影中七月的“自由选择”也是残酷的。她不再是书中那个树下仰望安生的女孩,也不再是那个只懂得依赖家明而不懂拒绝的女孩。她主动让家明离开,剪短头发,独自生下家明的孩子。她想选择成为安生,所以她对安生说:“我也想自由自在,和你一样。”只是男性话语中,“自由选择”会带来道德本质的不确定性和虚无性,原小说中的七月,“宁愿自己变成一个神情越来越平淡安静的女人”,最终她活着,安生死了;而电影中的七月在27岁时死了,安生代替七月成为“七月”。电影的结尾,“死而自由”的七月走向一座灯塔,这是值得玩味的。“灯塔”是伍尔夫《到灯塔去》的一个重要意象,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得意或失意,内心都感到茫然犹豫,感到生活与自己精神、心灵上的隔阂。但是呈现生活中的冲突对立并非伍尔夫的目的,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达到生活的最终和谐,则是她的初衷。“灯塔”就是表征冲突对立结束的意象,也代表了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的消除。这是一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主张身体不是天生永恒的。性别问题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在理想的新社会中,只有人,没有“女人”和“男人”。也许,“灯塔”也是向往女性自由的一个意象吧!
——评电影《七月与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