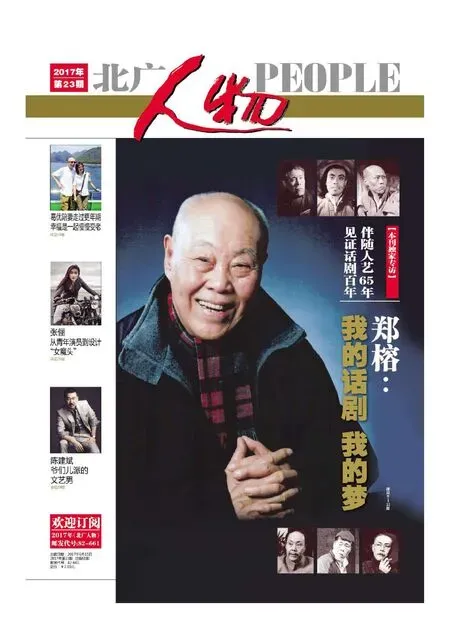刘恒从纯文学作家到顶级编剧(1)
刘恒从纯文学作家到顶级编剧(1)
他用毛笔写繁体字。这也罢了,还用毛笔写剧本;82场、100页,每次当他停顿,毛笔涮好一搁,欣赏码得整整齐齐的稿纸时,他心里舒服极了。
这就是眼下的刘恒。用毛笔写电影剧本,这在文坛、在电影界都是独一份儿。刘恒,生于1954年,作家、编剧,1986年发表小说《狗日的粮食》开始引人注目,一些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菊豆》《本命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编剧作品有《秋菊打官司》《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窝头会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刘恒起初临贴,颜真卿、王羲之、苏东坡……不过瘾,索性用毛笔写剧本,鱼和熊掌兼得。写的时候字斟句酌,于内容是一种思考中的沉淀,于书法是一种用笔间的揣摩。做编剧,本来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用毛笔写,便又增加了新的意义和趣味,他觉得跟文字更亲近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谁不知道一集剧本的含金量有多少呢?和被粉丝与资金双重驱动下多数网络写手每日海量的灌水不同,刘恒似乎生活在他的“小圈子”里,这“圈子”不受任何利益的干扰和牵制,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和习惯。这大概是他温和敦厚的表象下一种固执的坚持。从1977年刘恒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文学之路一晃已过40年。如果说七十年代爱上文学还有炫技的想法,那么现在,他所做的一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种淡定从容向古典的致敬与回归。
迷上鲁迅
1969年,15岁的刘恒穿上了军装,稚气的脸上挂着单纯的笑。军装在他或许也尚显肥大,但他却已是有着7年俄语经验的“老兵”。在做侦听的业余时间,他狂热地迷上了鲁迅——
记者:您多次说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鲁迅的什么?
刘恒:比较吸引我的是鲁迅的锋芒。他作为个体承受的苦难和不如意,向外界表达不满和愤怒的锋芒,符合青年人的状态。行动上不能反抗,至少要有语言上的反抗。这里也有信息源比较单一的原因。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文学书,苏联的作品也有,鲁迅的著作占有压倒性地位,杂文结集出版了很多单行本,我都买来看了。
现在从官方到民间对鲁迅的看法都有一些变化。任何轻视“鲁讯”的做法和观点都是目光短浅的。他们可能抓到了某一个鲁迅的弱点,或者他与现实的不和谐,就企图全盘否定,这是错误的。鲁迅的自我反省和对社会的丑陋面的批判,永远是有价值的。周作人对哥哥有一个很“毒”的评价,他说鲁迅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兄弟间了解应该很深。褒义地理解,可能是说鲁迅有浪漫主义的一面;贬义地理解,周作人可能扩大了自己的愤怒或者自己的正确。从某种角度来说,任何文人在以自己的文字表达思想时,都带有戏剧性。严格地说文字是一种表演——所有的文字,包括给人写信时的文字。
鲁迅是伟大的前辈,他最大的价值,是对国民性弱点的痛恨和仇视。某些弱点现今仍在膨胀,这种痛恨也依然存在。比如马路上的不守规矩,没有羞耻感,狂妄,狭隘……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这种弱点——也包括自己。我更感到鲁迅的那种痛恨是一种很无奈的表现。现在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依然无奈,只是表现的态度不同,有的人可能激烈一些,有的人缓和一些。我今年63岁,没有什么锋芒,一切都可以容忍了。
记者:曾经有过的锋芒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恒:我是从“文革”走过来的,回忆起来还是有一些愤怒,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对“文革”中发生的现象还是不能容忍。久而久之,这种锋芒慢慢淡化了。不知道是更客观了,还是更无奈了。我自己反思,我毕竟是这个社会变迁中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一些利益,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在利益获得一定满足的情况下,斗志有可能被瓦解。这是从贬义的角度说。从另一个角度说,年龄增长后心态自然变化,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对很多事情不较真儿了。所以我还是觉得,不论是好的作品还是好的思想,恐怕还是适度走极端好一些——不适度也没关系,超常地走极端或接近精神分裂,像卡夫卡、托尔斯泰。当然走极端和疯狂也都可以表演。有人认为托尔斯泰的出走是表演给世界看的,以离家出走的疯狂举动,向世界谢幕。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只是追随本能罢了。
我去西安郊区找贾平凹约稿,去陈忠实当时所在的文化站组稿,我们一起蹲在马路边上吃过泡馍。那个时候国家刚刚苏醒过来,有着纯朴向上的氛围。
我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无能和吝啬
对电影的爱和梦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因触动他的某个画面,或因一句记忆深刻的台词,总之,当他潇洒地转身投入编剧,未尝不是一种迟到的回归——
记者:1977年7月,您的短篇小说《小石磨》是发表在哪里?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时,哪些人对您帮助较多?
刘恒:《小石磨》是纪念长征40周年时写的。写作完全是自我摸索,我把小说寄到《北京文学》杂志,第一次投稿就被采用了,责任编辑是郭德润。后来我被调到《北京文学》做实习编辑,以公代干,一直做下来,1985年上干部专修班,脱产上大学,算有了学历,之前填学历都写初中二年级,连初中都没毕业就当兵去了。
记者:在《北京文学》时和哪些作家有过交往?
刘恒:那时挂在编辑部的有杨沫、浩然,但是接触不多。八十年代初,我韩石山家里约稿,他当时在汾西的一个公社,正聊着,公社广播让他开会。我去西安郊区找贾平凹约稿,去陈忠实当时所在的文化站组稿,我们一起蹲在马路边上吃过泡馍。那个时候国家刚刚苏醒过来,有着纯朴向上的氛围,大家都很友善。
记者:1986年,您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在西学思潮涌入的八十年代,您的创作受到影响了吗?
刘恒:读大学后有了完整的时间,《狗日的粮食》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很多经典名著翻译进来,都是很好的营养,只是我消化不良。有一段时间迷恋哲学,尼采、叔本华、萨特、克尔凯格尔等都接触过,多少都受了些影响。人所需要的思想的武器并不多。要掌握很多武器具备强大的思想能力,几乎不可能。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武器。有的时候没有效果,就是选择的武器不正确;有的人用简单的武器取得好的成果,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武器。
(未完待续)据中华读书报舒晋瑜/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