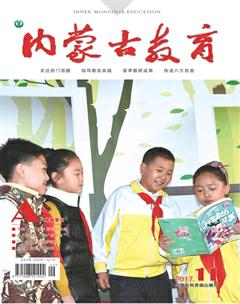夸美纽斯和他的《大教学论》(下)
王丛
二、关于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夸美纽斯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教学方法非常不满。他说:“这些学校教导青年的方法通常都是非常严酷的,以致学校变成了让儿童感到恐惧的场所,变成了他们的才智的屠宰场,大部分学生对学习与书本都感到厌恶,都想急急离开学校,跑到手艺工人的工厂,或找别种职业去了。”所以,对这样的教育进行改革,总结出正确的、适应学生成长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是夸美纽斯写作《大教学论》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研究教育教学的原则、方法是《大教学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夸美纽斯在目录中明确提出的原则有四个:便易性原则、彻底性原则、简明性原则、迅速性原则。此外,有的原则目录里没有提及,但出现在内容中,如第十六章“教与学的一般要求”,即一定能产生结果的教与学的方法里讲了九个原则,其中包括自然性原则、循序性原则、内在性原则等;在大的原则里往往又包含若干小的原则,如便易性原则,就包括了兴趣性等若干原则。夸美纽斯还对科学、艺术、语文、道德教育等学科,都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教学方法。夸美纽斯提出的这些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为现代的教育学奠定了基础,他的那些丰富的、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真知灼见,即使在当下也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真称得上是泽被后世。
限于篇幅,我们只重点介绍一下量力性原则和语文教学法。
(一)量力性原则
量力性原则也称“可接受性原则”,即根据学生的学力安排学习活动,用夸美纽斯的话说就是“一切事情都按学生的能量去安排”。《大教学论》中并没有“量力性原则”这样的字样,只有“便易性原则”,而“量力性原则”是后人根据“便易性原则”中的部分内容概括出来的。量力性原则可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1.学习内容不可过多。
夸美纽斯说:“自然并不使自己负担过重,它有一点点就满足了。比如,它不向一个鸟卵索取两只小鸟,只要产生一只,它就感到满意了。所以,假如学生同时要学许多东西,比如同一年内要学文法、辩证法、修辞学、诗词、希腊文等等,就会浪费他的精力。”这一条和学校关系不大,因为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内容是国家规定的,但却和家庭教育关系密切,尤其是现在,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希望孩子能学到更多知识,具备更多能力,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却不顾及孩子的学力,报班过多,使孩子疲于奔命。有个家长给孩子报了7个班,孩子说,“你还是我亲妈吗?”这种心态下,孩子会愿意努力学习吗?最后,很可能什么也学不会,甚至什么也不愿学。
2.学习内容不可过难。
首先,要从容易的内容学起,为学习难的内容搭建阶梯。夸美纽斯说:“自然是从容易进到较难的。比如,……鸟儿学飞,先习惯用腿站,然后徐缓地运动它的翅膀,直到自己能从地上飞起为止,最后就得到了充分的信心,能在天空中飞了。”所以,要“使学生先知道最靠近他们心眼的事物,然后去知道不大靠近的,再去知道相隔较远的,最后才去知道隔得最远的”。同时,夸美纽斯还强调,教师还要注意“用学生所懂得的语言去讲解”,以化解难度。
3.学习过程不可过急。
夸美纽斯说:“自然不性急,它只慢慢前进。比如,一只鸟并不把它的卵放在火上,去使它们快些孵化出来,而让它们在自然温度的影响下慢慢发展。”“如果我们拿了一只仄口的瓶子(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孩子的心智),把大量的水猛烈地倒进去,而不讓它一滴一滴地滴进去,结果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大部分的水会流到瓶子外边去,最后,瓶子里的水比慢慢地倒进去的还少。有些人教学生的时候,不是依据学生所能去教,而是尽教师自己所愿去教,这样的做法也一样的蠢……”
以上两条与家庭教育关系不大,但与学校教育关系密切。同时,这两条本身也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和进度都是安排好的,所以,为了赶进度,过程可能就过于急促,而过程的急促,又往往导致所学的知识因缺乏必要的铺垫而使难度增加。究其原因,还是没有明确教学是从“学”出发,还是从“教”出发的问题。
“一切事情都按学生的能量去安排”,并不意味着教学可以没有数量、难度、速度的要求,这一点拟放到介绍苏联教育家赞科夫时去谈。
(二)语文教学法
夸美纽斯认为,语文是学习的工具。他说:“学习语文,并非因为它们本身是博学或智慧的一部分,而因为它们是一种手段,可使我们获得知识,并把知识传授给别人。”这和我们今天说的“语文是百科的基础”意思是一样的。此外,他认为,学习语文的主要途径是实践、是模仿。他说:“一切语言通过实践去学比通过规则去学来得容易。”而所谓的“实践”在“这里指的是听、读,重读、抄写,用手,用舌头去模仿,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时时这样去做”。
所以,夸美纽斯认为,学习语文,知识是次要的。他说:“不论哪种语文,对它全部细微的知识进行了解是很不必要的,如果有人要去达到这种目的,那是荒谬和无用的。甚至西塞罗(他被视为拉丁语的最伟大的通家)对拉丁语的细微末节也并不完全知道……”在《大教学论》第十六章中他还说:“一切语文都不要从文法去学习,要从合适的作家去学习。”但是,夸美纽斯并未完全否定规则的作用,他认为,“规则可以帮助并强化从实践得来的知识”。不过他认为,“语言所化成的规则应当是文法的,而不是哲理的”,亦即是形式的,而不是内容的。所以,他强调,在语文教学中,“不应当探究字眼、成语与句子的原因和来历,或试图找出这一或那一结构为什么是必需的,而应当简单地说明怎样是对的,怎样才能选出那种结构”。
读到《大教学论》中“语文教学法”这一章,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夸美纽斯对语文教学法的阐述,精准程度令人咋舌,简直像是针对我们的语文教学量身制作的。他提醒要注意的,恰恰就是我们存在的弊端,如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的语文教学以理解分析为主,总是探讨某个词什么意思,某个句子什么意思,每个段落什么意思,全文什么意思……。也就是做夸美纽斯不让做的事——探究字眼、成语与句子的原因和来历。现在提倡本色语文,像夸美纽斯那样重视听说读写实践,这种现象才有所克服。但是,像“试图找出这一或那一结构为什么是必需的”这样的事情还在做,如经常讨论还可以用哪个词?为什么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这样用有什么好处?且往往被看作是教学中的亮点。endprint
三、关于班级授课制
大家一般都认为,班级授课制始于夸美纽斯,但其实并非如此
最早提出分班教学,亦即班级授课制的设想的,是古罗马的教育家昆体良(约公元35—96年)。他认为,大多数的教学可以用同样大小的声音传达给全体学生,所以,同一时间许多人听同一个讲解,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他还说过,根据一些教师的实践,可把儿童分成班级……
班级授课的实践最早产生于16世纪,亦即中世纪末期,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的学校,首先有了年级的划分和学制的规定。如1538年,德国教育家斯图谟在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创办了文科中学,设有九个年级,并进行了班级教学的尝试。
但是,我们还是视夸美纽斯为班级授课制的奠基人,这是因为夸美纽斯完备了班级授课制的理论并完善了其体制。在《大教学论》和《一个有秩序学校的规则》中,夸美纽斯最早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班级授课制以及相关的学年制、学日制,考查、考试制度。
他说:“太阳并不单独对付任何单个事物、动物或树木,而是同时把光亮和温暖给予万物。”所以,一个教师可以同时教许多孩子。“对教师,对学生,这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教师看到跟前的学生数目愈多,他对工作的兴趣便愈大。同样,在学生方面,大群的伴侣不仅可以产生效用,而且,也可以产生愉快……”从而论证了班级授课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班级授课制是提高教学效率的有力手段。
他提出的班级授课制的具体方法是: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将儿童分成不同的班级;每个班级拥有一个教室,一位老师,这位老师面对全班学生进行教学。与班级授课制相关,他还提出了学年制、学日制、考查和考试制度。他主张在一般情况下,各年级都应该在每年的秋季开始和结束学年课程,其他时间不接收儿童入学,以保证全班的学习进度一致。每日上课时间为4小时,在每学习1小时后休息半小时。每年有4次较长的休假日,每次休息8日。关于考查和考试制度,他提出建立学时考查、学日考查、学周考查、学季考试和学年考试。其中学年考试最重要,合格者可升级,不合格者要重修或勒令退学。可以说,现代学校的运作模式,在夸美纽斯那里,已基本完备。
四、关于德育
夸美纽斯非常重视德育。他在《大教学论》第十一章“在此之前没有一所完善的学校”中写到,“虔信与德行是教育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可是最被忽视。在所有的学校里,……这种科目只占一个从属的地位,因而在大多数情形之下,……学校培养不出合乎德行的品性……”教书育人,最重要的是育人,德为首,似乎各国,各时期都如此。宋代的陆九渊就说过,“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做个人”。
夸美纽斯认为:“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所谓“健全的判断”,亦即正确的判断,就是能明辨是非。用夸美纽斯在书中所引维末斯的话说,就是不追随没有价值的事物,不拒绝有价值的事物,不责备需要称赞的事,不称赞该受责备的事。而“健全的判断应该从幼年开始练习,这样,他到成年时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正确的判断就可以变成他的第二天性”。
此外,夸美纽斯还认为,德育与习惯密切相关。在《大教学论》第二十三章“道德教育的方法”中,他说:“应当教孩子们在饮与食、睡眠与在床、工作与游戏、谈话与缄默方面的事情,在整个受教期间实行节制。”这样以期使孩子养成好的习惯,而“德行是由经常做正当的事情学来的”,这与中国古代朱熹的“从近处做”的小学教育原则也是相通的,也都是正确的。
依夸美纽斯,我们似可以列一个这样的算式:健全的判断+良好的习惯=美好的德行。
说到习惯,夸美纽斯提出的这个习惯——服从,恐怕会引起争议:“我们应当使孩子习于根据理性去行动,不要受冲动的指挥。……孩子们的行为方式是不能够审慎与理性的,所以,假如能够强迫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先去履行别人的意志,再顾及到自己的意志,就是说,每件事都立即服从他们的长上——凡是想要教导孩子的人,开始就应当使他们习于服从他的命令。”(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夸美纽斯还强调,德育与纪律密切相关。他认为,榜样是德育的主要手段,“父母、保姆、导师和同学作为生活的榜样,必须不断放到儿童的跟前”,但是,他又强调,“榜样之外,关于行为的教诲与规则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谨慎到不让任何恶事得到一个进口,所以,严格的纪律是用来制止邪恶的倾向的”。
依夸美纽斯所言,德育与判断力、习惯、纪律的关系,似可这样阐述:判断力和习惯是德育的内容,没有了判断力和习惯,德育就是空泛的;纪律则是德育的保障,没有纪律,美好的德行就很难养成。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德育工作要注意的地方。
五、关于纪律
夸美纽斯认为,纪律是必要的。他说:“波西米亚有一句谚语说,‘学校没有纪律有如磨盘没有水,这话很对。因为如果你从磨坊取走了水,磨盘就会停止,同样,如果你让学校取消了纪律,你就剥夺了它的发动力。”所以,夸美纽斯强调,“犯了过错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但是,夸美纽斯又说:“严格的纪律不应当在与学习或练习有关的事情方面去用……。”因为,在他看来,在学习方面“施用任何强力的结果是只能使人厌恶学问,不能使人爱好学问。所以,我们每逢看见有人心灵受了伤,不爱用功,我们应当用温和的疗法去除掉他的毛病,绝对不可采用粗暴的方法”。
所以,夸美纽斯认为:“只有是道德方面的过失才能采用一种比较严格的纪律。”严格到什么程度?夸美纽斯认为,可以体罚,“假如某些人没有受到温和方法的影响,就必须求助于比较粗暴的方法……有一句谚语说‘责打是改良一个夫利基阿人的唯一方法,这句话对于好些人无疑是很有效的”。不过,夸美纽斯也强调,“这种极端的方法不可用得太随便、太热心”,“要到用尽一切方法之后,才能宣布一个学生不堪造就”。
因此,夸美纽斯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来说明纪律的形式。他说:“天上的太阳把纪律的最好形式教给了我们,因为对于能生长的万物,它都不断地供给光与热以及常常供给雨与风;它也供給闪电与雷,不过次数很少,虽则它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夸美纽斯认为“教学论是指教学的艺术”,又说明他的《大教学论》“就是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而他写作《大教学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却可以多学……”好像这只是一本关于教学法的书,但其实,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教育学,教学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大教学论》是一座宝藏,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文字生动优美,特别是贴切、精美的比喻与类比,俯拾即是,应接不暇。读这本书,如在山阴道上行走,心旷神怡。所以,它值得每一位教师去读,认真地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