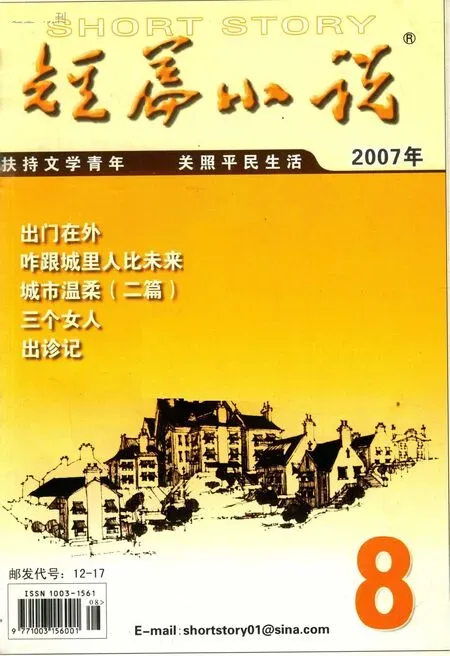姥姥的葬礼
◎葛有杰
姥姥的葬礼
◎葛有杰
一

那个雪天,姥姥迈着她的三寸金莲走了。
生前,她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我走那天要下大雪,出去(下葬)的时候,天又晴了。没有人会把一个老太太含糊不清的絮叨放在心上,到了她这个年龄,都有点怕死也最喜欢谈论死,说的做的都是“我死之后”的事。其实她走那天,就是如她所说的是个“下雪天”,大舅、二舅、大姨以及我的众多老表们都认为那只是一个巧合。天气的事,气象台都把握不准,一个农村老太太岂能预言得了?
姥姥具体的去世时间是个谜。那一天,大舅全家和媒人正在堂屋里商量二老表的婚事。二老表和齐庄的一位女孩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相恋。那个女孩我在二老表的QQ空间里见过,长得很漂亮,远看有点杨幂的味道。二老表曾拿着女孩子的照片给姥姥看,姥姥勉强抬起头,看了一眼照片,摇了摇头。“太瘦了,小屁股,生孩子不容易。”姥姥嘟囔了一句。这是姥姥生活经验的总结,小屁股的女人生孩子难,髋部窄小,生孩子时容易发生交通堵塞。二老表只是想在姥姥面前显摆一下他女朋友长得漂亮,并不是来征求长辈意见的。这个时候,姥姥对家庭成员的爱情婚姻失去了话语权。
大舅托媒人到女孩家提亲,女孩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看不上大舅这个家庭,大舅家主要收入就是打工,日子虽然过得还可以,在乡下属于一般家庭,家里又有一个快百岁的老人。这个家庭配不上女孩的美貌。
婚事搁置了半年多,二老表又出去打工了,偷偷和女孩联系。这不,女孩怀孕了。女孩的父母慌了,要在女孩肚子大起来之前把她嫁出去,在农村这是很丢人的事。托媒人主动和大舅联系,商量两个孩子的婚事。大妗子当即把原来准备好八万八彩礼减少一半。他们在堂屋里商量什么时候换帖,什么时候结婚,结婚时买哪些家具?屋里弥漫着欢快的气氛。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的姥姥不知道什么时候闭上了双眼。
老人去世时儿孙竟然不在身边,乡里人会把这件事当作丑闻咀嚼很长时间。于是,大舅杜撰了一个姥姥去世的准确时间,2014年12月11日上午11点25分。其实那是二老表婚事确定下来的时间点。后来我无意间发现那一年的第一场雪也是这个时间点开始下的。
姥姥活了九十三岁,活着活着就成了将军寺年龄最大的人。原先,还有一队老太太老大爷在她身后跟着,走着走着,就有许多人掉队了,后面的人越来越少。姥姥回头一望,孤独感油然而生,能和自己唠嗑的人寥寥无几,不知哪一天,自己也会从这个队伍中消失。
她变得敏感,亲人们都有意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每件事她都要发表发表意见,她的意见无论是正确的抑或错误的,都没有人理睬。她的权威随着她年龄的增长消失在无尽的岁月中。她坐在大舅的大门口,望着大道上人来人往,眼神浑浊,没有人读懂她眼神中包含的故事。要是一听到有悲伤的唢呐声响起,根据唢呐声的方向,她会问我,“谁又走了,是铁柱还是钢柱?”我说这个是铁柱,铁打似的身体说没就没了。那个钢柱在新疆发了财,最后也死在新疆了,尸体也没有运回来,没能葬在将军寺。她听后,迷茫地望了望昏黄的天,无助地低下了头,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隐藏在她深深的皱纹里。在她的脑海里,有一张表格,全村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已去世的、即将去世的、身体健康的都清晰地印在上面。所以姥姥能大致猜到是谁走了。
她很孤独,她的亲人们都在忙,哪有时间听她讲话?听她絮叨一个小时,少挣一百多块钱呢。现在的时间是用钱来衡量的,例如,大舅在郑州打工,一个小时一百二十块钱;二舅开物流公司,一天能挣好几千;大姨在郑州开个小店,一天也有几百块钱的收入;我写小说,十天半月写一篇,要是发表的话,能得到稿费千字30—50元。单位时间内,挣钱越多的人,对时间越珍惜。所以,我有的是时间听姥姥絮絮叨叨。听姥姥讲话,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她语速较快,声音较低,含糊不清,语言组织能力较弱,词语和现代社会脱节,有些词需要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才能听懂,例如,她把乡党委政府说成公社;把稀饭称为“糊涂”;把早晨叫做“清岛”,馒头叫做“发面卷子”。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碗稀饭。从她嘴里出来,就成了“今清岛起来,我吃了一个发面卷子,喝了一碗糊涂。”她一旦打开话匣子,就不愿收住,一件小事,循环播放。她讲话的内容以及她那不悦耳的声音混合着她身上难闻的味道,给听者带来极不愉快的感受。有些人出于礼貌出于假装的孝顺,坐下来听她讲话,听了一会儿,赶紧借故离开,去忙挣钱的事。年轻人不愿意听她讲,愿意听她讲的那些人,要么走了,要么躺在床上不能走路。她一生经历的事,她对人生的感悟,她对这个世界想说的话,她能说,却没有人听,这是最深的孤独。
和所有的老人一样。姥姥对自己的后事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安排。她经历过村里一些老人的葬礼,他们的亲人哭得很悲伤很响亮很像那么回事,但是他们给死者买的棺材是薄的,寿衣款式不好看质量也差,好多该做的事没有做,该买的东西没有买,好多不该省的程序都省略掉了,一套完整隆重的葬礼被这些“不懂事”的人给弄得七零八落。看到这一切,姥姥的心凉了,害怕了,亲人们的承诺靠不住,生前许的杠杠的,死后的承诺都打折。看来,自己的丧事还要靠自己。
所以,余下的岁月里,姥姥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态度是相当地坚决。她首先绣了一双精美的鞋,这种鞋在寿衣店里买不到,因为现代没有裹足的,姥姥眼睛花了,手也发抖了,真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做好后,装在一个鞋盒里,时不时拿出来试一下,很合脚,姥姥很满意。寿衣店里卖的那种,穿上不合脚,不好看,到了那边能稳当走路吗?她把亲人们逢年过节给她的钱、卖破烂的钱、政府给她的补助……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来,一共一万二千元。她用这笔钱买了一口高大上的“活”(棺材)。木材是金丝楠木的,棺材的上盖六寸厚,两箱帮各六寸厚,底六寸厚。首尾刻有“双龙戏珠”等浮雕,华贵讲究。这口棺材在将军寺行政村及其附近村庄都是一流的。棺材是姥姥到了那边的房子,能不讲究吗?他指挥大舅,把她的棺材放到她睡觉的屋子里,下面用砖头垫起来,上面铺上新塑料布。“我如果活到一百岁,公社就给我发百岁补助,我就能买一个比这还好的。”姥姥含糊不清地絮叨着。大妗子笑吟吟地说,妈,不缺吃不缺穿的,你就好好活吧您,肯定能活到一百岁。其实,我明白大妗子的心里话,老太婆,你想得美,你要是活到一百岁,还不把我耗死。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她也准备好了,什么噙口钱、蒙面纸、麻绳之类的,她怕子女们到那时一忙给忘记了。她把这些硬件准备妥当后,也想对子女、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生活安排安排,但有些事她无能为力。例如,我母亲五十三就去世了,她对母亲的一切愿望成了一场空;例如,她多次说让我赶紧找个媳妇,生个孩子,可是我今年三十五岁了,还是单身狗一只;例如她想让大舅、二舅、大姨之间的关系像以前那样融洽,这能如她所愿吗?
二
大姨第一时间从郑州赶回将军寺,还是没有见到姥姥最后一眼。这是大姨的失误,其实大姨在姥姥身边十多天了,但最后时刻,大姨缺席了。姥姥已处于弥留之际,但是还能吃点流食,眼睛还在转,还能用点头、摇头、绷嘴、眨眼睛来和看望她的人交流。这种状态已持续了十几天。都知道她快要走了,但是谁也把握不准那个准确的时间点,目测,姥姥还能坚持个十天半月的。大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回郑州的,她准备把郑州的事安排一下,拿些换洗的衣服和手机充电器之类的东西,再取点钱就赶回来。谁知她刚到郑州,姥姥就走了,这就是命运。
姥姥经常唠叨,“我有两个闺女,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死了。”大姨没有死,在郑州活得好好的。“她要是没有死,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她要是回来了,我也不会见她的。”姥姥赌气地说道。
大姨也有苦衷,将军寺不是想回就能回。
大姨的一生充满坎坷,姨父的父亲于柏龙是陈州城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权倾一时,办成达中学,办纱厂,开当铺。南关有一条大街都是他们老于家的财产,于柏龙为人奸诈刻薄,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解放陈州城时,又杀害了许多革命志士,最后被人民群众设计乱棍打死。县志上是这样写的,江湖上也是这样流传的。但在老于家的口中却是另一版本。于柏龙清正廉明,乐善好施,积极抗日,办学校招收了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著名抗日将领xxx就是他的学生。现在的实验小学就是在成达中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办了很多实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到了姨父谈婚论嫁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人人喊打的地主羔子,被下放到将军寺。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公社分给他一块地,紧邻将军寺沟,低洼贫瘠,是一块没有人愿意要的土地。姨父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收获寥寥。姨父一边种地一边跟着收音机学习英语,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再后来转正调到了镇上的职业高中。这个时候,经人介绍,他认识了离过婚的大姨。
大姨和前夫结婚时,姥姥就反对,大姨性格倔强,前夫性格也倔强,同“性”排斥,“他们过不好。”姥姥说。果然,大姨生了两个女儿后,无奈离婚。离婚时,姥姥又劝,能不离就不离,两个人过日子,棱角磨平了,日子就过圆润了。大姨性格倔强,仍然不听。大姨的二婚姥姥也很纠结。面前这个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高中语文教师曾是陈州城于家的三公子,如果再有“运动”,大姨会不会受到牵连?姥姥看不透当时的世事,把握不准历史走向。一次次运动让姥姥心有余悸。大姨三十多岁了,离过婚,身材不高有点胖,在农村要想再找个好婆家并不容易。在姥姥的纠结和众人的祝福中,大姨结婚了。
大姨随姨父搬到了镇上,学校分给他们三间房,三个表弟相继出生,姨父请父亲、大舅和二舅帮忙又建了一间房,作为厨房。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大老表于大海在郑州开个艾诺婚纱摄影工作室,日进斗金;二老表于大陆农学院毕业,擅长治疗猪传染性胸膜炎,技术精湛,成为豫东一代的名兽医;三老表于飞翔在外企任高管,月薪上万。三位老表年轻有为,海陆空齐头并进,老于家这一支又兴旺发达起来。他们把大姨和姨父接到了郑州,享清福去了。他们在郑州扎下了根。
大姨和二舅有很深的矛盾,和大妗子又相互看不惯,激烈地吵过架。大姨回来看望姥姥时,就把姥姥接到镇上去,两个人住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惯,生活理念不一样,大姨的脾气就像一颗易燃的炸弹,姥姥一句不合适的话,就把大姨的火气点燃了。姥姥仗着长辈的身份,想让大姨对她服服帖帖。她俩时不时也会爆发激烈的争吵,每次争吵,姥姥就会翻旧账,会用一系列的排比句来否定大姨现在的生活,一连用四至五个“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你会是现在这个样吗”,等等。姥姥给大姨设计了很多条生活路线,但是大姨一条也没有走,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走到了现在。大姨反唇相讥,“我现在过得不好吗?你看看你,哪个媳妇耐烦你?”“我媳妇对我不好,那还是我媳妇,你呢,连个媳妇都没有”。这句话戳到了大姨的心尖上,三个儿子虽然事业有成,但要么不愿结婚,要么不愿意现在找对象,要么女朋友要求在郑州市区买大房子。大姨近七十岁了,抱孙子的梦想越发扑朔迷离。姥姥仍然不解恨,矛头又对准了我,“那个青海,也不知道整天干的什么事,连个老婆都找不到”。吵着吵着,大姨和姥姥都哭了起来。
两年前,姨父供职的职业高中由于位置偏僻,留不住教师,生源不足,倒闭了。当地政府把这二百亩地的学校卖给了开发商。大姨家的那四间破房子被夷为平地。姥姥想让大姨回来,可是大姨回来后住在哪呀?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大姨失声痛哭,瘫倒在姥姥的床前。大妗子、二妗子和一众女眷陪着大姨大声哭。哭声的高低代表着女眷孝顺程度的大小,哭声越高,时间越长,代表越孝顺,反之亦然。葬礼也是一个舞台,是儿媳们在亲朋面前展示孝心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大妗子握着脚脖子,坐在地上痛哭流涕,“我的那个亲娘哎,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你走了让我可咋活呀!”;二妗子不甘示弱,声音更高更尖,“我的妈呀,你咋说走就走了,我还没有伺候够你呀!我上哪再见我的亲娘呀!”
大妗子、二妗子和其他旁院的妗子哭声虽然高,但表演浮夸,不走心,是一种程式化的哭。大姨的哭是失去亲娘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我握着大姨的手,看着大姨有些陌生的脸庞,我不禁痛哭起来,我想起了五十三岁就去世的母亲。
三
大舅和二舅的矛盾是逐渐攒起来的,俗话说,有一好必有一恼。大舅和二舅、大妗子和二妗子关系以前是杠杠的,谁家有忙活,不用请就去帮忙。收庄稼一起收,种庄稼一起种,做了好饭一起吃。之间的小矛盾被乡村的面子所掩盖,亲弟兄闹矛盾会被乡邻看不起。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家突然忙了起来。时间就是金钱在乡村被证实了。大舅一家全员出动外出打工,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二舅在县城开服装店,后来又加盟一家物流公司,生意红火。按理说,生活条件好了,关系应该更和谐。以前关系走得近,小摩擦忽略不计。现在不生活在一起了,大妗子和二妗子之前的点点滴滴有空间发挥了。“我以前对她那么好,有一次她竟然……”“那一次我赶集给他儿买了毛衣,她买衣服时就不想着俺儿,太不像话了!”妯娌之间的矛盾多多少少也影响到大舅和二舅的关系。
在姥姥的葬礼上,这种矛盾彻底地爆发了,利益冲破了面子。
养儿为防老,在乡村,赡养老人分三种模式:
一种是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就别无选择,老人就跟着儿子了,碰到恶儿媳就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第二种如果有两个儿子,两个老人一家承包一个,负责老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另外一个老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与自己无关。如果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儿子,那就轮流伺候。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一轮换。不知哪位高人在电视上学到一个新名词,老人到了谁家,那家就被称为“轮值主席”。
姥姥这一家符合第二种赡养模式,一家一个,公平公正公开。但到具体的操作上又出现了新问题。分家的时候,我爹我娘,我大姨和姨父全体到位,这个时候他们要在场,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他们的意见压根起不到作用。
相互推让一番后,还是由老大先挑。大妗子挑了姥姥。姥爷留给了二舅家。两个妗子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不管怎么分,只会把矛盾激化,都认为自己吃了很大的亏,是世界上最冤枉的人。
姨父是知识分子,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强烈反对这种赡养方式,认为这是不合适的,没有人道主义的,缺乏人性关怀的。“把老两口生生分开,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呀!”
只有孩子对不起父母,父母从不欠孩子什么。
大妗子看似很随意地挑了姥姥,其实,她是做足了功课,反复比较、假设、推理,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综合考虑后慎重做出的决定。
姥爷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失去了创造价值的能力,地里不能干活,家里不会做饭。反观姥姥这时身体还很硬朗,能独挡一面,支撑起一个家庭。大妗子相当于请了一个免费负责任的保姆,自己也能外出打工挣钱了。这一里一外,一反一正,大舅一家确实占了很大的便宜。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姥爷没过几年就去世了。二舅一家轻松摆脱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凝神聚力谋发展,物流事业干得红红火火。姥姥越来越老,渐渐地失去劳动能力,整天坐在门口,手里拿个棍,一是用来支撑身体,二来驱赶别人家的鸡子。大妗子只好留在家里操持家务,伺候姥姥。大妗子觉得选择姥姥是最大的错误,对二舅一家不满,对大姨不满,对已去世的我母亲不满,对这个世界不满,怒火只好发泄在姥姥身上。有亲戚去看望姥姥时,大妗子表现得很孝顺,是个贤惠的媳妇。但日常生活中她对姥姥的态度,经数人辗转,传到我的耳朵。
四
几年前,姥姥拄着拐杖,迈着她那独特的三寸金莲,把将军寺的领土都巡查了一遍。别人以为这个老太太心情不好,坐得久了,出来散散心呢,一些小伙子还给她开玩笑,“老太太,您小心点,别摔着了,摔坏了你大儿媳可不伺候呀。”姥姥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不愿意理他们,拄着父亲给她买的龙头拐杖慢慢向前走。其实她不是在散心,她是在给自己寻找最后的归宿地。多年的乡村生活,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她学会了怎样看风水,一个好的坟地风水再加上积善之家有后福,子孙后代荫福荣享,风水的优劣直接影响家人的财气、官运、后代升学、康健寿命等。给这个家族能做的最后贡献,就是把自己埋得好一点。姥姥给自己选择的墓地在志官家土地南头。前面是颍河的一条支流,叫将军寺沟,背后是一片高地,墓地入口朝向东南,前面无大树遮挡。可以说是背山靠水,“山管人丁水管财”。是典型的风水宝地。姥姥寻找到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就捣鼓着大舅去给志官换地。大妗子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志官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嗜赌成性,三十好几了还没有讨上老婆。胡子不刮,衣服不洗,整日蓬头垢面,饥一顿饱一顿的,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更别提伺候土地了。他的那块土地简直丢农民的脸。杂草比庄稼都要旺盛。还不如姨父家那块地呢。姨父家的那块地是天然贫瘠,营养不良,也无法改良,是上天注定的。志官家的土地是人为造成的。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土地是有感情的,是有生命的,是懂得感恩的。你不给它施肥,你不去陪伴它,它凭什么给你沉甸甸的收获?
拿自己家的肥沃的土地去换那样的一块地,傻子才会那样干呢,每亩地最少减产100斤小麦,这个老太太看来糊涂得不轻呀!姥姥悄悄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关键是这块地能保佑我们子孙兴旺啊!”子孙兴旺!这四个字说到了大妗子的心尖上。大妗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二妗子也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分上下,打了个平手。如果自己的孙子比老二家的多,说话也就多了一些底气,这也是一种胜利。
大妗子批准了这个置换土地的方案。大舅带着礼品和志官一说,志官也晕圈了,老大他是想干什么,为什么要和我换地,老大两口子尖酸刻薄的样也不会是学雷锋。这里面肯定有事。突然降临的好事让志官这个光棍不敢接受,吞吞吐吐地拒绝了。还随便编了一个理由,“我这块地是风水宝地,我死后准备埋在那,可以保佑我多子多福呢!”“呸!连老婆都没有,你怎么多子多福?”大舅心里明白,像志官这种货色,你主动找他办事,不让他看见实实在在的好处是行不通的。大舅一咬牙,第二次去了志官的家,这次手里多了一条“红旗渠”和一件“青岛啤酒”,又拍在志官桌子上五百元钱。看在烟酒和钱的份上,志官同意换地了。
我上过大学,还差点入了党,可以说是受了十几年的党的教育和熏陶。根本就不相信风水啦、神啦、鬼啦之类的封建迷信。我信奉的坚持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强的唯物主义观念。但是,对乡村这些流传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也没有底气反对。在将军寺这片大地上,有许多事不能简单地归为封建迷信,一些事用科学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将军寺原来有一座占地近百亩的大庙,始于汉,兴于明,香火鼎盛。庙里还有一位高僧,庙前有一棵大白果树,有几百年的历史,大得很。有一年,将军寺举办小满会,请县豫剧团来唱戏,有个瞎子听说白果树很大很粗,就把盲杖放到树的一旁,用胳膊围着这棵白果树开始量,摸到盲杖为止。围着这棵大树他转了整整一上午,逢人便讲“乖乖,这棵树真大呀!”其实是别人把他的盲杖偷偷拿走,听戏回来,又把盲杖放在树下。到了文革破四旧时期,大队干部把庙给拆了,种上了小麦;白果树砍了,给县高中做了课桌;把老和尚也给赶跑了。老和尚走之前说了一句话,“罪过,罪过,你们会得到报应的。”拆庙、砍树、赶走老和尚的是姓白一大户人家干的。此后,这个村姓白的中年劳力相继死去,死因各种各样,有出车祸的,有病死的,有淹死的,还有从房子上掉下来摔死的。有人统计过,姓白的那个家族几年之间出现了三十八个寡妇。白姓人害怕了,在大庙原址上建了一小庙,算是稳住了霉运蔓延的趋势。
姥姥的选择差点动摇了我多年的信仰,自从姥姥选好自己的墓地之后,大舅家的大儿子一下子生了四个儿子,二妗子两个儿子总共才贡献两个孙子。大妗子一个儿子贡献的孙子是二妗子两个儿子贡献的两倍。果然是多子呀!多福不多福另当别论。大妗子喜欢得眉开眼笑,我大老表掰着手指头细细一算,眼泪差点掉下来。在乡下,娶媳妇要盖楼房,这是标配。一栋楼房连建带简装修最少二十万,四个儿子,八十万。彩礼按最低标准六万来算,四六二十四万。大老表在四个儿子成人之前最少要攒够一百万才能完成他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姥姥选择的这块墓地风水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在将军寺,懂风水的人不在少数,看上这块风水宝地也不在少数。但是这些老人没有姥姥有前瞻性,没有付出实际行动。这里的风俗是先入为主,先死为大,按照死亡先后顺序有序入住,死得早运气就好,能埋个好地方。但是姥姥的这一举措打破了古老的顺序,破坏了规矩。姥姥是这一批老人最后离世的,理应埋在风水较次的地方。你在阳间活的时间长,死后又占了最好的风水。阳间、阴间的好处都被你占了,这不公平!
到了那边,这群老太太、老大爷会不会联合起来欺负姥姥?他们去跳广场舞不带着姥姥,姥姥会不会很寂寞?
天上飘着雪,我们一行人来到姥姥几年前就选择好的要永眠在此的这片坟地。举行个简单的仪式,烧一些纸钱,磕几个头,由大舅亲自挖前三锹土。做完这一些,村里的“百事通”永良一挥手,十几个年轻小伙开始给姥姥打坑。看着姥姥的墓坑,大姨坐在雪地里又大哭起来。
五
姥姥给自己准备的丧葬用品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些物品从箱子里、柜子里、床底下、墙上被取下来,花花绿绿摆满了一地。个个有种被欢迎出场的喜悦感。殊不知,它们将随姥姥一起永眠于地下。物品的丰富程度让“百事通”永良也大吃一惊,自己操持过这么多的葬礼,这是准备最齐全的一次,把这些物品用到该用的地方,就是一次完整的乡村葬礼程序,是一个难得丧葬的典范。永良心想,老太太是有福气呀!不知道自己死后葬礼会是什么样子?叹口气,急忙又去忙其他事去了。
由于下雪,姥姥的葬礼遇到了不少麻烦。大舅冒雪要去给亲戚们报丧,一到村口,见了人就跪在雪地里磕头,不管认识不认识。到了亲戚家,亲戚就会略带悲伤地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大舅就把准备好的台词拿了出来,是昨天上午11点25分走的,早晨还喝一小碗小米粥呢。亲戚说,节哀顺变,俺姑奶走了,也就不受那份罪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罪了。
确实,姥姥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受罪。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吃饭,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大小便失禁,后背都捂烂了,往外冒黄水。大姨把成人纸尿垫给她放身下,一动她的身子,姥姥就会发出尖利的呻吟声,她已失去了语言功能,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身体上的疼痛。在姥姥的床边,围着不少她的亲人,但是谁也不能替她承受这种痛苦。
大舅报丧回来,衣服被雪给浸透了。
最后,出口热度降温,印度尿素招标结束后的沉淀期再遇国际尿素价格跌势,至于11月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以及印度的尿素采购预期尚未明朗,且对近日震荡的贸易商报价或有博弈情绪。
由于下雪,大舅不能到每个亲戚家去报丧,就翻着电话本用低沉的声音和着屋里的哭声给亲戚们报告消息。亲戚们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哭声又联想到姥姥的年龄,不用大舅再陈述事实,也就明白了十之八九。
将军寺的人就不用再通知了,他们一听到哭声,就主动聚拢过来,听从永良的调遣,谁去镇上采购物品,谁放炮让烟,谁接待客人,哪些人去挖墓坑,哪些人抬棺材……永良根据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身体健康状况做了合理的分工。领到任务的村民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一场葬礼不只是大舅家的事,也是全村人的事。红事请,白事围,谁家有丧事,全村来帮忙,这是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如果谁家有白事,大家伙都不围上来,说明这一家在村庄里差劲到了极点。
近年来,由于青壮年大多出去打工,可供永良派遣的人越来越少,有时,一些年龄较大的人也要参与抬棺材这样的重活。
二舅躲在里屋,掏出手机,连上数据,用QQ、微信等方式向自己的朋友们报丧,在微信群里也发了讣告,并提醒朋友们来吊孝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由于下雪,永良指挥人把大舅家的院子用塑料布给搭了起来。大门口是办公区、财务区,俗称“柜上”,来宾们的份子钱就交到这里,永良坐在桌子后面,用隽秀的小楷写到:王庄,王有財,鞭炮一挂,礼金100元。院子的西南角是伙房,请来的厨师正在煎炒烹炸,散发出阵阵香气。对着堂屋门口,是灵棚,两边有一副挽联:梦断北堂春雨萱花千古恨,机悬东壁秋风桐叶一天愁。中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张姥姥的照片,照片出自郑州艾诺婚纱摄影老板于大海之手,由于照片是翻拍加工而成,照片上的姥姥要比现实中的姥姥年轻得多,精神得多。
为表达孝心,大舅原计划请县豫剧团来唱一天戏,但是由于下雪,剧团方面要价是五千元,大舅又考虑到天气冷,来听戏的老年人不会太多,只好作罢。二舅为了排场,拟个人出资请县城的红玫瑰劲爆歌舞团来激情演出,这个荒唐的想法遭到姨父为首的亲人们一致拒绝。
堂屋里,放着那口棺材,由于姥姥措施得力,保护得当,棺材没有虫咬鼠啮的痕迹,表弟用胶水、石膏搅拌均匀好后填棺材缝隙凹陷的地方,干后用纱布打磨,棺材里面刷上红色,外面刷上黑色,刷好后再用石膏补补,用砂纸打磨光滑平整后再上一遍清漆。好棺材就是好棺材,往那一放,气宇轩昂。棺材旁边有张小床,上面躺着我的姥姥。床边跪满了她的子孙们。
回顾姥姥这一生,十几岁结婚生子,把四个孩子抚养大,没有清净几天,一大群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蜂拥而至。大姨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也是由姥姥一手带大的,我和于大海也是姥姥的跟屁虫。大舅和二舅各三个孩子,要一视同仁,不能偏心。到了老年,老表的四个混小子又给姥姥带来不少麻烦。照顾孩子,照顾孩子的孩子,照顾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终于换来了这一大片哭声。
祭奠前,灵棚下方桌两侧各一人,为奠人祭酒时倒酒接壶。棚角站一人,应祭奠人执拱手礼,祭毕同样拱手施礼喊棚下众孝子谢祭奠人,叫站棚角。另有一人安排定顺序请客祭奠,叫引奠人,后跟一人手端木托盘,托盘上放折花三园纸筒一卷。引奠请上祭人时要喊:有请××地方客人××人上祭,等祭奠人过来,引奠人要和祭奠人拱手施礼。棚外要有多少按上祭顺序把客人祭礼供品礼金摆放在桌上。等一家祭完撤去,再摆放另一家的供品祭礼。
一般客祭奠,在门外先和引奠人拱手施礼,进院到灵棚前要和站棚角的也施礼。进棚不跪,先哭着到棺前跪哭,叫窜灵。回到灵棚下,开始行礼,行礼的名称繁多,有九拜礼、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珍珠倒卷帘、十八罗汉、二十四拜等,因人而异,祭跪中间,要到供桌前祭酒,叫转蛊。转蛊后再窜灵,叫双窜灵。礼毕中孝子谢客,与站棚角的施礼结束。祭奠中间凡女儿至亲,都痛哭不止。
祭奠完毕,永良又指挥人把棚拆掉,桌子摆开,开席!这时,人们悲伤的表情稍稍散去。一些相熟的人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吃过饭,送姥姥下葬,这一场持续三天的葬礼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时,大舅和大妗子发现了二舅的一个秘密,并与二舅争吵起来,葬礼暂停。
二舅交际广泛,当过两年村干部,周边村庄的小“土豪”、乡村名流、镇上的基层干部等二舅和他们关系都不错,不定期地坐在一起喝两盅。到县城开了物流公司后,认识的人更多了,其中不乏一些大老板。这些人和大舅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能来,是因为礼节,他们家有红白喜事时,二舅也给他们随礼了。他们的小汽车停在村口,摆了好长,相当壮观。
二舅之前已经提醒过他们,份子钱不要交到柜上,这是私人友谊,和葬礼无关。
大舅不这么认为,这场葬礼是由我家承办的,一切支出也由我家承担,相应的与葬礼有关的一切收入也应归我家所有,这是规矩。
二舅不同意大舅的观点。我的朋友们和你素不相识,他们凭什么要给你随礼,他们能来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几年我四处随礼,等的就是今天,到最后,这些钱你要是收走了,我岂不是亏大了。
大舅气得直跺脚。你四处打听打听,看看哪个村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来的是我家,吃的是我家的饭,抽的是我家的烟,喝的是我家的水,口袋里的孝帽是我发给他们的,啥时候也没有两个“柜上”!
二舅也很生气,咱妈事上我是没有花钱,但是我给朋友们随礼时你没有看到。我总不能替你随几年礼吧?
大舅又翻起了旧账,咱爹事上,我可没有像你这样偷偷收过钱。
那是什么时候,现在又是什么形势,能一样吗?二舅反问。
确实不一样,姥爷是二十年前去世的,那个时候大舅和二舅的关系还很融洽,虽说是二舅家承办的,大舅在人力财力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弟兄俩齐心协力把姥爷的丧事办得圆满。那时来的都是共同的客人,二舅也没有这么多朋友,礼金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收入甚至低于支出。
他俩的争吵打破了葬礼应该有的庄严肃穆悲伤的氛围。一些吃瓜群众对此也展开议论。
甲:要我说,这钱应该交给“柜上”,老大把老太太侍候到九十多岁,不容易呀!老二现在混发达了,不应该在乎这点钱。
二舅收的份子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以二舅现在的经济实力,千儿八百的他看不到眼里。
乙:老二要是不收这钱,真是亏大了,种田种到别人地里去了。
丙:老二也真是不像话,连老太太这种钱都敢收,真是的!
丁:嘿嘿,他俩不会打起来吧!
……
永良赶紧出来劝,他当过村里的支书,清正廉洁,口碑很好,德高望重,辈分也高。自以为凭着自己在年龄和辈分上的优势可以平息这场纠纷。
吵什么吵?老太太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闹,让她老人家怎么放心地走。等你娘下葬后,随你们怎么吵!
永良太高估自己了,在金钱面前,面子、辈分不堪一击。永良气得直摇头,办过那么多丧事,在将军寺还没有人敢不听他的,现在世道变了。
姨父也出来劝,你们的矛盾等咱妈事过去再说好吗?你们现在这么闹,就不怕别人笑话吗?
要搁以前,陈州城的于家三公子往这一站,谁敢说半个不字。现在不好使了。
大妗子停住了哭声,她心知肚明,这件事今天必须得到解决,这是最佳的时机,等老太太一下葬,老二带着钱开着车进城了,还怎么解决?
不下葬就不下葬,反正也不是俺亲娘,今天不把钱交出来,就不算完。大妗子说。
争吵还在继续。
大姨从里面慢慢走出来,突然跪倒在大家伙面前,磕了三个响头。老少爷们,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帮忙把俺娘下葬吧,让老人家入土为安吧,我谢谢你们了。说完,又磕了几个头。
永良赶紧拉起大姨,朝大家摆摆手,说道,各位老少爷们,老太太是我们将军寺年龄最大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有和谁红过脸,她的事就是咱将军寺的事,她俩儿子不管,咱管!老少爷们,来!抬棺材!
村里的人大多是尊重永良的,在这种场合,弟兄俩为了钱这样争吵,不管自己的老娘,这是在丢将军寺的人。
我爸和姨父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抬在前面,悲伤的唢呐响起来,乡亲们抬着姥姥的棺材向墓地走去。
姥姥的葬礼虎头蛇尾,草草结束,准备的丧葬用品,有一些最终还是没有用上,散落一地。姥姥的去世,让这个以她为中心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从此天各一方,也会成为村庄历史上一个事件。姥姥下葬几个月后,颍河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去世的人不再入土为安,要拉到殡仪馆火葬,原来的坟头铲为平地,种上庄稼,将军寺人的生与死,注定和以前大为不同。
六
雪停了,我站在姥姥的坟前,想起以前姥姥对我的百般呵护,不禁泪流满面。
之前我还担心,姥姥占了将军寺最好的风水,到了那边,她的老姐妹会因此冷落她、孤立她。其实是我想多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姥姥对我说,他们很欢迎她,向她打听阳间的事,并没有疏远她,反而很同情她的遭遇。姥姥那个阶段人的思想和现在人的思想不一样,世道变了。
葛有杰,河南淮阳人,周口市作协会员,《涡河》文学季刊执行主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大河报》《河南日报》《羊城晚报》《天池小小说》《金山》《老人春秋》《时代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件。

责任编辑/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