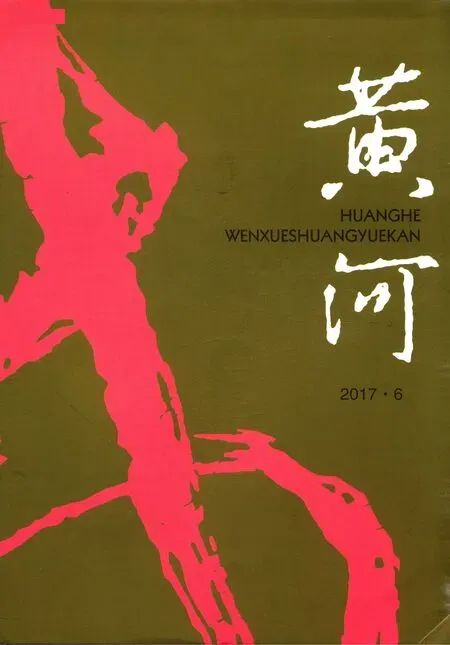一切都隐秘在暗处
燕霄飞
一切都隐秘在暗处
燕霄飞
我曾经在老家郊区有处小院子,大约三分地,五间青砖瓦房,一座挑脊门楼,与周遭邻居的房子连成一片。房子是我父母置办的,在那里我度过了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结束了学生时代,待业,就业,结婚。期间父母搬到了新居楼房里,而我继续留在那里,我和老婆每天将院子洒水清扫一遍。我们在院子里养了一条土狗,几只小猫,种了草莓和西红柿。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出生在那里。
房子内部格局简单,无出奇之处,只是有一盘火炕令我回想至今。那时候,我常常坐在马扎上趴在炕沿上写作。晚上有时候我会干脆匍匐在被窝里,以枕头为案几,写累了直接休息。一旁妻女发出甜蜜的轻鼾,院子里偶尔一两声犬吠。
邻居们无一例外,全是农户。他们的庄稼地离我们小巷不远,我经常能看到他们挽着裤腿归来,泥巴糊满鞋子和小腿肚。一度时期我总以为,他们一定视不事稼穑的我们一家为另类,事实上很长时间也的确难以相处融洽,我们家门口时常有鸡粪猪粪,甚至出现人便溺的痕迹。当我领着孩子路过正坐街的邻居们身旁时,孩子会不由自主地紧张得迈不开腿,我也很尴尬,跟他们打招呼时无非“忙呢?不忙,吃了?吃了”,就这么几句。曾经有一个光棍汉邻居径直敲开我家的门,理直气壮地向我们要钱花。我父母每次打电话来,总不忘叮嘱几句:晚上一定要把院门从里面锁好。
事情从什么时候有所改观的呢?难以说清。我妻子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从外地跟我回到家乡,此后她一直生活在我们那里,以教孩子们画画为业,直到现在。我每周从省城回去跟她团聚,她对我们那里已经比我还熟悉,比我的熟人要多得多。她否定了我要让孩子去省城读书的想法,也不同意由我父母帮着带孩子。她说她能搞定这一切,她认为我们的孩子突然间到城市去生活,会迷路的。她认为我们俩即便分开很久,因为有女儿在这里,有老人在这里,有她在这里,像小孩般单纯的我才不会忘记来路和归途。她是个有韧劲的女人。在我不常在家的日子,她跟农民邻居们相处得异常融洽,有一位长她七八岁的妇女,跟她简直成了好姐妹。渐渐地,我发现回去之后,跟邻居们交流没了什么障碍,我了解了他们更多的事情,也曾经去他们庄稼地里帮忙掰过玉米,几位邻居家办喜事儿,认为我算个笔杆子,还让我充当了几回账房先生。我妻子那位好姐妹家翻盖新房,我甚至还赤着脚去跟庄稼汉一起“夯地基”,我们把裤子挽到大腿根儿,彼此摽着光膀子,一起赤脚在松软的土地上跳跃欢呼,像跳大神一样,边跳边吼唱着不成调儿的号子,直到泥土板结、硬实,直到可以当作地基使用。
我还清楚记得那天晚上跟他们一起喝酒的情形。我妻子那位好姐妹的丈夫,往后我客气地称他为“哥”的中年汉子,为了他将要为儿子娶亲而落成的新居,也为仅仅有机会跟大伙畅叙心结,喝了许多酒。我们都喝了许多酒,我是被我老婆背回家的。
并不是说我跟他们就此成了朋友,没有,我承认,到现在我跟他们依然保持足够的距离,依然不能做出他们认为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情,如果我的孩子沾染上他们孩子的一些习气,我会很生气。当然,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淋着雨去看望一窝偶然发现的田鼠,花了很大力气从十几里外弄回一截烂树根,只可怜它长得丑,诸如此类,也会被他们嘲笑。这也是我后来将院子卖掉,离开郊区,离开那条小巷,而住到现在的小区的原因之一。我知道,交通不便,取暖不便等理由都很虚弱。
我想,我只是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情感,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态,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日常琐碎,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故事,知道了他们心中的所想所盼,理解了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理解了他们在利益取舍、道德纠缠方面为什么会那样做而已。
我并不能让自己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我不能简单地用诸如淳朴、善良、勤劳、贞洁或者恶劣、狡猾、奸诈、淫荡等词语来形容他们,我也明白,这些词语不能简单地用来概括我们每一个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管你生活在哪里,城市或者乡村;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教授或者农民;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度、哪个民族。
人太复杂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心理面孔。我曾经跟同样是学美术出身的妻子探讨过,如果给我们的世界画一幅众生像,不需要去芸芸众生中寻找模特儿,只看看我们自己就足够了。
我们俩曾经设想创作这样一幅油画,灰色基调里挤满蚂蚁,所有蚂蚁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但你仔细看,它们的身体里盛满人体的各种器官,有代表贪婪的嘴,象征欲望的生殖器,流泪的眼,滴血的手……因此,那些蚂蚁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的。但这幅画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觉得,蚂蚁的形象还没有在我脑子里清晰起来。俯下身来观察蚂蚁也很累的。
那些生存,那些行走,那些喧嚣,那些躁动,那些挣扎,那些叫喊,是不容易被看到听到的,不容易被世界的主宰者注意它们的。将一秒钟一忽念的思想停留在它们那儿,将一根线一缕蛛丝那样的情感停留在它们那儿,都是不容易的。
然而任何形式的艺术,如果不表达这些东西,还要表达什么?还想表达什么?还能表达什么?
不管艺术家的技巧到了哪个段位,修炼出多少根蜈蚣一样用来支撑行走的手足,他聆听暗处声音的耳朵不能关闭。
除了喜欢美术之外,我还喜欢诗歌。我觉得诗歌是人类最直接的声音,犹如婴儿降生时的那声啼哭,所有的表达方式以及所有该表达的内容都在其中。
我曾经跟一位同事、一位真正的诗人,在喝酒后吹牛说,我骨子里其实也是个诗人,是个写小说的诗人。事实上我认为不管是操持文字的,还是搞视觉艺术的,搞音乐的,他首先应当是个诗人。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搞怪的一句话,说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写诗的诗人,一类是不写诗的诗人。我觉得说出这句话的家伙比我还要傻得可爱些。我看到这句话时就开始为他担心了。我想告诉他,要小心一点了。按我的经验,正如我妈教给我的那样:想哭的时候就回家转转。
燕霄飞,山西定襄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藏孤记》,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西省文学院第三批签约作家,《黄河》编辑。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