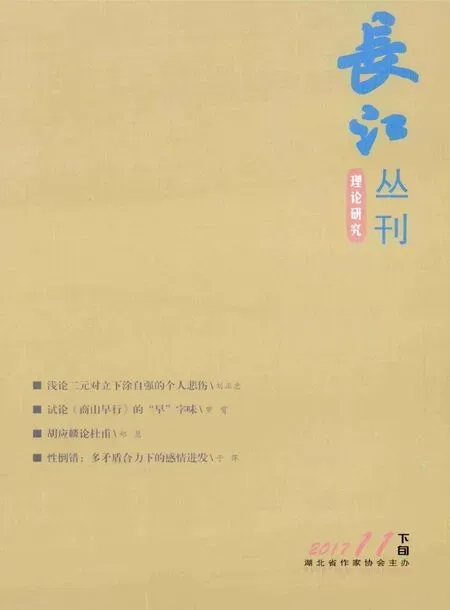天河叙事(五首)
魏荣冰
在坎子山听蝉
如一架云梯,通往天堂
我在云雾里以双手摆渡
云团环绕在身边
堆积一种单向度的白
消弥了世界的对立性
我体内的黑白二元结构
构成了与一座山的对峙
危石如累卵,比岁月更稳定
作为呼应,我交替伸出双手
试图抚平胸间涨落的潮水
与身体的日渐陷落相反
一座山带来新的海拔
沿着九曲山路吃力地攀爬
坎子山牛角般的峰峦
抬升一片惊世骇俗的蓝
蝉鸣是坎子山唯一的路标
童年时与我厮守每个夏天的蝉
它们用坎子山独一无二的元音
颠覆了我三十年的生物学认知
以及在城市里虚构的优越感
流过小城腹部,向南拐弯
乡音、跌宕身世和多变心思
淤积,长出炊烟和离离禾黍
如你所知:生命里布满水声
斟一杯湛蓝,擦洗日子和天空
北纬三十三度,一只白鹭降落
自由落体,摇晃万物的映像
小女孩儿
白鹭飞来的这条河流
有着动人的速度:生命在于节奏
昨夜的秘密装进蔷薇色的信封
打开丛生的新事物:列队加入
一段山脉隐居在目光尽头
像一个不习惯打扮的人,颈项间
围着乳白色的六点钟。你
从河水中看到的镜像,更接近真实
树篱修剪整齐,水草漫过
脚踝。晨练的老人拉长了弧度
很多人低头走过,他们心事重重
犹如剧院里正在上演的时光剪影
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儿
在土堆旁,用一小杯水浇灌大地
阳光从石榴树枝叶间漏下
照亮了她金黄色的发丝
南山的青草
母亲每天都去南山割草
四十多个春秋
倒伏在母亲的霜刃下
青草匍匐,母亲匍匐
傍晚,一阵风刮过南山
母亲一声叹息,落日坠落
坠落的还有母亲枯草般的白发
长期匍匐的碎日子停止了
母亲倒伏在南山的土冈上
在大理石和青草的夹角里
摆放着母亲的空竹篮
竹篮里装着弯月亮和矩形星空
南山的青草环绕着母亲
我倒伏在母亲的墓前
在绵延起伏的青草里
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杂草
映像
穿过悬索桥的弧形桥孔
白鹭带来镜子的速度
万物在河水里倒映面庞
循河畔行走的人加入它们
时间是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隔着三月、胸针,以及生死
从天地之间提取一个尺度
每一次疾走,都是为了停留
唯有河流,冲洗柔软的内心
天河叙事
1
在汉语里,姓名是一门玄学
测度事物降临的神性
地球上唯一叫做天河的河流
“驾山而下,如自天来”
在秦岭架设的天梯上
晾晒星斗和云朵的乡愁
一条挂在天上的河流
有着深不可测的身世——
一半在人间,一半在天上
2
天河长着蔚蓝色的脸盘
它的眼睛是雪原上的湖泊
倒映穿着蓝色披风的云
低头饮水的虹,和盘旋长空的鹰北纬三十三度
阳光向大地镀上一层薄铜
秦岭峰峦挂一幅水墨屏风
水声从飞白笔锋里逸出
天河与天堂互为镜台
3
在鹘岭东南山麓,深山药农
以一株绛仙草为天河接生
采药人采到一筐呜咽的泉声
隐居在山川云雾里的水族
在一首民歌的尾音里结盟
像丝绸一样缠绕秦岭峡谷
注入汉江,汇入长江
武当山脚下一片泽国
武当道场仙乐依次拨开丛林
天河沿着千里干渠一路北上
滋养北方干渴的心脏
4
让一条河流改变气质
最佳的方法是在它的体内筑巢
天河是秦岭深山走出来的村姑
有着民间的羞涩
她的纯净如衣领上从未扣过的纽扣
此刻,流过一座叫做郧西的山城
惯于打扮的城市强行联姻
在两岸围上石栏杆,雕刻爱情诗
她的脸上被涂满各种颜色的脂粉
她甚至怀上怪胎——
沙,骨骼,过期药丸,后半夜的空床
5
自然界的美学法则:随物赋形
而人类崇尚暴力美学——
以他人的生命嫁接自己的生命
削平山丘,建造摩天大厦
架桥,筑坝,改堤
把一条河流引向迷途
天河流过郧西县城的臀部
人们凿穿汉江岸边一座山
让天河抄近道跳进汉江
天河故道,筑成亚洲第一沙坝
千年天河老街,用一只门环
叩打锈迹斑斑的午后
6
天河与居住在两岸的子民
有着原始宗教一样古老的约定
天河永远流着它的清
人心永远淌着他的善
炊烟和帆,是人类的信物
涟漪与倒影,是天河的契约
人像一支楔子钉进河床
成为干涸的背叛者
人在一条河里玩蛇
比丛林动物更加凶狠和贪婪
河水流经人类的地盘
变得像人的血管一样浑浊
一条河流无法识别
带着人类脸部特写的狡诈
7
寻找方向,意味着失去方向
像一个人走失在人群中
一条河迷失在另一条河里
浑浊的河水无法洗白一条河的家族史
天河沿岸的森林、田地、城郭
学会了岁月的易容术:失去坐标
我坐在岸边,面朝逝川,背对荒原
从一截血管里聆听涛声
从一寸稻香中辨认岁月
我是被天河遗弃的最后一枚鹅卵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