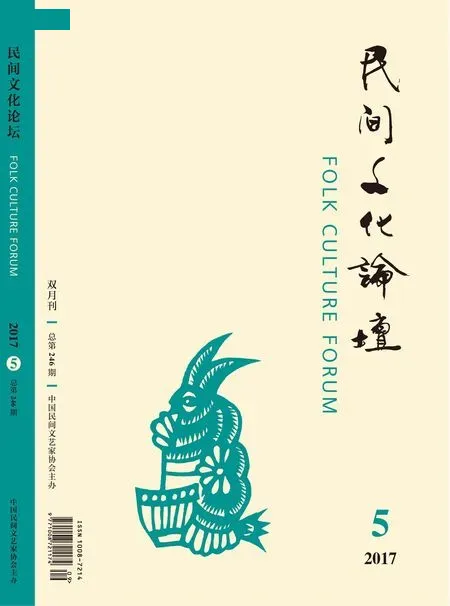都市的认同感
——浴火重生的城市文化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著 吴秀杰 译
民俗研究
都市的认同感
——浴火重生的城市文化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著 吴秀杰 译
城市的兴起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伴生现象;大量人口密集居住的大都市生活造成的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离、犯罪与暴力频发等问题,使得都市成为20世纪现代性批判的靶子,逃离都市一度成为现代人向往的生活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市文化被重新发现和塑造,再度焕发出多样性、包容性、具有多重文化品位的魅力。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都市在打造自我身份认同中再度成为宜居之地,为外来者的社会融合和身份认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本文勾勒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文化变迁的进程:从单调平庸的灰色水泥林,到五彩缤纷的各种社会与文化理念的实验场。
都市文化;身份认同;移民;社会融合;社会实验场
这件“I love New York”红心T恤衫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倾诉了人们对一个城市的热爱。它原本叙述了另外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一段慢慢被遗忘的历史。1972年,当一个艺术家小组设计出这个T恤衫时,纽约这个大城市远远不像今天这样为亿万人所倾慕。它似乎要宣告自己的末日降临:交通堵塞、雾霾、投机和犯罪横行,城市人口在减少。那一句“我爱纽约”是当时尚且留在城市里的人发出的最后求救呼声:“让我们别抛弃这座城市!”

图1 “我爱纽约”T恤衫(摄影 Wolfgang Kaschuba)
我爱……我们!
不过这早已是陈年旧事。如我们今天所见,纽约这样的大都会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充满多样性的文化空间、消费空间和感受空间。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景观和建筑景观遍布城市各处,了不起的技术装备与旅游业基础设施,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它们为不同人群所居住、所使用,这其中有当地人、外来移民、流动人员、旅游者。独有的自我意识与别具一格的精神风貌塑造了这个城市,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整合让它变成了世界之都,变成了某种标记。这种独一无二性给纽约人带来一种身份认同;同时,它又反过来迫使纽约人持续性地扩建城市,从基础设施到文化,从娱乐活动到娱乐价值,以便能让自身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要求城市不得不适应全球趋势,其代价是建筑学上的标准化和文化上的同一化。城市竞争越来越带来自我摧毁的效应。
这一发展模式早已遍地开花,哪怕在中等都市也是如此,连老城区也经常让人觉得是可以替代的、毫无特色。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公司、媒体、旅游者以及当地人来说与地点有重要关联意义的地方认同感陷入危险之中,即那些特殊的体验和设想:在柏林生活会有别于在慕尼黑或者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因为各地的历史、建筑、风光、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
因此,今天的城市推广计划才如此集中而深入地考虑这一问题:如何让城市最终变得不能被错认,什么是它的特殊风格、它的特殊颜色,以及它独此一家的标志。在晚现代时期以及在全球背景下,这些就显得尤为有价值:强调和维护那些真正刻写在该城市中的个性特征,让居民感受到这是“地方精魂”,由此出现一种都市的“我们”认同感。
这些为形成地方性认同感和定位的努力,在最近一些年当中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城市特征。这是一种文化“地标”,城市推广活动和文化专栏是其推手,它们也出现在旅游手册和互联网博客中,也通过电视系列剧和城市流行歌曲、通过图片相册和导游传播出去。城市被当作集体性的行动主体,成为地方性共同体和文化,它们的居民变成了同样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成为都市部落中的一员:他们从先前广袤的都市猎场回撤到隐蔽的保留地,以便能躲开房地产大鳄和建筑修复,躲开追名逐利之徒以及旅游者。人们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和“他人的”世界,移民风格也好,巴伐利亚风格也好,只是为了再度赢得距离和安静。可惜这经常徒劳无益,因为正是这种回撤到“独特方式”的街区和居住区,让观光者和投资者变得更为好奇,因为这种氛围让这些当地人具有都市本真性以及亚文化的殊异性。这些做法让当地人不情愿地掉进了旅游-经济牺牲品的模板中:文化很容易带来自食其果的效应。
赫尔曼广场——柏林
柏林有一个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直到不久以前,这并不能让人感到有什么可激动的。其他德国城市也有同样的地名来纪念不同的“赫尔曼”,有的是荣誉市民,有的是市长,或者是日耳曼部落的首领。柏林赫尔曼广场的存在开始于1885年,那还是有皇帝的第二帝国时代,纪念的是那位舍鲁克人或者日耳曼人,他原本是一位德意志-意大利移民,在罗马名叫阿米尼乌斯,在那里被训练成士兵。直到他似乎对毫无爱意的意大利欢迎文化感到失望,又再度移居到日耳曼,刚好在两千零五年以前,在离奥斯纳布鲁克不远的沼泽地中将罗马军团连同他们的统帅瓦鲁斯打得一败涂地(即通俗说法中日耳曼部落击败罗马军团的“条顿堡森林之役”)。不过,赫尔曼广场今天引起关注并非由于这一历史背景;更多是因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漂亮的字母“你害怕赫尔曼广场”。这件T恤衫连同同名的互联网博客反映了这一广场的特殊象征意义,展示的是“新”柏林的社会地貌和文化地貌。它正好位于草根多元艺术文化的旧重心“十字山”(Kreuzberg)与新重心“十字科尔恩”(Kreuzkölln)地带的交界点,是通向热点社会问题区“新科尔恩区”(Neukölln)的过渡地带。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还是都市现代性的核心地点:当时欧洲最现代的百货大楼Karstadt坐落在这里,这里是地铁和公交车的换乘站,贫民区和城市区的交汇地。直到今天,这个广场的外貌虽然保持着都市特征,不过标记的是另外的内容:这是一个由失业者、移民、毒贩子和涂鸦者构成的社会问题焦点地区。在这件T恤衫上,这些特征都被反映出来了:这是一个经典的“危险地点”的图标和象征,是大都市中那些不要去的地方之一。在依靠媒体化和奇异化存活的柏林“感受图景”中设定一个这样的“险地”,便是利用这一地点的传统并使其变为一种带有挑衅性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游戏。
这样一来,一句“你害怕赫尔曼广场”也带有双重含义:这是一种傲慢的挑战,也是向前往这些地区的人如旅游者以及新老柏林人发出的邀约。与之相随的隐含文本在说:“本色的”“真实的”城市,活在这些草根多元文化的街区,活在街区的共同体当中,他们将自己及其艺术、音乐和生活格调看作是特别的、先锋的:就是要与其他人的不一样。
同时,与新都市性的关联也就此产生出来。在新都市性中,似乎什么都能被变成文化,也就是说一切都足以、也有意愿被用于展示文化阐释,其象征性会被提升。在这种关联背景下,文化上的价值提升同时也能经济化和高端化:空间和地点、地产和房租、格调和特色都连在一起。考虑到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这种既富有创意、又不乏风险的共舞,今天的大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间政治和空间主体——正可以提供一个完美的实验室,来进行那些意图明确的或者“无心插柳”的高端化试验。“你害怕赫尔曼广场”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图标的知识产权属于当地的一家完全商业化经营的广告公司。
文化化——都市
柏林的这一例子要说明的是,调停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中的形象、平衡多侧面展示与刻意而为的奇异化图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话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今天打造“城市标识”与“社区建设”中都不可小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背景下“品牌”与“市场”的交互作用是多么紧密:这里指涉到城市中心的住宅和空间以及人们害怕其高端化。在很多城市,这早已经是头号的日常话题,因为城市中心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对居住者和投资者都是如此。他们都在意、也都力图打造“都市认同感”:展演都市的个性与共性,让都市生活世界中的经济威胁和社会威胁成为话题。

图2“我爱纽约”T恤衫(摄影 Wolfgang Kaschuba)
尽管有这样的模棱两可性,城市空间重获社会质量和文化质量这一事实,使得今天的城市,尤其是市中心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渴求之地。在1900年,马克斯•韦伯已经在最初的现代城市当中看到,人们充满渴望地感受到自由空气在城市中吹拂,生活格调的多样性以及生活方式的开放性让人兴奋得目不暇接。今天似乎我们又可以有类似的感知,我们的城市中心不再是一个纯功能性的工作与交通世界,即经典的由工业生产和消费组成的“福特式”地点。我们也从中看到生活世界的空间在日益增加,这要求城市有特别的文化质量,能够对当地人和旅游者、对老年人和年轻人、对单身者和家庭都同样有吸引力;对于那些新的生活方式——有生态或者能源、道德或者享乐的特定取向——都有发展空间。
在我们今天的渴望与马克斯•韦伯的渴望之间,是一段长长的城市危机时代。尤其是在1939年和1945年以后,城市因为战争的后果、汽车交通、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以及快速发展变成了那种“类属城市”(generic city),这是荷兰建筑学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自20世纪70年代就激烈抨击的:城市变成了没有生活质量和都市魅力的疲乏之地。库哈斯呼应了亚历山大•米切利西(Alexander Mitscherlich)断言的“城市的不适合人居性”的画面,他在此前十年将这一现象诊断为都市的单调性、社会匿名性以及愈演愈烈的逃离城市行动。1972年的德国城市联席会议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救救我们的城市——现在!”“我爱纽约”的T恤衫也在同一年出现,这绝非巧合。
在城市经历着深度的国际性危机之时,有一些来自国家的和地方上的反向计划出台,开始将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作为主动的、系统性的“文化化”来推动,作为有目标的文化上细胞再生举措。这些举措首先“来自上面”、经由城市发展政策而启动。法兰克福的文化负责人希尔玛•霍夫曼(Hilmar Hoffmann)提出的“给所有人的文化”这一口号变成了都市战斗号角。这在七十年代首先是一个城市文化“节庆化”的理念,其方式是要长期地设立音乐周、戏剧周,设立文学节、电影节,设立青少年之家以及文化中心。在八十年代接踵而至的是城市文化“机构化”,其方式是上千个博物馆和艺术场馆,老城的修复和重建。在九十年代,还增添了将城市文化项目“盛举化”:完备地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从大型古典音乐会和通俗音乐会,到艺术展览以及街头游行,这些“盛举”与国际性城市旅游热与都市形象政策结合在一起,让城市观光客的数量迅速推升。

图3 奥斯陆的歌剧院,2014(摄影 Wolfgang Kaschuba)

图4 被包装起来的柏林国会大厦(摄影 Wolfgang Kaschuba)
在最近的十年,市中心地带则出现了不折不扣的“地中海化”:系统性地让棕榈树和沙滩出现在城市中,城市沙滩、街头咖啡馆、躺椅、吊床、实况转播场所、晚会举办地等设施让城市的一部分慢慢地成为露天舞台和度假地。许多人虽然在话语中不无自我解嘲的意味,却带着极大的乐趣加入到这一新的都市表演中:这出戏叫作“现在我们来表演蔚蓝海岸(里维埃拉)!”尽管高纬度的地理位置以及比较低的气温,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必要时也可以用上通过公平贸易渠道购置来的毯子(柏林)或者不那么环保的电暖器(巴黎)。
公民社会——乌托邦
与“自上而下”的城市改造并行不悖,自20世纪70年代也开始出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都市化。都市项目和公民运动经由新的社会网络和政治活动而出现,人们占据城市空间、重整其原有的形式、赋予这些空间以新含义和新功能。一种遍及全球的“城市性”(citiness)从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种普适性的城市知识,它将新的都市生活格调与新“乌托邦”连接在一起,其组织方式是通过互联网或者街头,在这里聚乐晚会与政治的界线似乎终于被抹去了。我们的城市风景终于不再让人感到如库哈斯断言的那样毫无生气,相反是活生生的、有魔力的。至少对于那些有意在文化上发掘城市世界这一充满魔力的一面、并且也有充足财力的居民和观光者来说,的确如此。在这两个群体当中有这种愿望和能力的人,其比例如今都在快速增长。

图5 柏联邦总理府旁的沙滩,2013(摄影 Wolfgang Kaschuba)
都市空间作为文化实验场的功能并非全新现象,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若干世纪以来,欧洲城市的发展主要靠人口流动和移民,也就是说,人、理念、物品、价值的移入和交换。在跨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城市终于变成了“移民”地,成为社会相遇的空间,成为文化混合的区域。城市、流动性、外来因素在历史发展中彼此间的关联作用,已经成为马克斯•韦伯和格奥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思考的核心问题。尤其是西美尔曾经指出,要将外来者作为核心性的都市主体:与观光者不同的是,他们今天来到城市,明天还会留在这里;在很多方面,明天他们也还会是“外来的”,不会走进当地人的世界、让自己入乡随俗;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尝试着将自己的“不一样”变成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其形式也可能是坚决不入乡随俗。我们慢慢地知道,这种情况似乎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流动性和移民是城市的系统性外在关联因素,这在历史上已经体现为两种都市认同感:地方性的、容纳性的城区传统,以及同时存在的开放都市性,其根基在于城市社会异质性。这两种动力让城市的社会组合出现永久性的张力,这也给城市文化带来特殊资本:社会差异与文化上的多样性,给人们对于传统与创新、顺应与冲突、融入与隔断的经验带来了富有产出性的诸多层面。
当下城市文化和城市社会的建设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资本,大城市变成了晚现代时期的某种特殊偶像,日益增多地汇集了开放的文化纹理以及通行的象征含义。这些具有偶像性质的晚现代世界大都会如纽约、巴黎、伦敦、北京、甚至也包括柏林,为许多二线、三线的城市所抄袭、所模仿,它们也尝试将自己的市中心“都会化”“文化化”为某种有远大抱负的新形式,其目的在于产生认同感效果,以利于造成形成共同体的社会效果。这种行动策略显示出,在(德国的小城市)埃森或者巴登-巴登也不乏大都会的做法:举办大型的通俗文化活动、突兀的建筑物、将街区历史化与展示化、都市海滩和都市花园。所有这些活动也许型号小一些、花费低廉些、更费力些,然而它们带来的情感作用、在凝聚集体感以及提升认同感上的作用却一点也不少。
无论如何,这一趋势映射了全球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文化国际化的日渐增加,当人员流动、移民、旅游业显示出的可持续性交流效果已经初步凸显出来时,国际性文化交流便开始了。如今,互联网带来的可能性又步入全球文化交流行列当中,并成为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角色。认知与想象——开发城市文化有赖于此——有了全新的交流模式,这让我们的时空坐标发生了极端改变。似乎一切都是无限的,几乎都可以同时派上用场。“真正”生活在纽约或者巴黎,并不意味着能比在埃森和巴登-巴登能得到更多信息和知识,尽管在参与“本地的”活动和获得本真性方面还仍然有一些小小的优势。
实验场——城市
都市空间、图像以及网络的全球化让想象力提升,艺术和生活格调从中大为受益,因为城市空间越发强烈地被视为“公共”空间,一种谁都可以进入、可以当成舞台来设置的社会试验场地:街道被用作项目实验室,城市广场作为展示生活格调的舞台,房屋的外墙作为艺术画廊,餐馆作为品尝和烹饪的厨房。从中受益最大的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那种新“都市主义”——它经由不同的公民社会活动形式在我们的城市中迅速地传播和形成,比如上千个独立城市规划倡议与租户倡议,都市园艺和共有田园小组,维护学校与公园的活动,街区协会与跨文化沟通协会,环境与生态博客,圆桌聚会和社交聚餐,从南到北到处都有这样的活动,给我们的城市以一种让人“走进”的新方式。同时也有一些不怎么受欢迎的活动,比如针对难民居住区、建造清真寺和旅游者的敌意活动。“公民社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概念,几乎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类到这个概念之下。另一方面,我们也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这一标签下有很多私人利益,包括对外来者的敌意,被标榜成公共利益。这些也是我们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世界中需要观察和了解的内容。

图6 城市街头涂鸦中的观光客形象,柏林,2013(摄影 Wolfgang Kaschuba)
尽管如此,城市文化发展带来的后果肯定是利大于弊。原因在于,城市居民运动的讨论、展示、反思、组织和设计,其所有形式和实践都在重新磋商都市认同感设想和归属感,带有高度的象征精准性和确证质性;城市的主体在这里展演自己,同时他们也把城市展演为主体。某些展演有着竞争性的、冲突性的形式,许多展演采取的形式是理念、价值观和行动计划,其中有些是普遍共有的,有些则是某些共同体所共有的: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与宗教教区之间,不同的族群与性别之间,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在当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实际上,城市文化在运行“卓有成效的”社会融合政治和身份认同政治。
今天,我们的“公民”城市社会在精神上与政治上的更生实际上是都市“文化革命”。在战后的危机时代之后,城市社会和城市文化首先如凤凰一样从灰烬中一跃而起,为自己创造了新的主导形象、文化世界和生活格调。如今它们将“大城市”这紧张的功能世界逐渐转换成“城中心”这样有吸引力的生活世界。在德国城市的市场广场,人们露天坐在午后的阳光下,在大庭广众之下放松地喝上一杯意大利拿铁玛琪雅朵咖啡或者来一份威尼斯阿佩罗开胃鸡尾酒,尽管在口味上未必如人意,但是在精神上的享受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样的情形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了。
市中心的开放氛围以及城市对外敞开心扉的姿态,使得城市以一种新方式成为社会认同政治的核心资源。我们日益将自身、自我图像、诉求、愿景和希望与城市的生活世界、空间、设施和形象关联在一起。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实验场,也是展示文化意义上生活格调的舞台:在行使这双重功能的同时,在过去几年和几十年的公民社会更生中,城市也日渐赢得能给人带来认同感的新面孔。当然,这一切也让我们的城市感到不堪重负,因为我们想要从中获得一切可能有的东西:要安全,也要冒险;要共同体也要多样性;要聚会也要安宁;要消遣也要免费。这一切最好同时都有,而且最好在拐个弯就能到的地方;反正一切都要与我们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同时还要远得喧闹之声不会入耳。
城市要满足所有这些诉求,这肯定不容易。不过,我们已经从城市生活以及城市发展中明白了一点:城市成为实验场和舞台,要比成为停车场和墓地好多了!
K890
A
1008-7214(2017)05-0071-07
沃尔夫冈•卡舒巴 (Wolfgang Kaschuba),曾任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教授、所长,自2015年起,担任柏林社会融入与移民问题实证研究所(Berliner Instituts für empirische Integrationsund Migrationsforschung,简称BIM)所长。
[译者简介] 吴秀杰,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自由译者。
[责任编辑:王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