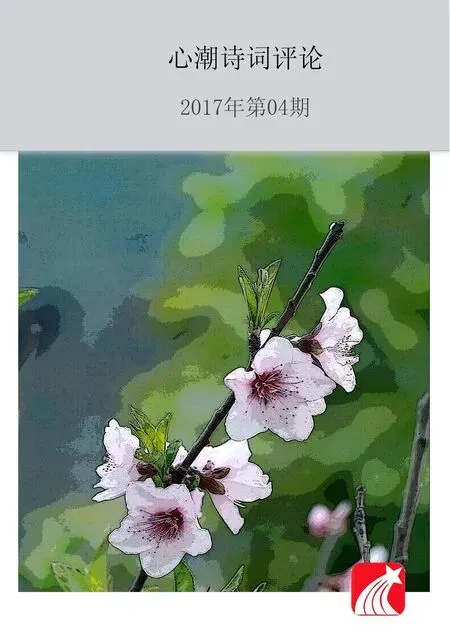笔走龙蛇,诗铿金玉
——沈鹏先生《三余笺韵》诗词赏析
林 峰
笔走龙蛇,诗铿金玉——沈鹏先生《三余笺韵》诗词赏析
林 峰
斥笔龙蛇走,冲冠鬓发邪。
苍茫唯独立,旷达致无涯。
此诗名曰《斥笔图》,可知诗为先生题画之篇什也。《三余笺韵》卷首即京师画坛为山方家为先生所造之像。画中先生健笔饱满,如虬枝临雪;银丝飘动,似霜鹤朝阳。复以白云舒卷之姿,秋雨淋漓之势,潇洒绝尘、卓然而立也。此外,画中再无一花一石、一草一木,苍茫大地,唯先生独立于斯。其旷达修洁,飘然出世之风采已与日月星辰合二为一,与天地宇宙融为一体。故画中不添一物,却似有万物萌发,生机一片。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此留白处方现真妙境也。正是:挥毫之际,喜烟岚吞吐;神游其间,欣襟阔无涯矣。
《三余笺韵》诗书双璧,互为映照。先生书艺,妙绝人寰,普天之下,谁个不晓。当年柳耆卿“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今日吾曰“凡有烟火处,人尽知沈书”也。看先生吹林扇树,呼云来纸上;拔剑横戟,唤风起毫端。先生斥笔,便如帐下千军任其驱使,阵前万马供其驰骋。其书法之创造性与艺术性皆当世无匹。前人曾有“观人于书,莫若观其行草”之谓。盖草书于书道诸体中极具个性化与表现力。而先生之草书最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先生法乎古贤而又自出机杼,能融古为己,推陈出新。观先生草书笔致开张,气韵生动;沉劲俊深,古朴飘逸。如灵蛇出没,又如神龙在天。堪谓:寓冲和于奇崛之中,寄自然于法度之外。动静相生,巧拙相间;我书我心,酣畅浑成。已辟大化之道,已开大美之境也。故先生之书能令人心驰神醉,物我两忘。先生书道,今人论述备矣。晚辈不谙书艺,今惟以片言只语聊述一己观感尔。
先生书中山斗,亦诗中名宿也。惟先生书名委实太盛,故予人“书为主、诗为宾”之感。其实不然,先生诗格律森严,语言典雅;韵味淳厚;体格高峻。且笔下寓意悠远,寄慨深沉。能自具面目,别开蹊径。读来清新净丽,满口流香。如:
苍茫暮色山如铁,万里无云月似钩。
诗思潜蛩吟断续,凉风初透入清秋。
(《山居夜静》)
诗写山中夜宿之见闻:夜色昏茫,纤云无迹;青山如铁,明月如钩。四围蛩声断续,凉风拂袖。诗人淡伫楼前,诗思如缕,不觉诗从口出,好一幅静夜山居图也。全诗景中含情,情与景合,且出句闲雅,语势空灵。青山明月之静与夜蛩清风之动相映成趣,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矣!此诗亦被先生视为得意之作。再如:
百丈危岩百尺台,群峰聚散眼前来。
峥嵘六十年间事,只隔东南海一杯。
(《奉化妙高台》)
妙高台位于浙江奉化溪口,为雪窦胜景之冠。远望则天宇苍茫,云雾四合;近观则波光照眼,松涛盈耳。人来台上,如置仙境,如上瑶池也。且妙高台与中国近代史密不可分。先生到此,怅触前尘,自然感慨万端也。危岩百丈,高台百尺,极写妙高之险;群峰壁立,众山环抱,可见妙高之幽。而“群峰聚散眼前来”之描摹又极为洒脱,似乎群山环列端为恭迎先生一人。如此构思则语境顿活使诗中又添一别趣也。忆及国共两党之争,不觉六十年矣。先生于此大笔一转,用“六十年”与“水一杯”之天壤反差,将如烟岁月、尘封往事都付诸清流一盏,个中亦暗寓人生百年不过世上一瞬之慨。先生真阅历深邃,怀抱别居也。此诗似写景而实咏史。清沈德潜曾云:“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事,已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而咏史诗亦每多沉郁涩重之作,而先生写来却极是轻松飘逸,大有运斤成风,游刃有余之快也。故诗中诸量词之遣用,皆有四两拨千斤之妙。如此举重若轻,非斫轮老手不能为之。
先生其性耿直,其骨硬朗一如其冲冠怒发,昂扬向上;亦似其如椽神笔,刚直不阿。故其诗作便多横空盘硬之语,劲健排奡之势,如:
久雨初晴色色新,山光峦表逐层分。
路回忽听风雷吼,百丈飞流大写人。
(《黄山人字瀑》)
雨后天晴,尘氛尽洗;山光峦影,渐次分明。首两句铺陈,原也寻常。至三句一转,石破天惊,如春雷贯耳,又似惊飚裂谷。但听得满山轰鸣,回声四起;飞流百丈,呼啸而下。气势何其阔大,气概何其峻伟。其声势较之李太白“飞流直下三千尺”想来亦洵不多让也。此诗景中寓情,情中见人。于先生心中,处世为人当如奔腾飞瀑,勇往直前;而仁心至性应如清泉千里,润泽山川。其心性之仁厚、品行之高洁,由此可以概见也,此黄山人字瀑亦可视作先生高尚人格之写照。
先生情牵桑梓,心连故土。虽万里暌违而初衷不改。一日先生过浙江舟山,泊宿于定海之上。忆及先祖躬耕垅亩,于斯起居,不禁感慨丛生,夜不成寐。晨起又见日出海上,渔歌回荡;远处重峦叠翠,水碧波平,更是情不能已,句由心生也:
日出东隅步履轻,层峦添翠水添青。
悠悠吾祖桑蓬志,不绝人间鱼米情。
歧路亡羊杨子喟,迷津问路桀长耕。
今宵何处舟中宿,汽笛长鸣又一程。
(《夜宿定海》)
先生心存夙愿,今来祖地,自欲一探究竟,故怀揣渴想,步履轻捷。远山近水,曾照故人之影;芳草云崖,长留先祖遗踪。山水依然,吾祖百年矣!昔年先人曾抱桑蓬之志,游历江湖;更负鱼米之情,泽被一方。每忆及此,先生便欲一展平生所学,造福乡邻。诗中先生以“歧路亡羊”“迷津问路”自警自励,令我尤为震撼。一八旬长者竟有如此恢廓之胸怀,不令人不折服,不令人不敬佩,亦足可为我等后学立一座标也。且诗中用典,浑然无迹,直似信手拈来一般,一如清人王士祯所言:“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池北偶谈〉)。由此亦可见先生满腹积学之精深。
甲午新正,马年伊始;神州万里,缤纷无限。面对斯景,先生亦时有新感,不吐不快也,试读其诗:
疆场万里一横行,呼啸风飞龙虎声。
志遂霜蹄弄骄影,功成玉辔待新征。
枥寒旧日苦温饱,厩满今时乐太平。
报效忠诚生死事,膘肥还欲请长缨。
(《马咏》)
马,嘶风践雪,掠野奔星。如青龙破雾,腾跃千里;又似金蛟出海,纵横九州。宋人王安石曾有诗云:“骅骝亦骏物,卓荦地上游。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骅骝》)。一代名相王介甫千年之后竟与先生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一如汉魏之乌骓赤兔比肩于当今世界之汉血宝马也。先生一路坎坷,遭逢跌宕。然履险涉危,不改下帷之志;经霜历雪,常葆磨铁之心。故诗中有志遂霜蹄,枥寒旧日之勾染。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报效忠诚生死事,膘肥还欲请长缨”如此结拍,尤其感人。此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独白亦或是诸葛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誓言。老人之霜眉白发与挚热丹心早已光鉴长天也。
先生一生所学似文江书海,渊薮恢弘。但又从不以此自许或固步自封。而是广设绛帐,遍开学馆;嘉勉后学,培植新人。故尔门庭兴旺,桃李满天。有诗为证:
它山玉石同磨砺,白雪青丝共雅音。
馀勇岂惟三寸舌,不才无愧十分心。
天寒似坐春风暖,巷隘难禁酒气深。
漫道雕虫咸小技,穷源须探广陵琴。
(《讲座》)
诗写先生开坛讲诗,传经布道。自古书为诗体,诗为书骨,又诗书一脉,诗书同源。先生自幼熟读经史,诗书同修;学储二酋,道通八家。故平日课徒授艺之时,亦主诗书双习,以丰学养;经史并研,以厚基石。诗中白发青丝互为衬映,春风好酒两相激荡,使画面色彩明朗,情感浓烈。而余勇与不才之自谦,三寸舌与十分心之形容,更是先生暮年壮心、不遗余力之生动体现。时人尝谓诗学技小而不屑一顾。殊不知诗学即国学,小技乃国技也。若传承不力,必成广陵绝响,岂不令人扼腕。老人暮年心绪,精诚一片,源于肺腑,感天动地也。汶川地震,惨烈空前。来时山呼海啸,地裂天崩;震后疮痍满目,百孔千疮。人居无是所,畜归无是处。灾民引领而望,华夏举国救灾。先生初闻震讯,五内如焚;回肠九转,欲哭无泪。远处云愁雾惨,眼前绿暗红销。先生哀思如潮,悲从中来。提笔写道:
五一二之前,汶川无所闻。五一二之后,汶川即近邻。虽无亲戚故,愿为汶川人。震波有远近,灾情结亲姻。神州凝板块,造化变晓昏。注目瓦砾场,秧苗又绿茵。
此时先生直欲腋生双翼,直下汶川,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虽无亲戚故,愿为汶川人”。先生如是想,亦如是行也。其不仅亲历义卖善举,且多次捐资捐物,仗义疏财,为汶川重建,慷慨解囊。其急公好义之仁心厚德,已在文坛传为佳话。先生心忧天下,情牵黎庶,其另有一绝亦堪与此诗互为印证。
白云泉水问源头,身与范公形影游。体味饔飧断齑粥,从知天下乐和忧。
(《过苏州天平山范仲淹读书处》)清风明月,落叶飞花;遥山绿水,石径松声。皆世间美景,人恒爱之。先生超然物外,恬淡闲雅,一丘一壑,一觞一咏皆能动其心怀,引其遐思。如:
叶落秋风至,仰天长一呼。
凭窗无远目,伏案可幽居。
暇日休窥镜,忙时要读书。
夜来闻蟋蟀,能入我床无。
(《丁亥新秋偶成》)
见一叶落而知秋,先生凭栏纵目,思绪萦回。楼头落叶纷飞,西风萧瑟;天边斜照朦胧,断鸿声杳。先生直欲仰天长啸,击缶而歌。想到一生忙碌,时光荏苒,先生亦难免有时不我待之感。又思至身逢老境,而犹能惜时如金,勤读不懈,也算不枉此生,稍感慰藉。刚念及此,忽有蟋蟀声响自窗外而入,先生童心复萌,顿生奇想。“夜来闻蟋蟀,能入我床无。”此句化自《诗经》“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语,但已自成格调,化古为新,显得自然天成。且语态诙谐,妙趣横生,极富浪漫色彩。尤其“暇日休窥镜,忙时要读书”两句,明白如话但又语重心长,堪称诗中警策,催人奋进。又如“垂柳眉长鱼水恋,残荷莲老脍莼思。”(《戊子秋兴》)“絮落泥中定,篁抽节上生。驿旁多野草,润我别离情。”(《雨夜读》)“早开旋早落,枝叶映流霞。念彼群芳好,明春先发芽。”(《壬辰秋咏迎春花》)等等皆诗中好言语,含蓄不尽,耐人寻味。
先生另有《自遣》一首,吟来极其闲雅,显得韵味无边。如:
性本甘清寂,生来少自由。病从药壶累,心向水云游。阮啸鸣琴起,陶吟采菊悠。惯看舒与卷,便说乐中忧。岁月砰然晚,雪霜好个秋。凭栏抒浩气,外物复何求。
此诗当可视作先生晚年生涯之鲜活剪影。晨观朝露,暮赏夕阳;窗前兰竹,案上琴书。皆先生所好,亦先生所钟也。病踪飘渺,中有人间忧乐;萍影东西,皆作世上云烟。先生所经所历已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故先生之所思所感亦非常人所能体悟。人世沉浮、百年哀荣于先生眼里亦不过身外余物、浊世尘埃。闲散似嵇琴阮啸,悠然似陶令东篱,逍遥如此,便纵有黄金千镒,亦不为所动也。惟岁月如流,砰然万里;转瞬之际,霜雪满头也。但桑榆未晚,尚有红霞满天;此生虽老,尤觉浩气不减。读先生诗,但觉其中时有蓬勃之声喷涌而出,醒人心脾,振人精神。此诗境界之空阔,思理之缜密,皆为上上之选。
三余集中好诗无数,佳作盈篇。如:“石劫千遭情入幻,诗经百炼气生柔。瑶琴弦断追前韵,管鲍金分启后修。”(《读汝昌先生九十华诞唱和集步晓川诗兄韵》)“人情练达通关节,世事悲欢急就章。好了歌如何好了,荒唐诗益转荒唐。奇书哪得千回读,磨墨人磨夜混茫。”(《红楼梦馆促题匾额》)皆别出心裁,见解卓越,且时空交错,极富哲理。再如:“涉世神灵忌,投毫鬼蜮訾。”(《读李汝伦诗》)则笔触犀利,入木三分。而“兔毫落墨三江水,国事开春八阵图”则气魄宏大,想象奇崛。“掷地有声真铁石,临川着墨幻云霞。”(《贺刘征诗长研讨会暨展览开幕》)此为先生赠刘征老七律诗中颔联,铿锵有力且色彩斑斓,已将刘老平生精华尽皆囊括,堪为诗中点睛。
先生帆扬学海,旆展书山;穷索典艺,苦研诗经。可谓翻破黄卷,挑瘦青灯。如此竞辰继晷,日锻月炼,故能法宗圣哲,道究天人。兼之先生天赋奇高,灵光闪耀,终成文坛柱石,国中人瑞也。惟先生功成不居,深藏若虚。其温柔敦厚,大有古君子遗风。先生曾有一诗可鉴其心镜:“学剑无能漫学书,浮名浪得遂知虚。为窥八法穷终岁,可惜平生负五车”(《检点旧作》)。如此谦怀,恰似曹孟德《短歌行》中言语“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也,放眼众生今已不复多见。《南史·庾肩吾传》又道:“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先生之平生绝学与人格操守亦足可为当代文坛树一楷模,立一典范。故诗文有终,而景仰无限也。晚辈昔日曾有《南歌子》一阕为先生八旬华诞寿,而今日用之本文作结,亦觉妥贴不过,并可聊表敬意于万一也。词曰:
风袅晴烟细,珠凝玉树清。舞催三叠吐琼英,醉得满堂锦绣尽东倾。 铁划临笺古,霜毫带月明。燕山云老起苍鹏,要踏青冥九万作歌行。
丙申谷雨后三日于京东一三居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方世焜